量子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无尽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优质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红牛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非凡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剧情介绍
影片讲述了由金柱赫饰演的画家英秀和他的恋人敏贞(李宥英)之间的故事。英秀从别人口中听说敏贞曾和陌生男人一起喝酒,这件事引发了两人之间的争吵。英秀第二天去找敏贞,却发现敏贞、也有可能是和敏贞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也可能是双胞胎,也可能不是)在和许多陌生男人不停约会,而那些男人全部都是她之前曾经交往的男人……演播时刻 第一季731恐怖女体试验彼得一世家园防线迷城攻略拉字至上:Q世代第一季星际之门 SG-1 第九季寻凶诀网络迷宫周末情侣开学吧,博仁少年荣誉团队 Honor Society锥子剪刀石头布 香港版狙击之王:暗杀辣手急先锋最后得分藏海传淑女情挑复合吧!前任复仇吧缘:出云新娘我是你的英雄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两个爸爸2016花魁2007大玩家1992超越边界2003天使不设防颠覆死亡博士刘罗锅断案传奇最后的棒棒睡美人2011钱学森清明上河图密码为爱而生4年,2男,1爱情东北老炮儿嘉莉妹妹吃货宇宙东京大饭店日以作夜
长篇影评
1 ) 这人生有什么,都是逢场作戏
是一部看了让人感觉糊涂的电影。
其实没有角色,只是被分成两派。全是男人与女人的对话,在爱的背景下,彼此抱怨,也互不理解。最后对话都只好被划入:你不懂xx。
而里面的人物其实又都是非典型的男人和女人。即便洪尚秀电影里的两性往往界限分明,主角也常常追问:为什么男/女人是这样那样的?
但进一步说,置身到这部电影的设定里,其实没有性别,只是被分成很多人。全是人与人印象中的对话,在梦的设定下,一切对话变得模糊,观众的想象得以被拓展,人物的胡来程度被放开。
导演在写剧本的时候难道真的不设主题?也完全不在意表达?看完电影,我反复追问。
怎么样才算认识一个人?而又如何去定义一个人?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感觉,得到对方的某一面。还是综合交错关系里的信息和说法,得到一个相对多面的概念?哪一种更值得被信任?
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抛来这些问题,但没有给答案。电影自身都常常分不清现实和梦。
看完一部电影,经常会有“看不懂“的怀疑。但其实不是不懂,而是没有感受,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时候,总是会用“好的作品不需要主题”的万能借口。
要习惯去做两件事,猜测创作者下笔前的冲动是什么?基于个人经验能够感知投射到的是什么?洪尚秀的电影,需要不懒的观众。
题外话:据说这部是导演在恋爱后写下的剧本,大概这是为什么,里面多了许多纯爱的对话。
抄一些台词:
“这人生有什么,都是逢场作戏。都会拉屎,都会吃饭,只有爱情是无价的。别的都是没用的毫无价值的。“
“我就想跟我爱的人好好地过日子,直到离开这个人间。我的愿望仅此而已,别的都是胆小鬼们会做的补偿而已。用扔掉真心的代价,而得到的补偿。”
“我的余生就想好好地活下去,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真正的爱情。不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之类的一幅画。”
“喝吧,是个好日子,而且还下着雨。喝吧,可怜的男人。”
“那我们经常吃西瓜吧。“
“好的。”
2 ) 爱是愚人的国度,看他们演的好辛苦

看洪常秀的电影,需要用到梁静茹的一句歌词:「爱真的需要勇气。」
一个导演,20年孜孜不倦地坚持沉浸在同一个剧情风格中,无论电影市场如何堆金垛银,他都是照常拉出几个男女,谈情,做爱,慵懒,茫然。
就像恋爱中的他和她,有情饮水饱,不会羡慕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
就像洪常秀那些电影,能上映就行,哪怕这部又不到两万人观影人次,大概他也不会羡慕百万和千万票房。
所以喜欢洪尚秀,以及看他的电影,都需要勇气。
爱这事儿,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比如爱能让一个人变蠢,谁都蠢过。
在洪尚秀的电影里,爱着的人则会更蠢,无论男女。
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们作为观众清醒着,或者洪尚秀不屑于迎合观众需求,制造角色代入感。
男和女,是他的。
情和爱,是他的。
你只管负责看就行。
看,《你自己与你所有》里——
睡觉的房子一如既往地狭小,洪尚秀的男主金柱赫和其他男主一如既往地窘迫。
还是一如既往:漂亮的女主李宥英喜欢他,和他在这么小的房间里说话,啪啪。
以及吵架。
猜疑、占有也是大部分男主的特点。
飘舞、游荡则是大部分女主的特点。
吵吧。
吵到最后,离去或者回来啪啪。
没有什么是不能以离去方式解决的。
没有什么是不能以啪啪方式解决的。
碎掉,或圆满地碎掉,看你选择哪一种。
洪常秀似乎不喜欢撕心裂肺式的吵架。他和她,闷吵。连痛苦都很像深夜的雾,浓烈,诡异,缥缈。
要么大雨滂沱,要么雪花纷飞,要么电闪雷鸣,要么溪水潺潺,你这么雾影绰绰,太不招人喜欢了不是吗?
大部分人会说是的,否则他的电影观影人数应该和名气成正比。
但雾也有雾的好,世上哪有看得如此真切的事?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也是一种美。
美是需要慢慢咂摸的,但就怕抿着嘴,美是咂摸到,蒙圈倒是好几圈。
这个时候别怀疑自己的观影智商,蒙圈的不仅是你,演员也是。
中国演员大概都想出演一次王家卫的电影。
韩国演员大概都想尝试一回洪尚秀的画风。
但并不简单,这俩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用剧本折磨演员。
不是剧本太厚,而是往往太薄,或者就是一张纸。
不仅是这部《你自己与你所有》,前面好多片都是这样。
比如2009年那部《懂得又如何》,就是他在参加仁川电影节时,就地找人,拉来了金泰宇、严智苑、刘俊相、高贤贞等人,对,河正宇也在里面酱油了两场,在只有一个片名的情况下,边拍边磨,花了不到10万美元拍成的。
但是它买到了10多个国家,还获得了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编剧提名。
服吗?不服忍着吧。
很多敬业的演员在开机前都会认真揣摩阅读剧本,理解所饰演人物的性格,甚至动手补写小传。
「人物小传」在洪尚秀这里是个不存在的电影名词。
他是谁?为什么这么做?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演吧。
在《你自己的与你所有》里,金柱赫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的、李宥英不知道自己的性格定位、金义城不知道为为什么要怂恿弟弟……
除了导演,不,连导演都不知道这些。
他们演的好辛苦。
最后说下剧情吧。
讲真,洪尚秀的影片内容是用几句剧情概要装不下的。我写过不少影片的解析,但却忌讳解读他的片子。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洪尚秀,你看到的、想到的,就是你的。
哪有什么标准答案,你完全可以将「自以为是」变回中性词。
也许,这就是洪尚秀和他的电影的魅力。
✎文︱韩影书 ©原创︱著作权所有
3 ) 洪尚秀的小把戏越玩越娴熟
4 ) 从《爱上两个你》说电影
1
洪尚秀的《你自己与你的所有》(又译《爱上两个你》2016),获得64届圣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贝壳奖。在我看来,这种荣誉对于他来说太轻。我一直把他的电影当成无冕之王,也就是说,获奖反而对于他是一个讽刺,因为他的电影跟那些电影节的热闹与所谓艺术的主旨,完全完全的不搭界。你能想象小津的《晚春》去得“金棕榈”吗,那就太可笑了。

这就是《罗生门》与《东京物语》的区别,无所谓高低,只是风格各异,两类镜语,两种表达,各人喜好的口味不同而已。120多年的光影史,注定有一类不属于得奖之列,但却是这个星球上永远的一汪心水,如同那些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熠熠升辉。
你可以说洪尚秀一直都在重复自己,如同小津战后《风中的母鸡》之后的光影,总是重复着茶泡饭般的滋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扑扇流萤,正对应着他战前光影的苦业无明。在他参与了一场侵略战争后,兀地风格大转,风向大变,不再是《长屋绅士录》的寻子慨叹,也非《父亲在世时》的未了肿胀,抑或《东京合唱》般的生活窘迫,更非两屁男孩总是做着不许动的鬼画符手势。
战后的小津,似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否就是他对于这场战争反思的结果,还不得而知。生活如流水,开悟过后的他,只对流光碎影感兴趣。于是他用平稳的镜语,去静静地表现衣食无忧人生活的情感嬗变,不以离奇的情节去取悦观众,而是以角色的看似微不足道的情绪,呈现他们纠结不已的心事,然后去试探、感应及对接,有时是如笠智众与原节子这种“父女之间”的心结,有时是嫁女后的无语徒叹,更多的是注视和静默。
小津光影中的人,他们总是一直在等待着什么,永远的在等待着什么。这不只是人生的终点这么简单,真的把女儿嫁了出去,却也非如释重负这么简单,反而彼此的牵挂,更有一种愁肠百转之感。我想,那一定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观照和细细打量。小津与编剧野田高梧一边饮着清酒,一边凝视着远山流水。他们的一致,犹如他们的口味。他们不再依赖叙事这种一般的方式演绎光影的精彩,只需悄无声息地呈现角色微妙的情绪即可。所以,我说过,只有那些能精准又诗意地阐释角色情绪的光影,才是最高格的电影。
世界百年光影史能一以贯之这种风格的,并不多,有的只是灵光乍现,并不能持久。格里菲斯是这种诗意镜语的源头,然后是德莱叶、布努艾尔,战后,布莱松、安东尼奥尼、伯格曼、费里尼、安哲罗普洛斯及塔可夫斯基,都各自创立属于了自己独特的诗意风格,而现代的维姆·文德斯、罗伊·安德森、贝拉·塔尔和布鲁诺·杜蒙,则属于后现代镜语,完全是另一种高格。大卫·里恩与赫尔佐格,注定属于另一种恢弘又奇异光影的气象。法斯宾德只属于他自己,让人伤怀。
就地域而言,我常称为中东铁三角的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都有着各自的独立镜语,尤其是以阿巴斯和莫克马巴夫的伊朗,带动了他们的追随者,在重重铁幕之下作出了最为成功的尝试。而东南亚的阿彼察邦、陈英雄和潘党迪等名导,对应着中国台湾的侯孝贤、杨德昌和蔡明亮等,催生出有别于小津电影的另一种现代性东方镜语。这当然归功于独一无二的侯孝贤,他是这种现代东方镜语的创建者,或者说集大成者。
如此说,都不为过,因为侯孝贤有一个系列镜语体系支撑。不成体系的,就只能说是灵光乍现。或者可以说,杨德昌对应着潘党迪,而侯孝贤则肯定对应着陈英雄和阿彼察邦,蔡明亮犹如杨德昌和侯孝贤的混合体脱胎而出的独特创作。王家卫和陈果则是从香港这块活色生香的海角长出两朵最炫丽的奇葩,《重庆森林》和《香港有个荷里活》,总是会《榴莲飘飘》。
2
那为何我先绕过中国大陆,不是因为没有好的镜语,而是还未形成体系。我所说的体系,是指哪怕一个导演能一以贯之拍摄一种高格的电影。王小帅算是,且极为难得。《白鹿原》之前的王全安很猛,我对于他一直抱有期待,《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等都很牛掰。李杨《盲井》《盲山》后,没能持续,让人遗憾,这同样受制于电影的审查。张杨很安静,还坚持着。张元《回家过年》后,遗憾因为别的原因,未能发扬光大。
娄烨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风格,仍属于《苏州河》《颐和园》那种驳杂又冷峻的光影,可贵的是,他总是在探索之中。这些年的大陆的独立导演,基本上也都是这种凛冽风格的延续,还未真正达到更高的创作层次,镜语大多还属于模仿和探索阶段,都是压抑状态下的自我表达,仅此一点也弥足珍贵,且是中国未来电影的希望,无疑就是他们。
这其中的优异者可列一长串名单,其中身为作家的导演万玛才旦无疑是这群作者影像当中的翘楚,其扛鼎之作《塔洛》一再被提起。其它的卓越者,不止是作者电影(包含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如拍摄《铁西区》《疯爱》的王兵、《流浪北京》《调查父亲》的吴文光,李红旗的《好多大米》,茅毛的《此处,彼处》、杜海滨的《少年小赵》,赵亮的《悲兮魔兽》、毕赣的《路边野餐》、杨超的《长江图》等等,还有很多,未能尽观,恕我未列。这群新锐方阵之巨,足以让人叹为观止,所以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这同样需要坚守。挺住意味着一切,并非一句空话。
而这二十年名声最大的贾樟柯,自《小武》《逍遥游》《站台》之后的电影,总体趋于平稳,如果说要有所超越,或只是突破自身。这三部佳作,每年都让我不自觉的拉一次,尤其是《小武》,我试图找出与布莱松《扒手》的异同,结果乃徒劳,完全是不同的影像,这就是贾氏活化于自我影像的集大成风格。但另一个问题是,《三峡好人》之后,贾氏风格有了延展和多元,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其本身就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何我们的导演不能一以贯之的创作属于自己的电影,即作者电影,总是在途中会发生裂变或脑梗,为何?!仅仅是因为自身环境变好了,养尊处优了,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名利诱惑哪里都有,那为何别人能把自身的坚守保有成一种固执的习惯,而中国这些导演一旦成名后反而不能。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创作多元的作用及视野宽泛的取舍。其实,这并不可怕,尝试多元,如果发现跟自己原有风格不搭,还可以返回,就怕总是在变化总是在尝试,没完没了,最终肯定会丧失自己原有的风格。时间是经不起折腾的。凡人事都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为时间总是会眷顾那些始终如一的诚实的人。
试想,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如果一直坚挺自己《活着》《霸王别姬》《太阳照常升起》之前的风格,这将是怎样的壮观景象,但他们放弃了坚守,等他们想转身时发现未时已晚,心态变了,思路变了,创作的“处子之身”早被打破,《归途》成了强驽之末。当然,还是要为这种理性回归给予一赞,但他们创作的状态想找回来也并非易事。
这一批名导中,唯有拍摄过《猎马札撒》《盗马贼》《蓝风筝》等经典佳作的田壮壮导演,一直在坚守,他从没有屈服于市场,去拍什么大片,他是自我电影体系的创建与坚守者,这点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本命年》的老导演谢飞乃是一个榜样。还有一直静谧地拍摄属于自己影像的霍建起,从未有波澜,也从未有离开,这本身就极为难得。顾长卫的《孔雀》《立春》,稀有的清醒与警醒,乃是一种思想上的构建。如果一个创作者,要想保有一以贯之的创作,唯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状态,守株待兔般拍摄属于自己独有的影像,这看起来很笨,却是朴素创作的真理和大道。
回想一下,谢晋1986年拍摄《芙蓉镇》之后,面对其拍摄风格的指责,于是也想变一下,结果一部不如一部,这让他自己大为痛苦。不单是电影创作,所有的创作,都应坚挺地保有一贯的状态,静静地,默默地,不露痕迹的,时光总会奖赏这种静默的状态。如果挺不住,人云亦云,跟着西方那些零碎的影像概念去走,总是会吃大亏。
归根结底,创作者的使命担当,终究是第一位的,这点从伊朗电影人的顽强坚守,就能得到最好的答案,无须赘言。其实,中国电影人什么也不缺,就缺使命担当。他们不缺钱,更不缺才华,小聪明比比皆是,就缺点憨憨的劲头,缺点笨拙。
其实,这些年,那些从西方舶来的某类东西,并不新鲜,五十年代就被西德克鲁格等玩滥了,这边有的人却以为找到了“真知”。我经常说,这些只是形式感的炫技。谁玩悬乎谁玩空。戈达尔只有一个,你再去跟人家玩,就只是死胡同。形式永远只能为内容服务,如果内容空洞,形式玩的再酷,那也只是自欺欺人。再加上,有的人内心的风骨早没了,受不住名利之惑,结果就会栽在名利之上,纵然天天走在红地毯上,那也只会遭人鄙视。导演还是得拿出过硬的作品说话。
3
说了一大通不客气的话,那我就得回到洪尚秀,韩国这位独一无二的创作者(当然,金基德也是,但的确我对于他有点审美疲劳了,他还是要靠离奇的叙事致胜),让我真的心悦诚服。我之所以不用导演,而是用创作者,因为作者电影如他这般,编剧和导演,甚至摄影基本上都是由他通盘掌控,可谓彻底的作者电影。这部《你自己与你所有》当然一以贯之了他之前的影像,这是基本点,或者说其核心所在。
身残志坚的画家崔英秀,跟漂亮的女友敏贞同居生活,但这段时间,让他很是苦闷,他总是不自觉地疑神疑鬼,怀疑这个天天睡在一起的女人,跟别的男人有一腿,具体是谁,他也搞不清,反正如同他说的这是直觉。他说,他的自觉很精准。为何精准,因为他靠自觉创作绘画,这是他跟老友说的。

老友劝说他想开点,但他说你为何不替我想想。老友劝说无效。的确,喜欢泡在咖啡馆的敏贞,总是独自品尝,谁不想跟这样亮爽的女人搭个讪说说话呢,于是乎自称画家的男人和自称话剧的编导和眼镜男等,都上来主动跟他搭讪,要么说是以前在某个画展上见过,哑谜打的还挺玄乎,但效果不错,要么说有一个角色适合你来演,效果当然也不错。
敏贞也总能应付自如,因为她从不报上真实姓名,让人误以为她是敏贞的妹妹,或者她就是另外一个女人,只是说她长得跟敏贞像而已。其实,她在跟这些男人笑谈时,并无过多暧昧举动,最多也就是说到兴奋处搭个手,身子前倾点,仅此而已。
影片出现繁贞第一次去咖啡馆返回后,一直闷闷不乐的崔英秀同志不干了,他从床上起身质问她干吗去了。有点闷,去喝咖啡。跟男人吧。不,一个人。我感觉你跟一个男人。不,一个人。我相信我的自觉。但你别忘了,我养着你(你的鬼自觉养不起你),我这么辛苦,工作累了,去喝个咖啡,你也要像审问犯人一样的对我,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疑神疑鬼?!
嘟嘟嘟,你还有理了,告诉我是谁,我非揍死他不可。这日子没法过了,跟你这样的人,真的没法过。嘁嘁嘁,你跟男人一起咖啡馆,还有理了。不跟你说了,我们分开吧。分开?是啊,分开,不是离开,分开,说明你还有那么点机会……

这下问题大了,真的分开,崔英秀同志可受不了了,立马瘫软,孩子般“哇”抽泣,哀求她别分开。不,真的要分开,要不你这样疑神疑鬼地会没完没了,真受不了你这样子的忽冷忽热,我出去了。你真的出去,这么晚了,要是遇坏人怎么办。什么坏人。我是说遇到吃你豆腐的坏人。你就是把世上的人都想得那么的坏,你也不是坏人……敏贞真的走了,分开与离开,只差半步。
之后,拄着拐杖的崔英秀遂进入寻找敏贞的模式。寻找当然是一个阴差阳错的逗逼过程。敏贞对于他的待见,仅形同于他刷自我存在感的意义。如同他老友所说女人要哄。英秀同志也想哄来的,但说着说着无名火就上来了。敏贞说,为何你的无名火总是那么大。所以,这不是吃醋妒嫉这么简单。崔英秀只能在敏贞身上才能找到存在的价值,至少他潜意识这样认为,或者说事实也是如此。
而敏贞却不能在英秀同志身上找到丝毫的存在感,反而只有无穷尽的指责和愤怒,她当然要逃之夭夭。她却能在咖啡馆在别的男人身上找到存在感,不管那些男人怀有什么样的目的。这就是差异。差异迥然,想法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更不要说谐和与幸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显然,她是不满足于现有感情,这个拄着拐杖的男人过于反复无常,过于失去理性,总是在自我的假设中生发诸多肿胀感。

再者,敏贞这样的女人,的确渴望得到更多的爱,让爱填满苦闷空虚的内心,或许对于她未尝不是一个解脱。有时,跟异性交流,至少那聊天的海阔天空,可以抚平其内心的不快。这并非说她水性杨花,如同不能说洪尚秀影片中的男人都是花心大萝卜。
咖啡是苦的,喝下去却能解乏。咖啡馆的老板和员工总是对她频繁更换男人谈心,免不了戳戳点点。那她到底是谁呢。她希望活出不同的我,一个精彩,一个沮丧,这恰是幻想和现实的一对矛盾体。
4
在寻找中,英秀同志总是很恍惚,如同他拄着拐杖那么的不利索。敏贞的亮丽让他挥之不去,更让他如坐针毡怕她跟别的男人跑了,那只永远不会落下的靴子,总会担心哪一刻会砸在头顶。好在第二次寻找见到了她,他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样乖乖地坐在那,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思念你。敏贞是一个柔情的女人,抱着他的头说我也想你。那让我们和好如初吧。好。
虽然说了好,却未见他俩真的在一起,反而英秀在继续寻找,或者说他在寻找某种不确切的东西。如他跟时装店女主人和小饭馆女主人交流,看起来略显多余,却是他六神无主的证明。

男人只有失去了,才会反思,但依然会固执己见,江山难改,秉性难移。敏贞若妥协了,如常一起,想必即刻陷入互伤的恶性循环。不眠不休的对掐遂成了疑神疑鬼的常态“斗鲨”模式。这非一句对错所能了然和概括的。这是男女两个物种,面对感情的不同应对方式。或者说,爱情和婚姻中,某一类人处理情感的生动呈现。
但是,也许是看到英秀同志寻找的太辛苦,影片最终还是让他跟敏贞在夜色的小巷相遇。之前,她从咖啡馆两个为了她逗逼的男人中脱身而出。英秀问他为何拄着拐杖,他说受了一点小伤。想起片中,她对那位画家所说的,她喜欢残缺的美。在这找到了佐证。他请求她和好,她说我们都已分手,他再三请求。终于他们和好了。
原来,这第三段,其实是他们之前某个N次分手后的再次邂逅。随后,他们在停电的小屋里,烛光摇曳,二人相亲相爱的谈心。敏贞说停电了,爱爱之前停电最好,我觉得刚出生的宝宝好可爱。他说当然了,生命的开始吗。她兴奋地说你说的好有哲理。我会当个好爸爸,好老公。所谓爱上两个你,只不过是时间作用于爱情的反差而已,并不真切。
突然,她头疼了。幸福来得太快了,让她承受不了。想必如此反反复复的折腾,让她有点恍惚。只是一会就好了。她说是不是我们谈情说爱的太多了。当然了,我们以后要一直这样。但她说我还是怕幸福会消失,不过,我曾经拥有过。他信心满满的说,不够,要一辈子。
可能是聊得太多,都有点饿了,想到了冰箱还有西瓜。切好后,她端过来,一块块地送到他嘴边,看起来真的好幸福。只是这过家家般的幸福,只是他俩分分合合的其中一个场景而已。因为,只有停电了,他俩才有机会谈情说爱。这是导演的精心设计。爱情与心情,似乎都是要靠撞大运才能有一个欢愉时刻。

洪尚秀一直喜欢表现这种想爱却不懂得如何爱的男人,有点蔫坏,有点搞怪,有点磨矶,当然还有点闷骚,甚至有点猥琐。惹鬼又怕鬼,一旦惹到鬼上身,又想找借故逃离。他们无一不善饮爱发点小脾气。低度烧酒和日本清酒乃是导演的醉爱。善饮的男人,是否都是如此这般呢。我想,这正是洪尚秀电影的生趣所在。微醺过后,男人一般自会胡言乱语,任性而为,不免让人发笑。这正是洪氏电影对日常生活阐释精准的所在。
实际上,洪尚秀利用同一风格创作不同电影,借此全面解构男人如何被女人吸引,如何被女人塑造又如何被女人鄙视的逗逼过程。男人到最后,为何总是会成为女人眼中的废柴。看似男人主宰的世界,实际上是被女人掌控着。
不止于此,更主要的是其中的品味过程,这才是洪尚秀的牛掰之处。这种悠悠品味,配以那谐趣的合奏音乐,让男人一会狗急跳墙,一会软不拉叽,一会喜笑颜开。有鉴于此,洪尚秀的每部电影,也就是一个生趣的试探之旅,好像永远没有尽头的探索,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内心的情感之需,还是身体的存在之求。
如同我在一篇文中所说的,他的电影总是润物细无声,让人沁入心脾。他的电影,还蕴含一种神秘的喜悦,或者说欢愉之后长长的落寞。冷静的街道,局促的咖啡馆或小饭馆,男女的静静对视,抑或男人酒后的哭哭啼啼,皆是洪尚秀电影不变的幽趣所在。这注定了他的创作永远没有停顿,如同他创作的这些角色,永远没有情感的安然和结果。
你自己与你所有,并非对立的存在,当然,也非最终的谐和。原本他们都还在路上,如同我们,永远都还在路上晃悠,永远没有一个结果。没有结果,说明还有某种熹微的希望,这才是有滋有味的人生吧。
2016、12、12
5 ) 你自己与你所有
6 ) 爱情的六耳猕猴
佛说六耳猕猴的诞生源自师徒之间的不信任。在《你自己与你所有》中,导演也讲述了一件爱情跋涉之中六耳猕猴的故事,让人沉浸与现实的虚幻之中。
影片开始,男主与好友的一番对话后,男主对恋人产生了怀疑。
接下来是另一个场景中一个女人与一个陌生男人的对话,男人似乎认识该女子,可女子却绝口否认,男人一开始就叫出了女子的名字“敏贞”,正是男主恋人,可女子最终以双胞胎妹妹自称,并和这个男人开始了交往。“六耳猕猴”似乎就这样诞生了。
接下来是第三个场景,男主卧室中的第三段对话。男主与恋人敏贞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敏贞一气之下离开了男主。
影片这三个场景的切换,三段对话,把故事彻底铺开了,接下来将人引入了虚虚实实的世界,或者说“六耳猕猴”开始“胡作非为了”。
同样的咖啡厅,同样的座位,同样的女人,不同的陌生男人,一切与开篇第二个场景如出一辙。更加有趣的是两个男人还曾是中学同学,他们因这个女人再续前缘,给影片更增添了一份生活趣味。



我认为影片中最为有趣之处在于男主的想像,他在去敏贞家道歉时,坐在门口,此时影片描述了男女主复合的场景,当人以为破镜重圆的时候,影片切回现实,男主没等到恋人,独自离去。结尾处又有一个画面与之呼应,男女主幸福的坐在床上,谈着谈着投入睡眠,镜头转向床下的蜡烛,火焰似乎就象征着这场爱情一般,飘渺却又真实,镜头转向床上的男主,此时只有他一个人,我不禁又怀疑之前的甜蜜是男主的YY,可就在这时,女主似乎是从厨房回来,她给男主端来西瓜,两个人甜蜜的品味起爽口的西瓜。导演就这样挑逗着观众的神经。




敏贞作为影片中神秘的存在,她的真实性挠得人心里痒痒的。影片结束于男主与敏贞的复合,或者说男主重新认识了一个与敏贞一模一样的另一个女人,男主最后向“新”的恋人表达真心,正是对她表示完全的信任。也许如果最初男主没有听信朋友的传言,接下来的一切都会化为一缕青烟。
正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导演创造了六耳猕猴般的敏贞这样的角色,也许并不是想要告诫人什么,而是鲜明的描绘出了生活的趣味,让人能够在这样的虚虚实实的生活中去发掘乐趣。这也是这部影片的魔力所在。这让我又不禁想到《这时对那时错》,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心理微妙的差别而出现截然不同的走向。洪尚秀的电影总是如此简单,如此朴素,却又如此深入人心,可见他颇得生活之道。
毕竟,说真的,全身心地对对方投入信任,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们也许就生活在似梦似真的世界中,想想真是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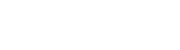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男渣女婊,天荒地老,恋爱脑的男人真是蠢透了(包括尚秀·洪...)
恋了爱的洪尚秀,依然洪尚秀。渣男配婊女,撩闲与闲聊。浑浑噩噩,酒馆喝酒。恍恍惚惚,床上吃瓜。
哎我为什么要看洪尚秀
天哪,熱戀中的洪尚秀!
生活的发现,懂得又如何,试过才知道,剧场里和剧场外,拍完电影去私奔
继续男人与女人的交锋,爱一个人能否接受包括缺点的所有,正可谓恋你非你。喜欢幻想对象更完美并且征服欲强的男人,实际在情感关系中反而占有主动性的女人,在失忆与初识的游戏中尴尬美好,甚至爆笑重逢后对男女的双向嘲讽,总体不如上部但也干练有趣。台北金马影展。
不知道为何第一次有了看腻洪尚秀的滋味。一如既往的尴尬,只不过我觉得我需要一本鉴婊手册。
这届洪尚秀不行
Nobody's girlfriend Minjung.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几个韩国妹子是同一家整形医院整出来的... 🤷🏻
看著他每年一部,有種看人練武之感,更簡約更精緻,連多餘劇情也沒有,說洪氏有潔癖,更是他如何將手法隱藏內化敘事。同樣母題,但變出一部《變形記》,証據是女孩在咖啡店閱讀卡夫卡,連身裙,還有衣服店換杉公仔,女人是觸摸不定。但男人嘛?依然愛死一個對象(究竟是幻影還是另一個?)你愛的是什麼?
三星半。私以为,洪尚秀是一个野心大于才华的导演,这对于那些想要对他进行阐释的评论家来说是致命的。强撩,最后那些影评比电影还尴尬。洪尚秀的电影太随意了:当天写就的剧本,演员突发情况也自然的进入剧本,凌乱的构图...但authorism的他似乎要去颠覆一些电影中传统的法则,总感觉心有余而力不逮..
头一次感到洪常秀也有要看得够够儿的时候……不玩结构只靠梦境就真的无聊得紧了。《自由之丘》这种纯属无聊到爆的尬聊片也因为神一样的结构变得饶有趣味。论梦境,无数前作都比这个好,要是论喝酒,哪里比得过《夏夏夏》啊。大概其有趣的也就是这个戏精附体的女主(长得真有点像金敏喜!)
导演是不是在自黑我不知道,这次没玩结构,概念却又挺有趣的。一顿大酒过后,又是新的一天,又是一个新的我。女人的虚伪多诚实,我不认识你我缺爱你快夸我美。而男人的诚实多虚伪,我还是那个我像最初一样爱着你你是我的全部我向你保证不干涉你的生活。
干了这杯,我们从头开始,不对,是我从头爱你,你随意就行。
没有烧酒,只有米酒加咖啡。结尾的小伎俩强调了并没有梦,日常转为寓言和男主的两次恍惚更近乎于虚实相间的白日做梦。结构则转成了性别上的对立又统一,一男逐多女好比《夜与日》,一女戏多男则又是《我们善熙》,在爱情中谁能懂永远谁能懂自己?洪常秀恋爱中的作品,不存在好不好,只看你腻不腻。
故意(或非故意)隐去的某些细节让时间线出现故意(或非故意)的颠覆混乱,与近年《这时对那时错》《自由之丘》都有相似处,三段“认错”不仅在结构上一以贯之的互相照映,更呈现出调侃两性关系的惯常趣味;身份的不确定,“情敌”的意外相认,狠狠揶揄了一把男人们。
就别责怪洪尚秀的片子总是喝喝小酒、拉拉小手,路边抽烟,咖啡馆搭讪了,就男女之间那点永恒的破事儿,别管发生在哪儿哪儿,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连说的台词不也是千篇一律?就算花样翻新的开辟不同的场景,上演的,也终究只会是相同的戏码。所以,就这样吧。
洪尚秀:剧情三件宝,素淡女人,憋闷男人,嘴炮聊骚。用景三件宝,咖啡酒馆,路边小摊,无人街道。主题三件宝:关于爱情我知道。关于性我知道,关于爱情和性TM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仍是梦境与想象,小趣味与小细节,似你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