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剧情介绍
乔在父亲死后,陪母亲卡特琳娜赴意大利参加歌剧演出,却因寂寞而染上毒瘾,使卡特琳娜份外心痛,对乔百般迁就,竟使两人发展出一段畸恋,在道德觉醒下,幸未造成大错。卡特琳娜不得已将隐藏多年,乔另有生父的秘密说出,为使父母破镜重圆,乔乃前去找寻亲身父亲。 导演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阐述这对母子的行为,认为人的所有意义和能力都源自于性欲的需求,月亮是代表母亲和女性形象的载体,以隐喻母亲对儿子的性影响链·爱人狼游戏:地狱走佬威龙女孩,女孩战旗飘飘英雄光荣绽放——杨靖宇中国女孩2023跟随节拍跳起来超能第二季那年八岁情妇第四季监视者粉雄救兵:德国篇第一季圣诞奇迹2024魔鬼雷普利救僵清道夫我们不能在一起末法王座之影他乡明月群青战记松江教父我才不会被女孩子欺负呢荒山女侠我的简·格雷第一季绿皮车黑色画集~证言~太阳的新娘棉尾兔盾神二十一天德雷尔一家 第二季踢出一片天理科生坠入情网女神本色出走的马蹄螺旋:町工场的奇迹隐秘的诱惑反杀202238岁的伊丽卡你好乔安初来乍到 第五季横财三千万全程直击第一季
长篇影评
1 ) 《月神》:循环困境下的欲望母题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775.html
舞台之上,是威尔第歌剧《费德尔》的演出,卡特莉亚的激情演唱将自己的演艺事业带向了顶峰;舞台之下,是坐着的乔和保罗,他们隔着一些距离,但是在卡特莉亚精彩演绎的时候,他们相视而笑,然后热烈鼓掌——台上和台下,演出者和观看者,以及母亲和初次见面的父子,仿佛在着“月亮”升起的晚上,真正走到了一起,而缺失了父爱的孩子也第一次在父亲归位时长大成人。
《费德尔》剧中的那句台词似乎是贝托鲁奇用来阐释着最后的月圆之夜:“我的成年已经到来,我为自己能认识到这一点而鼓掌。”但是那一枚月亮却并不是真实出现在直升飞机飞过的天空,它只是舞台上的一枚巨型聚光灯,当人造的月亮取代自然的月亮,贝托鲁奇所命名的“月神”是不是也成为了一种人造的景观?在舞台演出开始之前,保罗走到卡特莉亚身边问她:“我的儿子呢?”卡特莉亚指着台下坐着的乔说:“他在那里。”保罗慢慢走下来,在走近乔的时候,仔细打量了他,但是紧接着打了一个耳光,遭受了肉体疼痛的乔没有哭泣,只是低着头摸着脸让自己慢慢恢复,而当卡特莉亚在舞台上正式开始演出时,那一个耳光带来的疼痛似乎全部消失了,在对视中,在微笑里,在鼓掌中,仿佛这个光不曾落在乔的脸上,仿佛生父对于他的第一次见面完全充满了喜悦。
保罗为什么要打乔一个耳光?乔为什么在被打之后在母亲的荣光中微笑面对?贝托鲁奇似乎想用一种羞辱式的仪式结束父子分离的痛苦,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保罗不是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反而是乔,他在几乎不知道自己生父还活着的情况下成长,在一种爱的缺失里,他疯狂,他极端,他甚至染上了毒瘾,最后甚至和母亲卡特莉亚发生了乱伦,一个缺失了父爱的孩子,一个生活在变态母亲身边的孩子,为什么反而遭受了疼痛的耳光?而当耳光打下来,隐忍的他在最后露出笑脸怎么就变成了一种成长?而实际上,在这个欲望被压抑又导向歧途的过程中,真正的实施者正是卡特莉亚,而在一记耳光的仪式里,她站在舞台上继续着自己的梦想和理想,非但没有为自己曾经的自私而付出代价,反而在父子的鼓掌声里变成了“月神”。
卡特莉亚和保罗为什么要分开?贝托鲁奇并没有直接的交代,但是开场和结尾却提供了解读这种缺失的线索。开场时是幼年的乔,他光着身体坐在阳台上,手上拿着一块饼干,饼干上的蜂蜜流到了婴儿的腿上,这是卡特莉亚开始用嘴舔着乔腿上的蜂蜜,又吮吸了手上的蜂蜜,接着给了乔一块饼干,乔把饼干送到嘴里,却突然呛住了,于是在咳嗽声中他开始哭泣。这时候出现了父亲保罗,他的手上拿着盛满鱼的篮子,然后拿出刀开始剖鱼,这时的卡特莉亚开始播放强劲的音乐,在音乐的带动下,她和保罗开始在阳台上强劲舞蹈,沉浸其中。而受到冷落的乔哭泣走进了屋子里,屋子里的女人正在弹钢琴,她是乔的奶奶,保罗的母亲,当乔向她走去的时候,身后拖着一根长长的毛线,最后女人抱起了乔,安慰着他。
在字幕出现之前的这一开场白,似乎就展现了这个家庭以及乔最后走向欲望深渊的深层原因,卡特莉亚用嘴舔着乔光滑的身体,这是欲望的一种原始呈现,也预示着母子之间原始的性隐喻,但是在乔和强劲的音乐之间,她更倾向于音乐,也只有在音乐中她开始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存在,而把幼小的乔搁置在一边;而保罗作为父亲,几乎没有和乔有过直接接触,这是父子之间关系裂隙的一种证明,而且当时他的手上拿着刀,在一家原本充满温馨感的氛围里,刀子和充满腥味的鱼似乎预示着某种暴力,而他最后找到儿子的那记耳光,就是这种暴力的体现;而乔要离开对自己不关心的母亲和充满暴力的父亲,但是他的身后拖着一根毛线,就像没有完全独立的脐带,他的离开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成长是之后必然的寻找。
但是,这只是展示了乔和父母之间存在的断裂感,并没有解释卡特莉亚和保罗之间的分手,而这个答案似乎在最后揭示出来,在歌剧即将开幕的时候,乔找到了披着白色纱巾的卡特莉亚,在这之前,根据卡特莉亚提供的线索,乔已经找到了和自己母亲住在一起的保罗,“我们都在找你。”乔这样说,而保罗当时问乔:“我儿子呢?”乔的回答是:“他死了,但是他活在我心中。”或者正是这个答案使得保罗知道乔就是自己的儿子时,打了他一记耳光。而在乔面对母亲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保罗时,卡特莉亚说出了自己内心一直没有告诉乔的那个事实:“你长大了,像你父亲——你是我亲生的儿子,不要走你父亲的路,那会让我疯狂。”保罗走了怎样一条路?卡特莉亚的回答是:“为什么我跟你的父亲分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呢……他爱他的母亲。”
因为爱他的母亲,所以他们分开了,因为无法忍受这一点,所以乔缺失了父爱,很明显,乔缺失父爱的成长经历完全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他就是一个受害者,而当母亲这样说的时候,似乎也在杜绝一种恋母情结,但是在没有找到保罗之前,在乔陷入成长的困境时,卡特莉亚又完全自私地复制了这种母子之间的畸形关系,也就是说,当她以这样一个理由离开保罗母子,却在乔的身上重复了这样的悲剧——所以无论是“我的儿子死了”的保罗,还是用一记耳光换来成长的乔,他们都被卡特莉亚这个“母亲”所制造的欲望母题所伤害,尤其是乔,似乎从那一丝不挂的童年开始,就陷入到这个无力挣脱出来的困境中。
但是,贝托鲁奇似乎将卡特莉亚的这种母性悲剧淡化了,反而让她变成了“月神”,这一种赋神行为根本无法解决乔的难题,也无法为欲望寻找到一条合法化的途径,它甚至在隐秘的乱伦关系里成为又一个缺失的父亲。当然,贝托鲁奇指出了卡特莉亚作为母亲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个沉浸在音乐中忘乎所以的女人,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音乐,就是舞蹈,就是歌剧,“我的理想就是能走向国际舞台。”这是一种可以抛弃一切的理想,但是现实对于她来说则是:“我还没有实现就已经人老珠黄了。”说保罗只是爱自己的母亲,无疑也是一种自私的表达,所以在离开保罗带着乔的生活里,她和道格拉斯走到了一起,而这种组合似乎对于乔来说,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在开场那一幕充满隐喻的镜头之后,是已经成为少年的乔,而他身边则有父亲在,他们的关系看起来也比较和谐,只是他希望母亲在外面演出时,能带着他,但是卡特莉亚和道格拉斯都拒绝了他。
道格拉斯之死充满了神秘色彩,甚至匪夷所思。在他开车准备接送卡特莉亚出发,不想自己撞到了路边的围栏,当卡特莉亚急匆匆赶到现场,道格拉斯的头靠在方向盘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这是自杀?似乎在道格拉斯出场到自杀这一段情景的展示中并没有充分表露他选择自杀的原因,他和乔吃完早饭之后,和卡特莉亚说起了昨晚做的一个噩梦,但是因为时间原因他没有说出这个噩梦,希望在车上和卡特莉亚说,然后拒绝了卡特莉亚演出时带乔,然后走到了阳台发现了乔的一块球拍,然后倒了一杯酒,然后说到了关于中国的电视,最后一头撞死。在死之前的这些举动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预兆,有一种可能就是昨晚的噩梦,它缠绕着道格拉斯,它让他只能用酒来麻痹,最后因为喝了酒车撞到了围栏。但还有另一个可能,那就是当道格拉斯走向阳台时,发现了阳台栏杆下面一块已经干了好久的口香糖,他说这是“古物”,并骂着说:“肮脏的人,把口香糖到处扔!不可思议!”
阳台里的口香糖,曾经出现在贝托鲁奇的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里,当时的保罗走到阳台,拿出在嘴巴里咀嚼了许久的口香糖,然后黏在栏杆上。这像是一种电影的延续,但更多的是贝托鲁奇设置的一个隐喻,当时的保罗是预见了自己的死亡,所以他听到了枪声知乎,喊出了一句“我们的小孩”,然后失去重心地走向阳台,最后缓缓倒下,蜷缩成一团,像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寻找母亲的子宫。“我们的孩子”是保罗让自己成为孩子——男人和女人,母亲和孩子,出生和死亡,在无名的状态中,保持最后的仪式。而当这个情节成为一个由头,似乎在这里成为了失踪的父亲的隐喻,“我们的小孩”更成为乔成长的一个线索。
但是,这种延续还是显得有点牵强,道格拉斯和乔之间的关系没有被贝托鲁奇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当他死去,乔似乎彻底失去了父亲这个符号,所以他们的矛盾就完全成为了母与子的欲望母题。卡特莉亚整天在外奔波,根本无暇顾及乔的感受,她对乔的爱是机械的,也是盲目的,所以卡特莉亚是造成乔畸形心理的直接原因:乔变得神经质,乔开始注射毒品,乔开始远离正常的生活——在他的生日那天,他去找正在演出歌剧的母亲,而母亲以“你不要乱跑”为由批评了他,在这个属于自己生日的日子,反而得不到母爱,这对于乔来说,无非是笼罩于童年阴影之后的集中大爆发。
但是,卡特莉亚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采用了更加畸形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当乔出现异样的时候,卡特莉亚没有很好地用母爱却安慰和感化他,母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是呈现出对立,甚至是一种失去常态的对立:母亲说自己一生的理想就是歌唱和跳舞,乔却说“我讨厌跳舞”;母亲弥补的一场生日让乔邀请了好友参加,乔却躲在角落里撸起袖子开始注射;母亲自责太忙了,乔却打碎了物品,自己开始弹奏钢琴,母亲伸手去摸他,却被乔骂“你这个婊子”……在两个人之间,完全是各自破坏欲的呈现,即使最后卡特莉亚带着他去“寻找”父亲,乔也是自己开着车把母亲留在路上,而到了路边酒店,卡特莉亚又故意对载她的司机说乔是小流氓,而乔也毫不在乎自己的母亲竟然开始喝酒开始鄙视……
完全不正常的母子处理方式,让人看到他们一样的偏执一样的疯狂甚至一样的变态。而贝托鲁奇为了表现乔对于父爱的缺失,竟然用母亲来唤醒他的欲望并且用自己的肉体让他得到满足,这实在匪夷所思,似乎也曲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卡特莉亚得知乔开始吸毒之后,似乎幡然醒悟了,于是她开始体悟儿子的内心渴求,但是简单得将之理解为欲望,于是,她对躺着的乔说:“你真性感。”那天乔开始下厨做饭,卡特莉亚非常意外和惊喜,但是乔的厨艺很烂,在他灰心丧气的时候,他说自己偷她的钱买毒品,还说“你从来没有理解过我”,以为母子之间的隔阂会通过心理疗伤来化解,但是除了卡特莉亚去找提供毒品的穆斯塔法之外,似乎并没有挽救的措施,她甚至作为一个母亲像情人一样抱住他,当乔摸她下体的时候没有阻拦,乔靠在她胸前用头触摸她的乳房的时候,她也没有反对。
或许在卡特莉亚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恋母情结,并没有涉及到什么乱伦,但是当乔在路上顾自开车离开母子之后又重逢,在汽车旅馆里母子又发生了欲望故事,当时的乔躺在卡特莉亚的身边,卡特莉亚主动脱去了乔的衣服,然后吻他的后背,之后当乔用嘴舔她的脸的时候,卡特莉亚又用手自摸下体,沉浸在欲望的释放快感中。尽管他们显得克制,尽管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但这完全不是正常的母子关系,也不是所谓恋母情结的表现,而是在进入一种乱伦的状态。这完全将乔带入了一种歧途,似乎在卡特莉亚看来,乔注射毒品,乔丧失理性的行为,乔神经质的表现,甚至乔当初对女同学琳娜说“我想进入你的身体”,都是一种欲望受到压抑的结果,所以她要释放他的欲望。
但是,这种释放既违反了道德,而且也是一种误读。如果按照贝托鲁奇的思路,应该把这种性格的畸变看成是父亲的缺失,保罗离开了他,道格拉斯死去了,在只有母亲的生活里,乔本身就处在不正常的关系里,而且卡特莉亚和他的日渐疏远,让他离正常的爱越来越远,所以他首先需要卡特莉亚的拯救,所以她变成了欲望意义的月神,但是这种纯粹建立在肉体欲望释放基础上的赋神行为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逃避了关键原因,而当卡特莉亚带他去寻找父亲,并且最终找到了,只不过是一种符号的回归,这个打了他一耳光的男人能弥补乔缺失的父爱?父爱的缺失本来是夫妻之间的问题,但是当卡特莉亚说保罗太爱自己的母亲而离开,她对于乔的畸恋似乎又回到了循环状态。
自始至终,卡特莉亚没有试图改变乔的现状,没有试图付出真正的爱让乔走出迷局,欲望的“母题”只是母亲设置的一个幼稚命题,所以,最后的月神只不过是演出的聚光灯,最后的掌声只不过是安排好的形式,乔的成长也只是在贝托鲁奇的屏幕世界里成为一种传说。
2 ) 被遗忘的月神~
称Bertolucci为世界影坛的电影大师当之无愧,他是六○年代意大利新电影的领航者,以绚烂的影像和前卫的内容迷倒全球影迷,有不少人说,看他的电影就像是一场视觉飨宴一样赏心悦目。他的作品中混杂政治与情欲的手法是让他大受欢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972年那部马龙白兰度主演的<Last Tango in Paris>(巴黎最后探戈)推出时,像是往世界影坛掷了一颗震撼弹,片中直接的情欲探索,让他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导演;但也因此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许多「猥亵、色情」的负面批评随着众多赞许出现,甚至在许多国家都被列为禁片,但这却无损这部电影在影迷心中崇高的地位~经过七○到八○年代间的稍稍沉寂,贝托鲁奇以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传记片<The Last Emperor>(末代皇帝)达到事业巅峰,入围奥斯卡九项提名,也风光的拿下全部九个奖项,创下影史上的最辉煌纪录。紧接着贝托鲁奇持续炫目的影像与浓烈异乡风情的风格,推出在北非的<The Sheltering Sky>(遮蔽的天空)、在印度的<Little Buddha>(小活佛),就连以他家乡意大利为故事背景的<Stealing Beauty>(偷香)、<Besieged>(困境)里,都可以嗅到不同的异国味道.诸多奖项对于贝托鲁奇这位电影大师以及他超凡的作品来说,也只是锦上添花罢了~或许有很多人会因此把他归为那种擅长大场面调度的导演,但其实他骨子里,应该还是典型的欧洲导演,更注重表现人性的深层面.
这部<La Luna>是他继72年的<Last Tango in Paris>之后又一部因涉及敏感题材而引起轰动的争议之作,虽然在各大电影节广受好评,却因为影片中那对母子间的暧昧关系而遭到众多保守人士的笔诛口伐,这部影片在美国被禁至今,发行DVD的也就欧洲的两个国家~但论起影响力,却远远不及导演的其他作品,感觉这部片子在导演的作品表上被忽略了,反倒是我,因为那次在杂志上看到这部影片的介绍而印象颇深~其实我也很好奇,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影片,总想着有什么机会能一窥究竟.所以在淘碟时看到这部片子还是莫名兴奋了一阵~~~感谢D商啊,挖出这么难找的碟,不容易~
影片讲述了少年Joe在父亲死后,陪同身为女高音歌唱家的母亲Caterina一起赴意大利参加歌剧演出,却因为被冷落而染上了毒瘾,使Caterina分外心痛,对儿子的愧疚让她对Joe百般迁就,一种复杂的情感在母子之间蔓延.....最后Caterina从这种异样的情感旋涡中挣脱出来,并将隐藏多年的秘密说出,原来Joe另有生父,为使父母破镜重圆,Joe只身踏上寻父之旅......
看这部电影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实在不象是79年的一部电影!也许和DVD的影象修复技术也有关系,这部影片从始至终都洋溢着一种鲜活的生命感,就像一部新片一样,让本来以为会看到一部模糊粗糙的古旧作品的我惊喜不已;第二个感觉就是导演确实有两把刷子,每个镜头的运用都充满了情感流动的力量,能把就算放在今天还算是禁忌的题材在26前就表现的这么到位(联想到去年Nicole那部<Birth>,只不过是稍稍触碰到一点敏感的边就一片争议,就不难理解这部影片缘何被禁至今),不得不承认Bertolucci确实是很具有前瞻感觉的出色导演.影片一反常规,风格独具。浓重的异国风情,Joe的青春气息,Caterina的美妙嗓音,使导演在叙事手法上表现出跟过去相当不同的风格。
这部片子着意塑造了一个陷在成长困境中的少年Joe的形象,父亲的早逝令他提前品尝伤痛,母亲和旁人对他的陌不关心使他迷失在自己的世界中,但另一方面他的情感世界也是极为丰富的,他身上时刻都漫溢着青春的躁动,爱与被爱的不同情感几乎都交织在了他身上。如果说<La Luna>是一个感情磁场的话,那么,Joe无疑便是这一强磁场中的磁核了。 此外,该片在充分表现人物感情世界时,似乎也在探讨道德与人性,理智与情感间的矛盾和冲突,无疑是加深了影片的回味余地的,或许是同一个导演的作品,我总是有意无意的把它和03年的The Dreamers比较,一样举重若轻的镜头运用,平缓但震撼的情节设置,影片中的那些情感在导演的镜头下并没有让人有突兀之感,也是导演执导功力的体现之一.
这不是又一部<Lolita>,也不是另一部<Last Tango in Paris>,更不是一部简单的讲述俄底浦斯情结的普通电影,它只是将一个少年的迷惘,失落,成长的种种的经历忠实的记录了下来~~一部不应该被忽视的电影~
P.S.看完之后去查当时的演员,发现时间真是毫不留情...影片中扮演母亲Caterina的著名演员Jill Clayburgh现在已经60多岁了,早已不复那时的美貌~~而扮演Joe的Matthew Barry,当年拍摄该片时才17岁,现在也人到中年,难以找到当时那种青涩少年的感觉(照片就不贴出来了,说惨不忍睹也不为过...)感叹一下~不过能把自己的最好的年华留在电影胶片中,也许也是一种幸福吧~~
3 ) 母亲与父亲相遇的地方,即是《一九零零》里的故乡
一看到那农场,不就是哪张盖天红旗张起的地方啊! 农场主的豪宅原来就是威尔第的别墅。 而贝托鲁奇原来就出身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帕尔马,这里就是他的故乡,是他的童年记忆,他的精神骄傲,《月神》里的歌剧是威尔第的《费德尔》。贝托鲁奇对左派的激情印象是如《阿依达》一般壮烈悲情吧。 那么《月神》里的父亲,一个帕尔马人,是谁呢? “威尔第在自己的别墅里看到埃及,威尼斯” 原来那时期的贝托鲁奇是从家乡来看到世界,从家乡人来描绘阶级,来具象化共产主义的激情。 他对左派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其实和东方某国的同名词并不雷同,有强烈的个人背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激情宣泄,才是第一位的,而这几乎必然带来随后的流逝与幻灭。 于是当那时东方某国的只看到他张开了那面遮蔽天空的红旗时,他所痴迷的却是随后这张故乡的红旗与曾经的欢呼与呐喊逐渐向地平线远去。 《末代皇帝》本可能是贝托鲁奇电影谱系里的最另类,因为除了受邀在左派国家拍摄外,与他前后作品所关注的主题和人群相距甚远,但他还是通过溥仪和婉容发掘出了从期望到幻灭,既荒诞又迷梦的人生,这两个人物依然是属于贝托鲁奇的。
4 ) 啤酒瓶上的蛋卷
本以为这是一部很沉重的片子,直到最后一分钟也有这种担心,但是没想到是那样的结尾,很喜欢,想来这个收场可能是所有可能性里最精彩的了。
题目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觉得那家伙随手把蛋卷冰激淋插在啤酒瓶上真是神来之笔。
最惊奇的是居然看到了贝尼尼,只有一分钟的戏,却十分出彩。
5 ) "I want to understand you,I want to be inside you "
这部电影没有任何艰涩的成分,让人喜欢上的是一种漂浮于意义之上的东西.一种景象上的迷离和情感上的错位,或许每次看它,想起的都是人只有在青春期才能不受指责的进行的心灵的混乱.
母子关系的张力总是被一种优雅的姿态和生活的乐趣本身所柔化,这是对于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最为可爱的地方.永远不会出现真正的决裂和本质上的对立,一切都发生在深夜的意大利花园和绣满了龙的中国式长袍下,真诚的迷乱成了令人心醉的生活状态.
我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喜欢着它的轻浮,喜欢女主角无意识的绝望中的美丽面孔.欣赏着她在罗马的清晨中飘扬的蓝色衬衫和白色裙子.他们因为意识不到缺失的究竟是什么而盲目的在夕阳下的河岸上行走,亲吻彼此,并暧昧的沉沦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卡特林娜在木斯塔法住处的那段戏很有意思,一个毒贩也有着对于艺术的创造力和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让她感到一种姿态的尴尬.
同样喜欢那带着意大利口音的异常简单的英语对白,像脱离了两种文化的人在自己舒适美丽的孤岛上无所适从.
我曾说这是一部根源电影,它让我理解了母亲的溺爱中那我本不能理解的部分.一种遥远的缺失造就了人们彼此间几近盲目的需求,而很多时候世人将它误以为爱.
"我想要理解你,我想要进入你的身体"
"我吸毒,是因为我无所谓."
"对什么?对我吗?"
"你在说什么啊?我指对一切!"
"为什么我跟你的父亲分手?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说呢.......他爱他的母亲."
6 ) 影片最终考验的还是编辑、导演和演员.....
《欲孽迷宫》充满了令人不快的断背和反断背,以及莫名其妙的一夜情;而作为坊间名声最高的《母亲,爱情的限度》,整片都让我极其不舒服,母亲的疯疯癫癫,儿子的二了吧唧,配角的自以为是,都令人作呕。最后母亲死的时候,我竟然高兴的很,这个疯女人终于死了,《欲孽迷宫》的母亲死了有点可惜,而本片的母亲和儿子最后的归宿令人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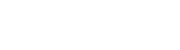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调度真是太喜欢了〜〜〜〜虽然看的是意大利语兼英文但完全不妨碍理解(☆_☆)有些激动
片头就是一个拉康的隐喻。第一个阶段,孩子依恋母亲,镜头表现是母亲亲吻孩子滴在腿上的水。第二个阶段,父亲介入并向孩子显示自己的权威,镜头对应母亲离开孩子去找他的父亲。第三个阶段,孩子始而认可父亲,从依恋母亲到转向崇拜父亲。戴爷的镜与世俗神话有过深刻的分析——贝托鲁奇的影片与其说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不如说是其背反。影片的叙事动力,不是对母亲的渴求,而是对父亲的渴望,与其说母亲成了儿子欲望的对象,不如说母亲只是一种媒介,要通过并超越母亲而得到父亲。
《巴黎最后的探戈》中,保罗临死前走到阳台,把嘴里的口香糖黏在栏杆底,然后死去;《月神》开场不久,乔的继父临死前也走到阳台,发现栏杆底粘了一块干了的口香糖,一边骂着一边把它揪出来。两次都用特写交代这块口香糖,是要把两部片联系起来—前者是男人对子宫的向往,后者是追寻母爱。
贝托鲁奇第一部不那么政治化的作品,处理的相当克制甚至唯美,内在的情感纹理细腻,调度和摄影给了这个稍显概念化的故事更强的张力,吉尔·克雷伯格对角色的处理很强的层次感,母亲是抵达父亲的一道桥梁。
其实我没太看懂,就是为了讲述一段变质情感…?过度的亲情溺爱,变成了混杂各种欲望的不伦感情……电影难懂…真晦涩……
有《遮蔽的天空》和《偷香》的影子。贝氏电影除了革命主题,总有关于躁动的青春,非常态的情欲和亲情。。。他的镜头里,再不堪的角色也出奇的美,女主角和拉尔夫费因斯很像。这样美的电影,居然被美国禁到如今,笑一笑质朴可爱的美国人吧
贝托鲁奇到此为止所有的片子都还在和爹妈较劲,以及,他是真的热爱威尔第啊
9/7/2006 2:15pm HKFA
好棒的片子!百合妈Jill Clayburgh简直了,那个时代的女神,身材非常好。
6/10。片头母亲安抚着戏水的孩子,随后切入俯冲的直升机闯入母子世界,父亲引诱母亲共舞落单孩子,儿子从剧院窗口窥视布景中月亮代表的母亲释放了童年欲望。同性恋矫正源于异性肉体和精神安慰,餐厅那场戏,母亲与载她的陌生男子调情报复,儿子敲打餐具捣蛋,对抗后以激情和解,两性关系转换不露痕迹。
弗洛伊德的俄普狄斯情节演绎,性是第一驱动力,不完全从男性角度出发,因为加上了母对子的欲望。儿童出生后意识产生前认为母子一体,但父亲夺走了母亲,让他意识到世界和他不是一体,所以他恨夺走母亲的父亲,使他想要杀死父亲而夺回母亲,占据母亲。对父带来的阉割畏惧,最终使他转而认同父亲,并控制对母的欲望,转向其他女人,开始自己人生。最后儿子和那个女孩坐一起算圆上结局了。就是用俄普狄斯在构建电影。妈妈像娜奥米沃兹,很美啊。
爱总是好的,只是爱有各种禁忌。
我总是觉得这个结局会更好点,结果我错了.一部根源电影,它让我理解了母亲的溺爱中那我本不能理解的部分.
奇妙的遗传基因,父与子共同的命运,都囿于母亲怪诞畸形的爱护围栏内,这样的畸恋像一条神秘、疯狂与病态的阴影,淹没于星夜月光下的人生之路上。
30年前就有这么大胆忌讳的话题,老贝的思维真是超前啊!
老贝年轻时候的电影总是会表达很多东西,不管是什么,都让人觉得奇美无比又心痛不已。La luna带我领略了歌剧之美、艺术与家人的不可兼得、美貌如花又深陷毒沼的孤独少年、母与子的“亲”与“疏”,还有父亲的缺失与归位…全都太妙了。要知道这些东西够其他人拍五六部的了,有的可能还讲不明白,运镜也不会这样行云流水,构图也不这样帧帧如画。有两场戏简直美到哭泣:一个是Joe在看意版配音梦露时,月亮是如何慢慢展开在他眼帘;紧接着Joe去剧场找母亲,看到工作中的闪着光辉的母亲,也让身为观众的我被歌剧深深震撼。另,母子二人路过的那是《一九零零》取景地吧,这彩蛋可真行(●´∀`●)
演少年的演员是女扮男装吗?
歌剧舞台天籁之音部分,并非克雷伯格的原声,全部采用哑剧模拟演出。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她来演?至少部分原因和主题有关。据说意大利制片人因为故事主线的内容而对贝多鲁奇大发雷霆,禁止他选角意大利本土演员。最后母子俩的扮演者都只能来自美国。但配合主题去看,所谓“对嘴”缺陷倒也说得通顺。因为故事讲得正是父权缺失子悲迷失的危害!与母权为伍的音乐元素(钢琴和歌剧)在片中似乎无法充当褒义……不过影片自身似乎也存在着某种“父权缺失”:显性而强烈的政治元素,贝多鲁奇电影最重要的戏剧高能来源之一。重要缺位之下若能短小精炼或可掩盖不足,偏偏长达了一百四十多分钟?所以呢,也就这样吧。
迷乱、疯狂、忧郁,贝托鲁奇呈现的一对母子之间的情感战争背后却是一个寻父的主题,但抽离掉表面的剧情,电影真正想要表达的其实也是贝托鲁奇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身份”,异域之中、他者之外的我究竟是谁呢?儿子的美国身份,在意大利他迅速依靠滑板、毒品等美国元素来构建自我,但母亲时刻提醒他这不是他的真我,所以他依赖这段亲密关系又想斩断它,母亲努力构建的"两人“的世界也终究镜花水月,因为占有和隐藏本身就是罪恶的,她不惜突破伦理与道德的”拯救“就变得如此地尴尬,儿子终究不能将丈夫的身份兼顾,而她也终究不能兼顾起父亲的身份,月亮与太阳同在的世界才是完整的,儿子需要找到身份的最后一块拼图,母亲需要与自私和记忆和解,贝托鲁奇使用了大量的情绪化的场景来刻画自由的焦虑,人物的抗争也是隐喻着当下被割裂的世界的孤独内心吧
7.3/10 其实不错。但主要是“收”与“放”的问题,这部片中的疯癫过程非常精准和理论化,客观来说完成度很高,不过剧情也因此显得设计感太强和死板,让我很难主观喜欢。做两个比较:一是前作《同流者》,同样有大框架,但那部作品的框架规定了在哪收在哪放,该放的时候形式跟内容一起放,也很工整但完全不失力量,那时伯纳多也年少轻狂形式很大胆让人喜欢;另一部是《春光乍泄》,也是神经质的关系,但完全的放,完全的随意,有很多日常化的东西但指向和符号也没有丢。这部有点像哈内克,把人憋死,但本片事实上缺少向外的力量,最后的重聚只是符号意义上的完成,没有足够的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