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无尽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非凡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剧情介绍
歌舞伎世家音羽屋第六代传人尾上菊之助(花柳章太郎 饰)苦恼万分,父亲菊五郎(河原崎権十郎 饰)对他的演艺功底大为不满,耻于称其为自己的传人;师兄弟和观众们也对他的评价颇差。然而这些人又都当面奉承,虚情假意。周围只有女佣阿德(森赫子 饰)敢于当面指出菊之助的不足,并真心希望他的表演能不断精进。阿德的诚实令菊之助大为感动,心中视其为难得的知己。 但他们的友情却遭到身边人的猜疑,阿德被辞退回家。伤心的菊之助四处寻找,并决心不顾世俗的眼光娶阿德为妻…… 本片根据村松梢风同名小说改编,1939年电影旬报年度十佳评选第二名。老友鬼上身移民国度你和我XXX唇齿之间 第一季武神黑侠信徒X巴黎陷落怖谷鸟2024拔哥的故事锦绣前程1945谎言中的爱警部补碓冰弘一MIND罪恶天使少男奶爸第四季林海雪原再见夏天演员攻略之隐形恋人笑脸杀人狂小城故事多鬼同你有缘之阴尸路有泪悄悄流邻家律师赵德浩信守情洒虎度门玉钗盟我怕来不及水浒传1998月之暗面第一季极主夫道 电影版红线铁拳男人英语不能结婚的男人怪兽屋我的三个母亲双凤奇缘大上海1937守护黑面琵鹭侠僧探案传奇之开封府江山美人(2008)焚海的人妖狐传地狱之轮 第一季风云战国之列国午夜怪谈失踪:他们存在过人骨麻将粤语脆弱的英雄莉香:自称28岁的纯爱怪兽
长篇影评
1 ) 感受鼻祖级的诚意
这部年代久远的电影呈现出了最原始的诚意,镜头、演员、故事背景的营造都是仔细斟酌且看得出是专注度极高的。
就如故事里的艺能世家,带有使命感一般去认真的构建出一部艺术作品,看得耐人寻味。
后世的很多作品的细节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影子,毕竟是属于鼻祖级别的作品,如今在影院中看到4K修复版,实属荣幸~
2 ) “妾当如蒲草,蒲草韧如丝”
〈残菊物语〉讲述的一个歌舞伎世家的第六代传人菊之助和仆人德的爱情故事。
菊之助作为一个星二代,即使演技不好也受到了周围人的恭维,面对别人的口是心非、虚情假意他非常苦恼,但是这时候德勇敢的站出来指出他演技的不足之处,说了中肯的建议,这样的一番话让菊之助醍醐灌顶,他将德视为知己。
然而尊卑有序,在当时的日本他们的感情不被世俗接受,于是菊之助和德开始私奔,过着贫穷又艰难的日子。
两个人相依为命,菊之助琢磨演技,德在这段日子里为了维持家计积劳成疾。再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德向菊之助的家人求情,给他争取了一个演戏的机会,从此菊之助一夜成名,名声大噪。
最让人感动和悲哀的是事情是,德在这个时候离开了菊之助,直到她临死之前菊之助才能找到她,看了她最后一眼。
总的说这是一个有关于“奉献”的悲剧讽刺故事,在男尊女卑的时代,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奉献了一生,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成全了他的名声威望。
里面的女人让我想起来“妾当如蒲草,蒲草韧如丝”,蒲草虽然柔软纤细,但是坚韧顽强,无论有什么困难她都没有放弃,一直都陪在菊之助的身边。
整个电影下来最美的镜头就是菊之助和德在河沿上散步聊天平移的长镜头,经典的黑白画面,搭配上叫卖声,风铃声,两个人慢慢的走在夏日的夜晚,迷人的就像是一幅长画卷。
3 ) 一个伟大女性的牺牲
菊之助为何总不成器,我真没脸跟大家说这是我的后继人!”通道上的弟子们也议论纷
纷:菊之助的表演实在太差劲了!松助却劝菊五郎不要对菊之助过于严厉,免得别人说
他有了亲儿子就对他冷淡起来。
众人说话间,菊之助进来了。菊五郎怒火顿起,但想了一想,又压下怒火说:“不
错,你演得不错。”
走出后台,福助和通道上的师兄弟又言不衷地对他的表演随口称赞了一番。
出了新富座,菊之助坐上人力车直奔招枝酒馆。隔壁房间里刚听完戏的客人正在闲
谈。他们赞赏着菊五郎的演技,却轻蔑指责菊之助不过是靠梨园界他那个音羽屋的家门
在受人奉承。菊之助如坐针毡,赶走正抢着上来献殷勤的艺妓,悻悻地回家了。
他闷闷地回到家里,使女阿德正哄着他的弟弟小幸。一见面,她就对他说:“今天
我头一次看到了少老板你演的戏。我在浅草家听人说少老板演得太差了,心里很不痛快,
回来就去看了戏。”
“演得怎么样呢?”菊之助冷冷地问。
“少老板,我不怕你生气,我以为你应该好好学艺,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菊五郎的继
承人。”
菊之助的心颤动了。他感谢阿德当面跟他说出了真话。两人谈说着走进了院内,一
个女佣看到这副情景,露出了奇异的神色。
真诚的友谊从此开始建立。他们的接触加深了。月光下,菊之助望着抱着小幸的阿
德感慨地说:“人们当着面都信口开河地奉承我,推心置腹善言相劝的只有你一个人。
我听到你的话,就像奔走在炎热的山路时喝到冰凉的山泉……”阿德满含热泪深受感动。
她喁喁地鼓励着他。
菊五郎、松助都感到菊之助用功多了。可不是,今天那么好的烟火他都舍不得跑出
来看。但站在一旁的女佣却悄声对菊五郎的夫人里子说:“太太,阿德今晚也没有出来
吧!……”里子心头猛然一惊,立刻阻止不让她胡说。
第二天,里子把阿德叫到身边,用阴森森的眼神瞪着她,毫不留情地把她辞退了。
菊之助得知阿德是因为自已被辞退,立刻赶到浅草阿德家中去。阿德已经搬走了,
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她。
“好不容易找到你。因为我连累了你,我难过极了!”菊之助一见面就歉疚地说。
阿德见状,眼泪禁不住潸潸流下。但她恳求菊之助以后别再跟她见面,免得人们捕
风捉影说三道四。这样他便会在音羽屋这个家门呆不下去的。但他却坚决地说:“没有
什么可怕的,阿德,我已打定主意要娶你做妻子!”
回到家里,菊之助又与养父母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菊五郎怒斥他不用心学艺,
却把精力放在使女身上。里子更讥讽说阿德是因为菊之助将要做继承人才接近他的。菊
之助听后忿忿不平,他说,“只有阿德才说实话,有了她我才感到演戏起劲儿。我们的
行为清清白白,你们却把她一脚踢出门去。她蒙受不白之冤,太可怜!”
最后他表示自己不想靠老子的虚名,也不需要第六代的传名和音羽屋这个家门,而
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干。一席话说得菊五郎大发雷霆,把他逐出了家门。
走投无路,菊之助决定到大阪投靠多见藏老板。在那里,他的演技仍不见长进,尽
管多见藏颇有见地地竭力鼓励着他,但他再也见不着阿德,始终心灰意懒提不起精神来。
一天傍晚,正当他站在后门口茫然无绪地望着迷蒙的夜色,心中涌起了一了百了的
念头时,阿德竟提着包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听到少老板的演技得不到好评的消息,放心不下,我终于跑来了。”阿德掩饰不
住内心的激动,看到他一副悲戚的样子,又鼓励他不要泄气:“艺术在于自己对它的态
度,你要挺起腰来!”
菊之助把她带到自己居住的元俊叔家的小屋。房间里简陋寒酸,零乱地堆放着一些
戏装、道具。他需要有人照顾呵!于是她不顾羞涩,毅然表示自己愿意留下来。菊之助
兴奋地喊道:“阿德,我早就把你看作我的妻子啦!”
日子过得充实而又甜蜜。阿德操持家务,菊之助潜心学艺。她为帮助他演好戏,还
卖了自己的东西买了一只梳妆台。然而好景不长,多见藏老板这时忽因急病去世,剧院
顿时冷落下来。经理精简人员,解雇了菊之助。他不得不与串乡戏班订立合同,从此流
落江湖……
整整四年!东奔西荡的生活消磨着菊之助的志向。他开始为多赚几个小钱争角色,
他认为给不懂戏的观众演戏,没有必要正儿八经地念台词。阿德深深为他担心。
有一次,菊之助在台上连台词也跳着念。阿德痛切地批评了他,菊之助烦躁地与她
争吵起来,竟挥手打了她一耳光。阿德虽万分伤心,但还是情意深深地劝慰他说:“我
知道在这种戏班里委屈了你。你心情不好,可戏是一样应该演好的!”
菊之助的心又一次颤抖了!他激动地喊着:“阿德!”向她表达了内心深深的感激
和歉意。
串乡戏班终因经济拮据而散伙,阿德也积劳成疾病倒了。但为了使菊之助不至于中
途辍艺,她仍决定拖着病弱的身子去求正在名古屋上演的福助他们。
她向福助述说了菊之助多年来的辛苦锻炼和艺术长进,恳请他们在这关键时刻给他
帮助。福助被她的精神感动,当下一口答应,但他提醒她说,倘然菊之助演出成功回到
音羽屋家门的话,她就不得不与他就此分手。阿德听后含泪说道:“我是打定了主意才
来求你的!”
菊之助来到了名古屋舞台。散场大鼓响起,台下一片掌声。他的演出终于成功了!
没有谁比阿德更加激动,她跑到他的面前热烈向他祝贺:几年辛苦终于没有白费,他总
算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回东京去了!
夜里,大家在忙乱中上了回东京的火车,阿德却在这时给菊之助留下一封信,悄悄
地离开了……
菊之助与菊五郎、福助在东京同台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菊五郎兴奋地向公众
承认菊之助为音羽屋家门第六代,并宣布剧团到大阪巡回演出。
在大阪,元俊叔跑来找到了菊之助,向他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阿德病得很厉
害,却一直不让告诉你。大夫说她过不了今晚了!”菊五郎在旁边听到,向菊之助开了
口:“阿菊,去看看你的老婆吧!你能有今天,全凭阿德不惜身心交瘁地鼓励你、帮助
你呵!就说我向她致谢!”
两行热泪再也止不住从菊之助脸上落下。
赶到元俊叔家,阿德已奄奄一息,正处于弥留之际。菊之助一把搂住她,喃喃地述
说着对她的思念,并告诉她爸爸已承认了这门亲事,是他让自己来看她的。
薄暮时分,乘船仪式开始了。河面上九艘挂着灯笼的大船依次排开。第七艘船上坐
着音羽屋门下的弟子们。河道两旁人山人海。菊之助站在船楼上,面对欢乐的人群,想
起阿德,黯然神伤……
这时,元俊叔家二楼上,阿德含着微笑,溘然长逝……
4 ) 沟口健二含蓄婉转的“侧”描美学浅析
今天是日本影史最伟大导演之一——沟口健二诞辰122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一辈子在作品中为女性发声的电影人。

如果只用一个字来概括沟口健二的电影,非“侧”字莫属。由题材至运镜,从构图到氛围,无不透现着一种含蓄而婉转的“侧描”美学。
沟口健二的作品,大抵以女性作为主人公,涵盖古今时空,历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与苦难。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大部分女性都逃不出失去自己的“正面”、沦为男性的“侧面”的宿命——在家庭里,她们唯有“侍奉在侧”,以便扶立出男人的“光辉正面”;在社会上,她们只能自愿或非自愿地成为男性的玩物,遭侮辱,受损害,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一侧。与旧日女性命运相一致的是,在沟口健二的电影中,最常出现两类女性形象:一种是为了身边的男性而自我牺牲、默默奉献的卑微女性。另一种则是迫于生计以艺妓或妓女为职业的女性。

第一类女性形象,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残菊物语》(1939) 中的女佣阿德,在其他人一面夸赞歌舞伎世家传人菊之助的演技时,只有她敢于直接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菊之助由此对她好感大增,两人日渐亲密起来。之后,由于风言风语与菊之助父母的反对,阿德被辞退,她便不再与菊之助见面,生怕影响他的前程。菊之助一气之下决定和阿德私奔,寻求自立门户的机会。他们先投靠了大阪的剧团,阿德日日赶工针线活维持生计,并卖掉了自己值钱的东西,只为了给菊之助买一个排演化妆用的梳妆台。但好景不长,剧团老板因病去世,菊之助遭到解雇。两人只得跟着一个巡回剧团走了。此后整整四年时间,菊之助都只能做一个串乡的流浪艺人,阿德则不离不弃,忍受苦厄,全力照料着菊之助的生活。然而,巡回戏班经理突然跑路,阿德也因穷困和劳累患上了肺病。这时,二人得知东京的剧团要来名古屋演出,阿德便独自向剧团老板求情,老板终于答应给阿德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而他提出的条件正是阿德来之前已下定决心答应的——若菊之助演出成功,阿德就必须与其分手。最终,菊之助因其四年中的艰苦磨砺而大获成功,他的家人也终于接受了阿德。但就在剧团举行庆祝仪式的那天夜里,阿德溘然长逝。为了菊之助的事业,她就这样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其他典型的角色还包括《白绢之瀑》《折纸鹤的阿千》中为爱人不顾一切直至死灭的女主角,以及《山椒大夫》(1954) 中为了让哥哥成功逃出奴隶主掌控而自尽的安寿。

与此同时,沟口健二也拍摄了不少描写艺妓或妓女的电影,如《夜之女》《谣言的女人》《祇园歌女》等。这些女性大多也是善良而温润的形象,但也有例外,《祇园姊妹》(1936) 讲述了一对艺妓姐妹花的故事,姐姐看重情义、温柔忠诚、逆来顺受,但妹妹则圆滑老道、自私而精明、不重感情只看钱,但纵使如此,她也依旧没能挣脱出传统男权社会的网罗。沟口的遗作《赤线地带》(1956) 则是一幅饱含深情的青楼群像谱:五位妓女身上汇集了多种苦难,无论是为了生病的丈夫、债台高筑的父亲、生活拮据的儿子还是离家争取自主权,每一位女性似乎都注定要历经蹉跎,在误解与歧视的淤潭中泥足深陷。

这两类苦楚的女性角色,都凝聚到了《西鹤一代女》(1952) 的女主角阿春身上。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似乎注定要承受无数女性的所有苦难,但心灵却终究纯澈。影片中,阿春一共经历了十个阶段的创痛:因与“下等人”的亲密关系而被驱逐;被领主选为妾并当作生殖工具,用完即弃;被父亲卖入高级妓院,遭遇制造假币、自认“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骗子;得以赎身后去做女佣,却逃不过闲人的蜚短流长、太太的嫉恨(女性压迫更弱势的女性)与男主人的好色;在阶段5,终于和开扇子店的忠厚男子结婚,但不久丈夫却死于非命;入寺为尼,却遭男人索衣纠缠,被侵犯后还要被逐出庙门(性侵受害者反被污名化);被偷走主人钱财的男人强迫私奔;沦为街头妓女,被老男人们当作反面教材嫌弃与嘲弄;贫病交加中被新当上领主的儿子收留,却被其视作耻辱,失去人身自由;最终九九归一,再入佛门,流浪化缘终老……世事变幻无常,唯有女性的悲怆命途永无尽头。

与黑泽明对剪辑的倚重不同,沟口健二特别偏爱长镜头。他认为,一个场景最好只用一个镜头、一气呵成地呈现出来,即“一场一镜”的美学风格。我们知道,另一位日本大师导演小津安二郎也常常使用长镜头,但在小津安二郎中后期的影片中,几乎看不到镜头的运动,摄影机全程保持固定机位,凸显出一个“静”字,东方式宁谧而质朴的气息渗透其中。与此相比,沟口健二的电影则兼具“静”与“动”的魅力,既有近似于小津的“榻榻米机位”静止镜头,又不乏游移慢摇的运动长镜头。而最为人称道的标志性技法,当属沟口独创的开放时空观——在单镜头内无缝变换时空(这一修辞策略后为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发扬光大)。在《雨月物语》(1953) 结尾,“男主角回到了历经战乱的村庄,此时,他的妻子已经被杀死了。在前一个镜头中,男主角走进空无一人的废弃的旧房子,当镜头跟随他摇出房间再摇回来时,我们看见他的妻子居然坐在屋子中央,正在生火做饭......在下一个固定镜头中,妻子坐在门前缝衣服,时间是晚上,过了一会,我们看见阳光从门缝里射了进来。一个镜头就完成了晚上到白天的转换。”[1] 摄影机就这样在缓慢摇移中打通了时间的壁垒,虚幻与现实如此暧昧而迷离地交织在一起。
另一方面,沟口健二的长镜头往往以远景和全景为主,极少使用特写镜头(这一点又与黑泽明的电影大相径庭)。摄影机默默远观着世间百态,配合渐次横移的运动镜头,恍若一幅徐徐铺展开来的卷轴画。人说,沟口的长镜头就像河流一样漫长、悠远,缓缓流淌。这是一种十分含蓄、间接、优雅的镜头语言,流畅自然,并不炫技(不特意观察,你甚至感觉不出运动长镜头的存在),技法只是悄悄推动着叙事,镜头运动与故事演进融于一体,实属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构图上,沟口健二也喜欢婉转侧视的方位。这一点在《残菊物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拍摄室内戏时,摄影机多与门框或墙面构成约45°的斜角,不同墙面间的交界线常居后景中央,纵深感极强,这种面向侧方的斜角构图与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的正面垂直或平行的构图迥然不同。例如,在小津的代表作《晚春》(1949)和《浮草》(1959)的大部分镜头中,摄影机均垂直正对着门、窗或墙面,换句话说,银幕画面与门、窗或墙的所在平面保持平行。而在黑泽明的《用心棒》中,几乎所有镜头都处于垂直机位,无斜角,从而营造出删繁就简、大开大合的美感。此外,沟口健二电影中的人物也大多不会正面朝向镜头,而是侧对摄影机,这也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垂直或平行于墙面门窗坐卧,很少会长时间斜对着它们。室外戏方面,偶有近似中心对称或垂直纵深的构图,其余时候以街道上的横摇跟拍长镜头为主,人物在大部分时候同样保持着侧对摄影机的位置。

非对称、非平衡的构图也贯穿于沟口健二的作品序列,尤其是远景中的门框镜头:摄影机同样斜对着门框,且常常是一边门框位于画外,而另一边不仅门框在画内,还遮挡住了画面的一部分。这种前景被半遮掩的构图,亦与影片中半隐半现、半遮半露的门帘、纱幕或屏风相得益彰,凝结成独属于日本古典内室设计的朦胧美学。此外,在转场方式上,沟口健二钟情于叠化或门廊镜头。叠化使时空的转换变得柔和而平滑,而室外的门廊镜头(即正对着某一通道或门廊的不完全对称构图,角色在其间行走)也不失为一个缓缓过渡的方式。凡此种种,皆构成沟口健二间接而含蓄的影像风格。

这一影像风格的另一组成要素,便是一种水汽迷蒙的画面氛围,一种似雨似雾又像纱的氤氲之美,一如沟口名作《雨月物语》的雾中泛舟场景,如此朦胧而沉婉,不由得让人想及秦观的词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其后的《近松物语》(1954) ,亦有在雾气弥漫的湖上泛舟的段落,如梦似幻。即便没有类似场景,沟口健二的不少电影仍浸染在一片朦胧的气韵之中,再配上全景或远景的调度,你甚至常常看不清人物的面容。好在沟口的故事并不复杂,人物关系分明,所以倒也不会辨识不清。

与这种迷离而婉转的气息相契合,沟口的作品中也总有适度的留白与画外空间。以《山椒大夫》为例,影片中多次出现奴隶主用烙铁惩罚逃跑未遂的奴隶的场景,还有挑断脚筋的段落,而受难者均处在画外,我们未曾亲眼目睹这一惨象,唯有凄楚而痛苦的尖叫犹然回响在耳畔。影片中另有一个唯美而伤痛的段落:竹林掩映,雾气弥漫,昔日母亲凄婉的歌声萦绕耳边,为保哥哥逃亡成功的妹妹安寿决意自尽,缓缓步入湖中,及至画面一切,徒留几圈涟漪泛起。

不过,沟口健二的美学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渐次演进出了多种变式因素,几曲变奏愈发交缠期间。比如,沟口电影中的舞台剧场景,往往并不遵守“一场一镜”的旨趣,反而会从多种角度拍摄,切换不同机位。毕竟,若坚持使用固定长镜头来呈现舞台剧,未免有些过于原始和单调了,无法发挥出电影的多样性。
此外,沟口的“一场一镜”和婉转的侧描美学在1930年代时便已成型,在《残菊物语》中呈露得最为纯粹完整,但在后期作品中,这一风格一定程度上被削减、弱化了。剪辑的频度逐渐提升,大景别镜头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特写与正反打崭露头角。构图上,斜侧方与非对称不再是颠扑不破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不少正面和对称的构图。在他的遗作《赤线地带》中,连配乐也变得诡异古怪,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或许,这也和这部影片的现时性有关——直接反映二战后日本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若完全沿用旧有的含蓄美学,容易显得不伦不类。

最后,沟口健二的作品中并不缺乏直白、直露的台词,他经常给予人物控诉时代体制的机会。早在1936年的《祇园姊妹》中,身为艺妓的妹妹便多次道出女性完全受制于男性的社会境况。《西鹤一代女》里的下等武士因与贵族家的女佣相恋,被处以死刑,在引颈就戮时高声道白:“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所有人能不分地位的自由恋爱。” 《山椒大夫》中爱民如己却遭贬谪的男主人公不断叮咛儿子:“没有了怜悯心,人就会成为野兽。就算自己再困难,也要宽怀待人。人生来平等,每个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
这也正是沟口健二的可贵之处:纵使孜孜以求含蓄蕴藉的东方古典美学,他也不曾压抑直抒胸臆的愿望,不断呼吁着不同性别、不同阶级间的平等互爱。无论拍摄风格如何演变,他也没有失掉为饱受磨难与不公的女性发声的初心。
注释: [1] 康迪,安哲罗普洛斯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5
首发于公众号【冰红深蓝电影】,一起看佳片,赏经典~

5 ) 牺牲
沟口健二最后还是让阿德死了,如此苦难又伟大的爱情依然没能相濡以沫。爱情的悲剧远比喜剧更有力量和反思性,沟口从始至终都在秉承这一理念。《雨月物语》中死去的妻子,《近松物语》中赴死的恋人,《西鹤一代女》中被杀的丈夫。到了此片,两个身份地位悬殊的恋人同样最终阴阳相隔。
歌舞伎世家音羽屋第六代传人尾上菊之助并不是一个演艺功底优秀的演员,父亲菊五郎对他的演艺功底大为不满,耻于称其为自己的传人,师兄弟和观众也对他的评价很差。但因为菊之助的身份,这些人又都当面奉承,虚情假意。在菊之助身边的所有人中,只有女佣阿德敢于当面指出菊之助的不足,并真心希望他的表演能不断精进。影片中阿德与菊之助在演出结束后,两人结伴一前一后在路上由左向右行走时,阿德真诚的告诉了菊之助他的不足。这一段横移的运动长镜头让人印象深刻。菊之助很感激阿德的真诚,并且慢慢对阿德产生了情愫。但由于身份地位的悬殊,菊之助的父母告诫他不要被阿德欺骗了,并且背着菊之助将阿德辞退了。菊之助不希望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于是去了另一个城市打拼,在那里他遇见了阿德。他们相恋并最终走到了一起。但演艺生涯的平庸让菊之助慢慢变得消沉,抑郁。在这样的人生低谷时,阿德始终陪伴在菊之助身边鼓励和鞭策他。最终,努力打磨技艺的菊之助获得了事业上的认可和荣誉,可当他带领着演出团队在热情的群众间游行时,阿德却病死在了家中……
影片最后菊之助在狂欢的人群中和阿德孤独的躺在病床上的平行蒙太奇深深的加重了影片的悲剧气质。沟口电影中的女人永远是默默奉献并承受着生活中的恶意,无论是被礼教吃人,被抢夺,被侮辱,被杀害还是病痛折磨。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弱势和卑微始终是沟口在表现的主题。此片中阿德为了菊之助事业成功后能回到父亲身边而主动离去,因为她怕菊之助的父亲不能接受她和菊之助在一起,这种女性的牺牲精神和为男人付出一切的勇气也是沟口作品里最动人的旋律之一。
6 ) 当他拍摄电影时对那受到女性宽容而感到非常幸福的心情瞥上的一眼
《残菊物语》的剧情并不复杂:19世纪末的日本戏剧界,男主角菊之助是支配歌舞伎界的家族的第六代传人,是最有望成为第六代菊五郎的人员,也是第五代尾上菊五郎的养子。他的演技并不成熟,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备受赞誉,而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中菊之助忘乎所以,终日沉湎于游狎艺伎,几乎要荒废了技艺。但是人们慑于他的家族地位和他的身份不愿提出忠告。
就在这时前来尾上菊五郎家中照顾尾上菊五郎亲生儿子的女佣阿德出于对菊之助的爱护直言不讳地对菊五郎的态度进行了批评,菊之助则因为阿德这样的直率、勇敢而感动进而爱上了她。很快两人相爱的事情招致了闲言碎语最终传到了菊五郎夫人的耳朵中,最终菊五郎夫妇将阿德解雇,原因是阿德低下的身份引诱菊之助败坏了家风。
菊之助则不在乎这些原因,也不愿意听从家人的劝说执意去寻找阿德,也因此被赶出了家门。此后菊之助也无法在东京歌舞伎界找到工作。因此菊之助来到了大阪,并开始在尾上多见藏的庇护下台上演出,而由于其技艺不娴熟被观众嘲笑,而失去了家族名声庇护的菊之助也只能勉强登台,尝到了人生百味。此时阿德从东京跑来,与菊之助共患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尾上多见藏突然病故,菊之助又一次失去了保护伞,无法立足于大阪的歌舞伎界。
最终菊之助只得加入乡间巡回演出的剧团,不过在阿德的鼓励之下菊之助的技艺开始有所提升。然而在旅行途中菊之助所在的剧团因破产而宣告解散,而这时菊之助正巧听闻东京的歌舞伎团来到附近的城市演出,阿德便去活动让菊之助能够有演出的机会。而菊之助的技艺在阿德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有了极大的提升,在演出后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剧团也向菊五郎提议请求让菊之助返回东京的剧团,而菊五郎开出的条件则是菊之助必须与阿德分手,而这个条件只有阿德知晓。
就在菊之助搭乘开往东京的火车时,阿德悄悄地回到了大阪,住进了那个两人曾经一同患难的公寓。在菊之助知道真相之后也无济于事,此刻他已经成为了东京炙手可热的演员。
几年后,东京歌舞伎剧团来到大阪演出,菊之助已经成为了最负盛名的演员,在演出前夜菊之助与菊五郎在大阪护城河上接受群众的欢呼。在路过那所公寓的时候,公寓管理员匆匆跑来告诉菊之助阿德病危,就在这时菊五郎也承认了二人的婚姻,然而为时已晚,阿德在听到群众对菊之助一行人发出的欢呼声中与世长辞。
1930年代的沟口健二与小津安二郎是当时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导演,在10年前则是山中贞雄、五所平之助和成濑巳喜男等导演的天下,沟口健二在小津5年前执导影片,通过1920年代40多部影片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早期作品中沟口健二大量学习世界各地的风格,直到1930年代才被认作重要的日本导演,而这部1939年的残菊物语是沟口制作最为精良的沟口健二美学、风格、主题的集大成者,当然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首先从主题来看自然是一贯的充满社会批判的对于女性的同情(而小津则是当时庶民剧的代表人物),而在本片中的阿德又与他早期塑造的一般女性形象有所不同,在阿德主动与菊之助分手时阿德说“跟那样的男人在一起,实在没有意思”,在本片中更是抒发了一定的愤懑情绪,阿德作为一位非常特殊的女性直言不讳地对菊之助的技艺提出批评结果遭到了菊五郎一家人的怀疑与辱骂,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德也没有抱怨,而在离别时刻也是如此决绝并且在一系列事件的铺垫下形成的是一种充满愤懑的心绪,所以表面上本片是一部赞美自我牺牲的恋爱悲剧,但是这是一首以假装失恋来确保女性尊严的歌颂女性胜利的凯歌。
而这种自我表现反而使得本片呈现出对于阿德的竭力压制,阿德的行为成为了为她主人一家效劳、对于男子主义社会阶级歧视社会的肯定,这反而抒发了一种更大的悲剧性与讽刺性。因此《残菊物语》的成功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讲述了一部俊男靓女由于门不当户不对导致的恋爱未果惨剧,而是通过一种悲剧性的讽刺:这样一个存在歧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之中诞生的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之中被压迫最残酷的往往却最容易表现出对这样体制的忠诚与维护。当我们看到阿德迸发出那样的光辉时作为一个永远躲在身后的男主会感到幸福吗?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傻福。
而这样的傻福也一直在本片中延续着,沟口的电影之中不乏这样的女性通过自我牺牲令男性享受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傻福,沟口健二以锐利的笔触扩大化地呈现这样的一种行为批判了这样的社会与男性心理。本片中的阿德与菊之助的对比经过了一系列变化:由“女性献身于男性赎罪的对比”到“女性觉醒与男性利己主义对比进行抨击”最后到破罐破摔式呈现的“男性沉湎于女性献身的阶段”以达成巨大的讽刺与批评。
当然,本片中充满了沟口健二式的美学风格:采用远景镜头展现高度紧张的场面,尽量减少展现某个人物的反应,例如阿德前往福住老板家游说时完全避免了阿德的正面特写镜头,将她背对观众,利用固定长镜头,通过这种“非戏剧化”的方式令观众减少对于这类题材的情绪化反应,达成一种理性的效果,沟口的大量固定镜头较少移动,也迫使我们观看着以一种无情步调展开的痛苦的自我牺牲行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远景固定长镜头也令我们思考:为何这样的女性需要受到这样的苦楚。
并且本片中大量使用戏剧化的敏感对比照明,甚至经常将阿德没入黑暗之中使其偏离视线中心,在通过强迫观众巡视画面找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动作令观众主动地发现这样的自我牺牲的行为同时也暗示了阿德这样的女性在文本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整部影片之中却又是毫无意义轻易就会被抛弃的角色,表面看上去是阿德通过游说等一系列行为令菊之助享有“傻福”,而在影片中有时阿德甚至毫不起眼,正是这样与观众的互动更加凸显出本片感性的同时又赋予其理性,在被剧情打动之时也有审视本片的社会批判的意义。
而在本片中也并没有缺少对于父权社会的批判而不仅限于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对菊之助的讽刺,菊之助也是一个可悲可恨可怜之人,毫无自由可言,似乎在那样的境况下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只能”享有这样的傻福,他既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也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而这样的享福是好是坏自有观众进行评说与思考(非共情)。就在1939年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几乎所有产业都为日本战争服务,同样也包括电影产业,在那样一个分不清是全民疯狂还是政府疯狂连带百姓受苦的年代,几乎所有日本导演也不能免俗的加入了部队为战争服务,也出品了不少有关作品,我们也可以说或许日本从未离开过19世纪末那样的社会,政府逼迫那时的这些导演们以“自我牺牲”的心态为“大日本帝国”的崛起做出贡献并且还能成为美谈,而他们究竟是被那样的社会驯化服从于那样的军国主义思潮状态亦或是如同阿德一般的存在?这样想来本片甚至有些令人细思恐极。幸运的是这些导演大多都存活了下来在战后拍摄出更多具有反思性的作品,令我们得以一窥在战争前后他们的心理变化。而此刻我们作为观众在观看他们的作品序列时就像当年日本观众、现在的我们观看本片一样,可以以一种理性、非理性的角度观看那时的历史,正如我们观看这部《残菊物语》一样,既可以评说本片“对于男性过于宽容”也可以评说本片正是通过这种对男性近乎放纵式“宠溺”达成一种巨大的讽刺性。
有关那时的历史、这些导演的心态我们不甚了解也无从去求证,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作品管中窥豹,正如观看、理解《残菊物语》时我们可以通过他曾经的作品看出:
沟口健二孜孜以求的可能是:经过苦难的磨炼成为圣善的女人,忘掉过去的一切,对男人给予宽恕,从《山椒大夫》中紧紧拥抱儿子的双目失明的母亲,《西鹤一代女》中最后宗教式的形象,《雨月物语》中已经成为亡灵的妻子迎接丈夫和儿子,《近松物语》中女主人公面带微笑与爱侣共赴刑场等,沟口晚年大概是想对那受到女性宽容而感到非常幸福的心情瞥上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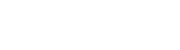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沟口的故事多大同小异,尤其在内里多很类似。不过本片在运镜上显然是早期沟口的集大成。包括全程冷静的旁观者态度与很多窥视镜头颇见功力。四星半。
日本早期有声片。摄影机运动(横移、tilt、跟拍等多方向、层次和节奏运动)和人物走位配合精妙。据说沟口非常喜欢排演,如此精确配合的确需演练多次。在摄影棚内拍摄才有如此强的控制力。用画外声音来暗示画外空间也出神入化。传统日本社会的阶层和性别偏见,使得女性成为伟大的“牺牲者”来成就男人。
凄婉悲苦的爱情故事。1.沟口的母题:为了男性而自我牺牲、默默奉献的卑微女性。整个故事又是在控诉阶层与身份的固化,门当户对的婚恋观与自由恋爱的新思想间的斗争。2.剧作上的三段反讽:争得爱情-丢了前程,于艰苦生活中迷失自我(失却事业信心&不再珍惜阿德的爱情)-磨砺锤炼出演技&依然保有阿德的支持,演艺成功-痛失所爱。3.比及后期作品,本片真正坚持了一场一镜,以固定长镜和摇移长镜为主。4.室内戏摄影机多与门框或墙面构成约45°斜角,墙面交界线常居后景中央,纵深立体感极强,且人物多朝侧面,与小津和黑泽的正面垂直/平行构图迥异,配合中远景机位及时而复现的俯拍或远处窥视镜头,含蓄而克制。5.室外戏才有几次中心对称或垂直纵深构图,街道上的横摇跟拍长镜(几回大仰拍)。6.高潮舞台戏,切换不同机位,且有正反打,角度多样。(9.5/10)
《残菊物语》里女主角的牺牲究竟是给谁的呢?是为她的爱人、为艺术还是为了整个父权家长制的体系?这三者在电影中重叠在一起,让电影在悲剧性之余颇有些弦外之音。最应注意的是,男主角的专长是饰演女性。而他演技的突飞猛涨是建立在枕边人的一路扶持之上的、他放逐时期的颠沛经历亦是下层女性的命运。这样来看,女主角的自我献祭以爱为名,以完善艺术为实,而最终以再度确定阶级关系为果。沟口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处理这出自我牺牲剧,而他最终对于这些权力关系的态度究竟是予以无情的揭露还是无奈的喟叹,这里实在看不出来。但显然30年代的日本社会对于这种献祭的精神是大力弘扬的,因而难怪本片会甫一问世便被封为圭臬。
影片当中菊之助与阿德经历了两次分别,分别之后菊之助去找阿德,一次在阿德的家连排的平房中,一次在火车站,两次是互相对仗的拍法,横移镜头,菊之助在寻找,依靠的是摄影机移动速度和演员表演走位及停顿的配合,菊之助的演员很有意思,这两段表演都有那种寻找中的“停顿”,他演得舞台感很浓,那一幕明明大量的群演,但就好像是他的独角戏,他面上急切的神情,时快时慢的脚步,还有那个停顿,都显得少傻傻的,是的,就是这样一位享受在女性牺牲里的少爷唯一付出的事。最后游船上,阿德在他们曾经在大阪住过的房屋中去世,那一刻风光的菊之助少爷有那么一怔,光辉好像互相调转了,死去的人变得圣洁,成功的人再一次被万人拥戴成为讽刺。
#SIFF#重看;尝遍人间冷暖,识尽风尘险恶,用艰辛流浪熬成的艺术升华,却要以忘怀告别终结情深;你是他清醒的劝诫者,是他长情的同道人,是他生命里的流星,更是他命运里无法抹去的伤痕,又一出苦情女性的悲歌。
下半场就闻到了悲剧的气息,实在很想逃。大段整场的歌舞伎表演,结尾的游船,确实又极大提升了悲剧力度。
8.0/10。1.一镜一景:全景长镜头极富表现“动的美学”。2.一出哀而不伤的纯美童话:五年来的不离不弃,为他的成名而默默离开,得到他父亲的原谅时却又不幸牺牲。3.结尾处的平行与舞台上的相似性转场使全片的剪辑不显单调。4.叙事太拖,扣一星。
此次电影节放映版本虽然是4K修复(目前世界上最好版本),但依然是不佳的拷贝,字幕也出了很大问题,所以观感非常差。被如此动人肺腑的付出所感动,被辉煌冥船过忘川的收尾惨得径直闷过一口气去...依稀记起初见那个深夜的长镜头,多么迷人又悲惨的命运安排....QAQ
建筑的精巧结构才能造就如此精杪的镜头运动,随着镜头横移,前中后景各自的层次不断开合,交代环境,提供引导,然后将调度放在演员身上。每一次横移都能提供有趣的信息,镜头不动,有事发生。
本片内容描绘日本歌舞伎界中严酷的演艺生涯,以及女性为爱而自我牺牲的悲情故事。是沟口『一镜一景』表现形式的起点,启用的男女主角均来自舞台剧演员。女主角森赫子较长于花柳章太郎,沟口也不做掩饰,是极力以「写实」风貌呈现。本片依据当时电影法被选为优秀电影奖,也是第一届文部大臣奖作品。
老拿女性表达定义沟口健二有点狭隘了,除了讨论艺术,讨论人生,讨论女性命运,更多是在表达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固化,结尾游船和病死的蒙太奇不仅凄凉,而且残忍,直接揭示了阿德也不仅仅是松之助的缪斯,而且是封建家庭集团加强内部结构的祭品,故事呈现的是一个献祭的过程,是传统礼教对人性的压制,是上流社会对底层的剥削。
20siff 残菊物语中女主很少展现正脸多是背影和侧影,作为女形的妻子及比他年长的卑微女佣,她不该有任何光彩,黯淡如柳枝低垂云遮月。只有她幼嫩的声音是醒目的,几近喋喋不休,时刻在袒露心声,作出劝告和鼓励。沟口的女性都像一根纤细的扇骨,在完成自我牺牲以后最终被收拢回男性自身
正逢沟口健二生日当天在电影资料馆观看修复版。工整古典悲剧,号称悲恋其实却是事业粉奉献的一生,却被各种窥探式的冷峻甚至阴森的镜头语言刻画得有一丝邪气。片中出现了《四谷怪谈》《艳容女舞衣》《逢坂关》《连狮子》四出剧目,菊之助果然还是女形功夫好。日本梨园世家的因循腐朽与跃进革命都让人感叹。ps现在的七代目长得跟主角简直一模一样,女形演员这种宽脸凤目长相太标准了。而日本梨园世家袭名制度真让人头疼,养子、女婿等联姻手段也跟中国梨园一样混乱,成駒屋家的孩子在片中只能当工具人配角。
20siff 1939年!!这大概是我看过最老的日本电影了,一点也不生涩,讲得都是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背景音效那些鼓点、节拍声、叫卖声。。。表现人物和剧情,在那个还没有背景音乐的年代。特别喜欢男主翻身的那场歌舞伎戏,镜头分述台上的丈夫和台下的妻子,祝贺成功出来真是止不住眼泪
艺道三部曲 感觉这已经不是殉情了,而是询道。喜欢上个这么头脑简单的男人可真够悲的。
Otoku在楼梯探出头,轻唤一声「あなた」,转而镜头对准了化妆柜前的夫妇俩,日常的爱大抵如此。病榻上的Otoku垂危之际,气若游丝却难掩喜悦地又唤了一声,随后在交叉剪辑中影片迎来了催人泪的结尾,这一悲剧被渲染得可泣。全然沉浸在蒙太奇带来的感人爱情悲歌中。四星半。
2017SIFF。沟口健二的布景、镜头语言与配乐惊为天人。这个人物性格与命运局限于时代的悲剧最终如女仆阿德逝去的生命般远去(包括歌舞伎艺术),整个电影中阿德几乎没有近景特写,却成为影史上最难忘的女性角色。
这可能是我看过的关于“艺术人生”的最好的电影,或许,直接说是关于人生的吧... 真正的“人生如戏”啊!一切的忍耐和付出,是为了什么?一个问题根本概括不了... 哭了好几回...😭 4K修复下还是朦胧,女主角的脸鲜少面对镜头,她完美得就像一个梦
调子特别沉静,风格很美,有大师风范。最后特别受不了菊之助的凉薄。最后几幕特别好,有红楼梦的况味,一边是满河灯火,鲜花织锦,烈火烹油,一边是凄凉寂寞,黯淡无光,生命到了尽头。游船上风光的菊之助忍了忍眼泪,向两岸的观众鞠躬致礼,你可以猜想,他总归会过得好好的,被时间治愈,被荣耀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