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地洞》:隐喻交织,展现出纪录片的魔力 | 专访TIDF亚洲竞赛首奖导演胡涛
采访:佟珊
整理:张劳动 佟珊
整理时内容有所删减
编辑:小nine
在刚刚结束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上,胡涛(胡三寿)的纪录片作品《地洞》获“亚洲视野”竞赛“首奖”及“再见真实”单元“评审团特别提及”。
凹凸镜DOC编辑联系胡涛导演时,他正在村子里拍摄纪录片素材,胡涛出生在陕西商洛山阳县湘子店村,他在这里拍摄并完成《山旮旯》《古精》《偷羞子》《地洞》四部纪录片的村子,其中《地洞》曾入选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纪录片研究者佟珊曾经采访过胡涛导演,访谈中,胡涛分享了四部作品的心路历程,创作机缘。以下为采访正文:

胡涛
1992年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湘子店村,2015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影视摄影专业。2013年在校期间,参与民间记忆计划,返回老家村子采访老人记忆并拍摄纪录片,完成纪录片长片处女作《山旮旯》(2013),及第二部片子《古精》(2015)。在校期间也创作完成剧情片《离殇》《灯火余生》。胡涛也参与民间记忆计划剧场《阅读饥饿》《阅读父亲》创作及演出。

佟珊
影像研究者,策展人。长期关注华语青年影像、艺术电影、纪录片与电影节文化。
采访者:你是怎么知道草场地工作站,以及如何加入到民间记忆计划中的?《山旮旯》是你在民间记忆计划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吗?
胡涛:是的,《山旮旯》是源于草场地工作站。我当时在西安美术学院上学,大二的时候,吴文光老师和草场地作者来给我们班,上纪录片课程。
采访者:你是学什么专业?
胡涛:我学的是影视摄影制作。那个专业的课程设置比较综合,吴老师这门课的课程形式是,每去一次,有三到五天的时间在我们那上课。
采访者:是什么形式呢?一去就连着讲三五天吗?
胡涛:对。给我们上课的基本上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放映草场地过去制作的片子,然后聊每个人自己的故事,还有一种就是身体工作坊。吴老师亲身介入,还有当时草场地最早的一批创作者跟着一块。
我记得放过吴老师的《亮出你的家伙》,还有梦奇姐的片子,还有一些创作者2010年、2011年回村做的片子。我会回老家拍摄,很重要的原因,是吴老师布置的课程作业。这个作业不是当堂完成,是以一个课后作业的性质来去创作。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发现它不仅仅是作业那么简单,在村里去采访的时候,这些老人经常会讲过去的事,因为我是在那个村子长大的,我觉得这种简单的采访肯定不够,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的,我对村子有了另一个更深层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从我出生到长大记忆里边的村子,还有那么多人都在这个村子里边生长,那次作业是让我打开了进入这个村子的“一道门”。

《山旮旯》海报
采访者:你跟你所拍摄的村子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一直生活在那里吗?
胡涛:对,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那个村子,我爸妈也是同村的,并在那里结婚。我在村里出生,一直到16岁我离开那个村子到县城上高中,接下来就到西安上大学。过年的时候都会回去。
采访者:你爸爸妈妈现在还生活在那里?
胡涛:对。还在那里生活。
采访者:所以你跟你的村子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胡涛:对,我的家人现在还在那个村子里居住。
采访者:第一年回村子里面拍东西,尤其是去做一些采访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让你觉得很意外的事情?
胡涛: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回答。第一个困难的东西,是自我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从小在那个村出生长大,对那些人太熟悉了,我比较偏内向,如果拿个摄像机去拍,人家感觉不太好。但是这个作业我必须得完成。
第一次拍,我最开始的采访,是采访爷爷奶奶。老人的讲述非常让我震惊。因为从我一出生,我就看到这个老人在村里边生活、劳作的样态,但是没想到他的讲述,仿佛撕开了他生活里“另一个世界”的样子,他经历了一些那个年代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历史书上可能连一页都不到,但是我没想到,老人的讲述那么的丰满,有血有肉。
采访者:你的作品跟民间记忆计划的早期作品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觉得你的作品相对更关注日常生活状态,没有那么强的行动性和介入性。你是怎么形成这种拍摄取向的?当时应该已经看过最早一批创作者的作品,对吧?
胡涛:对,最早是有看过梦奇姐的片子,包括海安、罗兵的片子,我当时的身份是在美院读书的学生,其实和草场地之间,是保持着有一种距离在,我觉得我的拍摄也能看出我的性格,我比较内向,拍摄也不太会把自己露在镜头里面,我不太去在画面里介入和行动。
当时的拍摄是一个重新去看村子、展示村子的状态,还没有很深的思考,《山旮旯》对我最大的一个意义,是让我打开了村子的大门。

《山旮旯》剧照
采访者:你的镜头非常讲究,从你第一部片子里面就能看出来。你后面的作品也基本保持了观察式的风格,你有尝试过更具有介入性和行动性的方式吗?
胡涛:这种介入性行动的边界是值得思考的,我在创作《地洞》的时候,我把摄像机支在那,和村民一起盖一座坟,这个坟是给我外公外婆盖的。我不得不跳进镜头里去,摄像机不得不离开我的手,我已经无暇顾及到机位或者角度。越往后的拍摄,我越来越体会到我在村里面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它不是一种特别强的行动介入,我特别喜欢这种生活的状态。
我在村子里生活,它本身已经属于一种行动,或者我和村民在一块生活的状态,它这个村子你永远不会摆脱掉,也不想摆脱,而且和村子里面的人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拍摄,成为了一种辅助。接下来进而去思考他们生活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生活的状态里边截取片段。我不知道未来我会不会有一种介入性的行动,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我不想只是导演,我就是一个村里边的人。

《地洞》剧照
采访者:《偷羞子》这部作品,是怎么想到用画外音来结构?
胡涛:因为我在那个村子生活了十几年,从小在村里边成长,我和村子之间天然有一种紧密的联合,摄像机不仅仅是拍到画面里边的东西,它有一种时间的东西在流淌,这种时间里被掺杂了许多的记忆片段,他只有属于我。可能大家看那个画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我看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海里边就想着过去的好多事,我觉得画外音在空间里面,是记忆的一种飞翔或者记忆的增长。
采访者:画外音其实也打开了另外一个时空,让影片的时间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当下。
胡涛:对。画外音也不像我正常讲话的声音,像是讲述者沉浸在叙述的记忆里,是一种和现实之间的叠加状态,我也不知道它叠加成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记忆它突然冒出来了。

《偷羞子》海报
采访者:我觉得你拍人非常有温度,透过你的镜头,我能感受到你对那些人充满了感情。《古精》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尤其是关于你爷爷的那个部分。那个结构安排很有意思,它超越了一种现实的线性时间逻辑。
你先是让观众知道你爷爷去世了,然后听到他在讲述他人生历史,也包括他的担忧,最后画面又回到他在村子的一些日常状态,好像他还活着,一直生活在那里。就好像你用影像的魔法让他复活了,特别动人。可以谈谈这个片子的创作想法吗?
胡涛:第一部片子拍完之后,草场地对我影响还在,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没有拍够,因为第一个片子的拍摄,导致了我大二寒假暑假都在村子里边拍。
我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那个时候很疯狂,拍摄了一些关于民俗的东西,我当时就已经拍了很多素材,不知道怎么做这个片,在2015年,也就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突然我爷爷去世了,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就回溯过去拍的东西,我想剪一个片子,在我毕业之前的一两个月时间,我疯狂的把这个片子剪辑出来了。
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状态是我想去拍摄,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就做了各种尝试,包括给老人,采访的时候,我自己买了黑布(做背景),在那个房间里面装好,还架了灯,当时是出于一种年轻人的冲动,想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爷爷的去世,让我有一种巨大的冲动,想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才给吴老师他们看,想用这个片子纪念我的爷爷。

《古精》剧照
采访者:《古精》比较集中在几个老人身上,也呈现了他们在村子里的日常生活。我不知道你在创作的时候,是就重点采了这几个人吗?还是你其实采访了很多,最后剪成了这个样子?
胡涛:采访不止那几个,七八个人。包括日常的素材也不止拍了那么少,之外的东西很多,村子另一个层面的东西也很多。但最后选择这几个老人,和他们的讲述有关。而且人物基本上都是我特别亲的人,里边有我爷爷,有我外公。我当时的想法可能也不是太成熟,当时挑选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叙述具有完整性。
采访者:我知道草场地有一整套创作方法论,其中包括邮件组通讯交流,会鼓励大家在影像创作之外进行大量的写作,包括写拍摄笔记、关于村子的思考所感等等。你觉得写作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帮助?
胡涛:写作对我很大的刺激是,它先于剪辑,更加自由,蔓延舒展开来,在你写作的时候有很多即兴的成分,比如我片子里那些旁白,在前面的写作过程中,撰写出来了,会有体现。写作和剪辑是互相存进的。
《地洞》的开篇的第一个镜头,最开始我没有想到用那个画面。最开始是以写作的方式,通过那个镜头我观看到我们村的好多人,然后我就写了一篇,写完之后,觉得这篇文章它可以转化成另一种意念,刚好构成《地洞》的第一个镜头,是一种互补和共振的状态。写作会让村子和当下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动态连接。
《偷羞子》中很重要的一个画面,是我奶奶在地洞里面挖红薯,我拍了一个周边全黑,她拿着手电挖红薯的那一个画面。
采访者:就是你第一个画面。
胡涛:对,当时这么做,这个东西像一个靶心一样,那个画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指向性的动作,在一个全黑的状态下,只有一盏微弱的东西在摸索,在找寻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就是那种性格的人,他把自己包裹起来,但是内心他是有如此丰富的想象,自己内心的想法,情感的东西,通过那个画面,刚好就做了我的作品的开篇,然后往下展开。

《偷羞子》海报
采访者:之前吴老师(吴文光)讲述“作品核”,曾拿《偷羞子》来举例。这个作品核你是一开始就很清楚吗?还是在中间找到的?
胡涛: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太清楚,是在写作过程中才慢慢确定起来。在写邮件组的时候,我有一篇文章,篇名就叫《偷羞子》,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小树没有嘴,是一个偷羞子。是我奶奶常常就是挂在嘴边的话,小树就是我大爷,最开始写作带我思考,我老家方言,它所暗含的另一个广阔的一种形象。
采访者:那你最开始想拍的是什么?在你找到“偷羞子”这个核之前。
胡涛:我有拍摄的苗头,是因为我大爷从08年到09年时精神上有了问题,我到16年(去拍摄)。我大爷疾病的这件事,家里面的人是比较痛苦的,我想他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整个人就精神失常了,我当时是想以这为切入的。
在回家拍摄的时候,我有点想拍那种猎奇式激烈的画面,但是现实里边并没有发生,我就是一直在拍,它不是显性的表现出来一种巨大的动荡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疾病最大的根源就是这种日常乱象,那种暗流涌动,慢慢才建立的意识。当时是有个想法,在拍摄到思考再到写作,这些东西它揉杂在一起,慢慢形成了这个片子想要做的一个方向。
采访者:所以你在拍的时候也会写拍摄笔记吗?
胡涛:有写,包括剪辑的时候也会写剪辑的笔记。也会回过头来看。

《偷羞子》剧照
采访者:草场地集体创作的形式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胡涛: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其实是在草场地这个环境里边,让我能坚定地继续拍摄下去。当你一个人去拍摄的时候,你是一种单枪匹马的状态,但是在草场地里边它有一种互相刺激、互相鼓励、互相看见、互相学习。你看大家都在拍的时候,你在氛围里边拍摄,你有种很坚定感。
整个社会跟洪水猛兽一样,把我们这些人一下子给淹没掉。但是草场地我觉得很重要的,它让每个人坚定地去继续拍摄,有一种互相取暖,真的是抱团取暖。
采访者:未来你的创作还是以村子为基地,围绕它来继续创作吗?还是你也不排斥其他可能性?
胡涛:至少创作这条道路上,这个村子它不仅是一个基地了,它是一个源泉的东西。我日常的拍摄不仅局限在村子里,我日常拿摄像机比较多,我走哪可以拍到哪。
采访者:所以你也有积累一些其他的素材?
胡涛:一年可能有一半的素材是这个村子之外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它带给我什么,但是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同样也是很重要,这些素材它在未来它都会成为一种财富的。创作未来最大的一个朝向,它不是走向一种固定而是走向一种自由。我肯定一直会在村子拍摄下,它像一个源泉一样的东西存在。
采访者:你年复一年地拍村子,当然村子本身会有变化,但在完成几部之后,你会不会有创作上的焦虑?比如如何找到新的可拍摄的东西或者主题?
胡涛:焦虑是常态的,我也就很坦诚。就拿我去年在村子里边举个例子,我去年基本上在村子待了小一年,我有时候拿着摄像机出门,刚走到门口,其实我就犹豫了,我为什么要出去?我有时候很怕见到那些老人,因为村子里面的人都走光了,我一个小年轻,我在村子里边晃荡,一种感觉就是迷茫和无所事事。
吴老师形容这种状态叫:枯寂的状态。你走到门口的时候,你又感觉你不想见村里边的人。因为我在村子从小长大,对村民太熟悉了,这种熟悉里边它掺杂一种眼光。
这种东西每个人可能都无法避免。当你去做一个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一时即兴的东西,它是一种年复一年的工作。在某个阶段就是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阶段,它不是一个终点。其实在你重复拍摄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阶段他会渡过去,之后,你又对村子或者又对自我在这个村子里边,有另一个意识上或者精神上的认知,我觉得这种认知像台阶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就看你想不想去迈或者敢不敢去迈。
一年一年的拍,会不会把村子的内容拍完,我以前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村子是创作的源泉、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它是永远拍不完的。对我来说很大的启发是,这个村子它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不停的每时每刻的变化,只是你能不能洞察到村子无穷无尽的宝藏和财富。
拿我的创作来说,我拍完《偷羞子》之后,我其实想拍我外公外婆,拍了一年,那个片子剪了两稿,但没有达到我内心想要的。《地洞》那个片子为什么出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想着去设一个主题或设一个创作的方向。其实拍摄或者创作,在日常里边,它是自然生发的,因为你要持久的去拍摄,因为拍摄的持续性,所以创作不枯竭。
比如说《地洞》,我是因为我外公外婆建造坟墓,我才去拍的。也因为我必须要去参与建造,因为我是他的外孙,他们要建坟,我不去,这其实在我们村里,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我自己内心也过不去。
我想我既然去了,我就把摄像机支着,反正它支在那儿就可以了,我觉得那个片子带给我很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倘若没有我之前的拍摄,我不可能把摄像机支在那儿,从我去建坟那天起,一直到坟墓建成,七八天的时间,每天的素材量至少有七八个小时,在那个地方定下来,就拍七八个小时。
到七八天之后,素材量有四五十个小时。如果没有之前拍摄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定力来去拍摄,可能拍一两天就觉得乏味了,我干活都干累了,还拍什么。你持续的拍摄,它总会让你的创作会持续,持续的过程中,不仅是拍摄,还有一种思考,裹挟着,往前一起走。
包括今年的片子,包括未来的片子,在你拍摄之前,越来越没有一个主题的东西或者方向,越来越多是拍摄之后的质感,一种思考,慢慢形成主题和方向。我觉得整个创作形成了一种广阔性,而不是因为一个题材、一个目的才去展开一个拍摄。没有目的,没有题材的时候,我们再去拍摄,你突然发现所有的拍摄都是,你一进那个村子就进了一个矿床。
采访者:在拍摄上,你说越来越没有主题和指向性。但在剪辑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要找到指向的,对吧?
胡涛:对,剪的时候,包括写作的时候,从这里边慢慢它有一种趋向和走向的东西。

颁奖词
本片是大胆的电影创作,也是对生命短暂的深刻沉思。导演以肃穆细腻的手法描绘他的家乡,同时自己和亲戚正遵照当地习俗,为家中长者建坟。影片透过精心设计的固定长镜头、缓慢感性的步调、省察的声音及迷人的开场和终场,为观众开启多重体验。本片从个人生活场域的提问出发,逐渐扩及社会、政治、精神层面,甚至是当今全球面临新冠病毒所衍生的经济难题,导演借由概念性形式及蕴含哲思的观点处理上述议题,使本片成为对当代面貌的独特见证。
采访者:所以感觉上,其实是你不带着任何预设先去到那里,然后在里面慢慢地去发现也好,感受也好,就是让一些东西自己浮出来?
胡涛:对。有时候我感觉我的创作其实跟人生的阶段还是有很强的联系,就是今年的一个状态,你生活的一个状态,精神的状态很有关系。它没有剥离开,我在村子里面,它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发酵、互相共鸣。它就没有一个终止,除非是你的整个精神状态,不想去创作,它可能就会枯竭了。
采访者:你每年回村拍摄,是有固定的时间吗?
胡涛:有固定的时间,过年期间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最少在村里待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在西安拍完一个工作项目,我回家又待半个多月。
采访者:每年大概会在村子里待多长时间?
胡涛:现在最少得有两个月以上吧。
采访者:你持续地拍摄村子、村民和你的家人,在这个过程有影响到你和村子以及家人的关系、交流相处方式吗?
胡涛:很具象的一个东西,以前和家人之间还是有点矛盾的。可能说话上,我觉得我的语气跟家人之间交流是比较冲的,拍摄的时候,尤其是把你的摄像机对着亲人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原来和你朝夕相处的亲人,其实到某一个程度上,他有他自己的另一面,让我和家人之间达成了一个沟通和交流后,我觉得另一方面真的是让我和家里人之间有一个互相的理解。
拍摄它作为一种对话的方式,或者说一种交流,至少对我个人是很有意义的。不然的话,以我的性格其实我比较内向,和家人交流就很少,但是因为有这种拍摄,我和家人有一种对话和一种交流的状态。
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每一年的回村拍摄过程,让我在城市里边生活的时候,或者在我人生道路、面对未来的时候,让我觉得有一个定点。不是一种漂泊或者流浪的状态,至少在某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知足、很宁静的。

颁奖词
本片独特叙事的手法、将看似平常的地方生活连结到更大的世界状态,令评审团惊艳。影片开头非常引人入胜,角色出场的镜头竟是从墓中拍摄,我们随后得知这群人是在为家人建坟。从杰出的开场镜头开始,全片未令人感到失望,一场比一场奇特,亦不失重量。片中隐喻交织,十足展现出纪录片的魔力,并提供对世界缩影的想象,以崭新的观点看待疫情、封城、死亡,以及政治和家庭关系——提醒我们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能多一分哲思。我们很高兴这部作品存在,也很兴奋我们能发现此一杰作。
采访者:你觉得这种被锚定的感觉,跟你持续拍摄村子和家人的行动有关系?
胡涛:很有关系,就是你的行动,它带给了你在未来人生道路上,有一种明确,或者说有一种定力的东西。
和我同龄的人,他们生活我也同样支持,但是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说,反正我们生活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迷茫。不知所措,被外在的事情带着走,反而我们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东西。
采访者:你这些作品有给家人看过吗?
胡涛:有看过。比如说线上放一个片子,我有时候也发到朋友圈,但是他们看的比较少。我和他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比如我前段时间就在家待着,我奶奶有时候看见村里边有个啥,她就跑过来,她说明天那个村子里边有个事儿,你去拍拍,我的拍摄其实很重要一点,我家人是支持的,而不是说你这个东西赚不赚钱。
采访者:从2013年开始创作到现在,有没有特别难熬的时刻?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真正给你鼓励的时刻?
胡涛:特别煎熬的时刻也有,包括现在,某一个层面上,我觉得就是一些生活压力。另一个层面,可能是创作的停顿期,但是恰恰这种停顿期,我倒不是太担心,因为你只要持续下去的话,这种停顿期它也属于创作的一种状态而已。生活的压力可能有些煎熬。
鼓励的东西,也很多。一个片子创作出来,我觉得是对自我最大的鼓励。这个鼓励不是说获得荣誉,而是经过这一年多时间的创作,这个片子做出来,你在花这么长时间里边,让自己的状态得到一个舒展,创作的过程,思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前进,一部做出来,你就有信心接下来继续做。其他的东西,包括草场地或者观众看还有电影节,它是属于创作的附加值,有的话就是像礼物一样,没有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影响创作的心态。
采访者:去年疫情的时候有很焦虑吗?
胡涛:有, 9月份的时候,村里边青年全走了,基本上都是老人了,但是那段经历真的是让我冷静起来,我多少年都没有看到村子四季的变化,在整个村子感受到一种时间的流淌,时间是一点一点的在那个村子里边度过。
采访者:这些以后会呈现在你的作品里吗?
胡涛:肯定会。因为那个期间也拍了大量的素材,大概有十几个T的素材。
采访者:我看你之前的片子,觉得虽然你是在拍村子,但更多还是从你的家人,你的家庭这个角度进入的,比如《偷羞子》的整个场景就放在你奶奶家的院子里,去呈现院子里面这三个人,但影片最后你列出了村子里一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从而有了一个从你的家人到整个村子的这样一个延展。你之后的创作是围绕家人,还是说会延展到更广阔的整个村子?
胡涛:未来肯定会涉及到更广阔的范围,这种广阔性,我觉得不是说涉及到整个村子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家庭,或者是更加的自由,而是你思考的东西到哪个阶段,到哪些方向。它也会越来越自由,至少在你的创作过程中能带给你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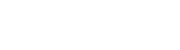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电影以一个固定、构图完美的镜头开场,宣告了活人造墓这一主题。村里世代的坟、宅相互争地,无论死者还是生者,灵魂都被封印在“入土为安”这句老话中,挪移了“被恐惧的乡土”这一表征。记录者有他作为乡土社会中一分子的人情联结,捕捉的是建造本身和施工图景,只有墓穴本身采用了内外微观。但他赋予影片太多自己的立场观点,将各种信息强加给观众——直观的自白、听来的传说、瞎编成分的梦境,连同带有社会目的的广播和人们的议论去组织他想要给予的信息,自我表达被安排地满满当当。
#2022TIDF :民间记忆影像计划作者群之一,一个百年家族在霍乱时期的生死疲劳纪实,或静默或悄然游移的摄影机,与不太显现情绪的独白,使得影片在一片沉默与数声谓叹之间浮现绵延的宗族宿命
#TIDF x DAFilms 旁白也太诡异了
开头那个长镜头挺妙的。
2.5。疫情给了不少的当代性和思辨性,不然真挺疲软的…..
很喜欢这个主题概念。广播里透露的实事背景和“建造一座坟墓”的前后对比,首先是对故事发生的地方的一种展现、记录,其次是一种当下山村中精神面貌的投影。看的时候思考了死亡、坟墓好像在我熟知的城市生活中仍然属于一种禁忌,但在这里,住房的旁边就是陵墓,生前就建好坟墓才能因为知道子孙还会祭拜而安心离去,也是这片土地的一种常态。镜头慢、旁白慢的风格保持到了最后,但也许还可以更凝练吧。导演选择从最熟悉的家乡的环境来记录当代,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最后一幕让我想到《蜘蛛的策略》最后,人人都归于芒草
村民们在坟上的闲聊太厉害了,比如——“以后这里就是死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胡涛的作品需要被放置到民间记忆计划序列里才能够更好地被理解。
#TIDF2023tour# 风格太像毕赣了,但是多了点疏离感少了些诗意
旁白读得很做作,这方面是导演不是专业演员的缘故,记录的内容也很无趣
肤浅又没有控制力的拍摄,慢镜头和声音不是这么乱用的。这几年华语纪录片都是这种假装深沉、内在混乱失控、表达空洞的伪批判实文青路线。要继续这么拍下去不如趁早收手。另外,如今TIDF的选片和评奖水平差距可以光年计,得奖也遮不住这片本质的烂。
一星半
【TIDF x DAFilms】一部拍摄家人建造坟墓的纪录片乍听起来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导演很清晰地找到了叙述的角度,不仅开场引人入胜,也构建起与家人的成长记忆,在建坟的同时疫情肆虐,成为这个家庭纪录片重要的时代注脚(IDFA选片一直都好棒)
这是离公众最远的那种电影,是极为个人化的自我表达。胡涛是有独特的个人影像风格的导演,安静,缓慢,可识别度也很强。这部作品拿奖,说明外面的电影节还是蛮重视导演的作者性。
#TIDF-DAFilms##补标复健# 陕西村落,家族,墓穴。草场地风格,关中话很亲切。2023.2
很不喜欢过分关注人声的声音处理,包括防疫广播的加入,虽然其荒唐的内容本身显然值得一听。没想到直面黄土的题材,居然是如此机械的观感。
不知所云 莫名其妙 矫揉造作
有想法,但真的很乾。乾癟疏離的旁白聲線、靜謐(但導演作為村裡人又會被cue到)的觀察鏡位;從地洞/墓穴內向外拍攝,旁白介紹每一位家人的開場,到收尾站在山上手持掃視村莊家屋傳來一聲聲回喊。充分經營的沉沉死氣,以及其中的毀與建,不能說不是一個形式與內容高度吻合的策略,但對我來說,效果除了悶實在不欣賞。自我與集體的歷史敘事問題。半星for荒謬的疫情期間廣播⋯(也標示出了清楚的時間與地點/距離,共時的大歷史)。
旁白学《路边野餐》的调调。
#IDFA2021展望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