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无声世界Todoelsilencio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入围华沙电影节前两部竞赛。 Miriam is an actress who is also a sign language teacher, but she is not deaf herself. However, a downward spiral begins when she learns that she will indeed become fully deaf. Despite having deaf parents, deaf friends and a deaf girlfriend, she refuses to accept a world without sound. A remarkable film, also in terms of sound.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怪侠看不见的现实—数据工人丝黛芬妮节振国暗影猎人第一季你的短信孟买传奇我和我爸的18岁欲1988我在等,风也在等刀剑若梦茶乡花正开伪行者太后吉祥河内,河内大树之歌天作之莓菜鸟王爷闹江湖宽恕2007爱无7限血洗鳄鱼仇欢愉的艺术喜结良缘
入围华沙电影节前两部竞赛。 Miriam is an actress who is also a sign language teacher, but she is not deaf herself. However, a downward spiral begins when she learns that she will indeed become fully deaf. Despite having deaf parents, deaf friends and a deaf girlfriend, she refuses to accept a world without sound. A remarkable film, also in terms of sound.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怪侠看不见的现实—数据工人丝黛芬妮节振国暗影猎人第一季你的短信孟买传奇我和我爸的18岁欲1988我在等,风也在等刀剑若梦茶乡花正开伪行者太后吉祥河内,河内大树之歌天作之莓菜鸟王爷闹江湖宽恕2007爱无7限血洗鳄鱼仇欢愉的艺术喜结良缘
长篇影评
1 ) 听障与间离
如果我们拿走所有的文字,代之以影像,我们可能会回到电影史早期的阶段,也就是无声电影的阶段。这可能仅仅是方法上的倒退,然而尼古拉·菲利伯特的《聋哑世界》(1992)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视野,这是一部记录聋哑人生活的电影,他们从小失聪,使用一种手势符号代替日常语言。这部电影的本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种对有声和无声文化的对比,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这种对照会被消解并转而支持以下的观点,即像片中那个极其雄辩的教授一样使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见解:“我的妻子和我都听不见,所以说真的我们希望有一个聋哑的孩子,事实是我们的女儿听力非常好,但这不妨碍我们一样爱她”。这不是一个把残疾转化为恩赐、把缺点转化为才能的问题,而是一条只有通过残障体验才可以理解并抵达的道路。尼古拉·菲利伯特并未打算“退化”到一个无声世界,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视野,在这里,寂静和话语可以彼此强化。
狄德罗在《论聋哑人书简》(1749)中告诉我们著名的作家Alain-René Lesage晚年失聪,但他仍然走遍各地去参与自己的戏剧巡演。“他说过,即使他已经听不见了,他仍然是自己的剧本以及演员表演的最好的法官。”[10]简单来说,这似乎意味着听力的损伤可以通过获得一种“从外部观看”的方式予以补偿,外部的观点源自外部的需求和渴望,这本质上是哲学性的。因此,绝非是巧合让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把这种间离(estrangement)视作电影的本性,仿佛这就是影像经验和日常经验之间可穿梭的那个入口[11]。也许电影可以带给我们那种通常只有通过高难度才得以认可的哲学写作,也就是说,一种非人的、被悬置的感受,就像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的:“一种充满色彩和张力的悬置”(a coloured and intense epoché)[12]。
原文参考文献:
[10]德尼·狄德罗,《狄德罗早期哲学研究中关于聋哑问题的通信集》,MargaretJourdain译,芝加哥/伦敦,The Open Court出版公司,1916年。
[11]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
[1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评论》,牛津Brazil Blackwell出版社,1960年。
出自马里奥·佩尼欧拉:《通往一种哲学电影》
原文见//www.douban.com/note/553646432/
狄德罗在《论聋哑人书简》(1749)中告诉我们著名的作家Alain-René Lesage晚年失聪,但他仍然走遍各地去参与自己的戏剧巡演。“他说过,即使他已经听不见了,他仍然是自己的剧本以及演员表演的最好的法官。”[10]简单来说,这似乎意味着听力的损伤可以通过获得一种“从外部观看”的方式予以补偿,外部的观点源自外部的需求和渴望,这本质上是哲学性的。因此,绝非是巧合让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把这种间离(estrangement)视作电影的本性,仿佛这就是影像经验和日常经验之间可穿梭的那个入口[11]。也许电影可以带给我们那种通常只有通过高难度才得以认可的哲学写作,也就是说,一种非人的、被悬置的感受,就像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的:“一种充满色彩和张力的悬置”(a coloured and intense epoché)[12]。
原文参考文献:
[10]德尼·狄德罗,《狄德罗早期哲学研究中关于聋哑问题的通信集》,MargaretJourdain译,芝加哥/伦敦,The Open Court出版公司,1916年。
[11]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
[1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评论》,牛津Brazil Blackwell出版社,1960年。
出自马里奥·佩尼欧拉:《通往一种哲学电影》
原文见//www.douban.com/note/553646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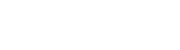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BC欧亚纪录片周No.5,赠票,35mins|很喜欢,还可以和赫尔佐格《沉默与黑暗的世界》(1971)一起观看。可惜要赶场未看完整,待补
聋哑世界 Le pays des sourds (1992)
有英版dvd, 借左比Carol(??)
无声的婚礼好感人。手语老师好可爱,看他讲故事是一种享受。这里的孩子都被爱包围的感觉。原来听不到是这种感觉,如果有一天我能拍纪录片,我想拍这样的。学习手语刻不容缓.......
听觉缺陷的人发展出了其他身体优势作为补偿,视觉敏锐、手指灵活、表情丰富。那个教手语的聋人老头,“说”手语简直就是在表演。
(琢磨了很多细节后加一星
78/100
太佩服太佩服了。一口气不喘地看完了。-_-
petit Florent萌哭我!!
En utilisant des langues des signes différentes dans différents pays, ils partagent le même pays des sourds.
让我佩服的纪录片制作者。看的英文字幕,等中文字幕到手,他的所有片片都值得再三学习观摩。
7.0;比較好奇他們怎麼吵架
常人永远无法进入聋哑人的世界,我们在其国度里不过是“他者”。O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U5r4NY0Zc/
寻求理解与沟通
关于听障人群的活动记录,包括教育、婚配、生育等社会活动等,再加上“Le Maigre”的回忆自“述”,大致勾勒出了该群体的整个人生。这个老师的表情动作太丰富了,天生的表演者总要被上天捉弄一番。一段戏剧表演完全通过演员的神情动作表现,发觉无声的表演总被“正常人”视作喜剧来观看。片中被父母送去精神病院的女士表明了“酷儿”身分间的区隔,海涩爱提出的“身份连结”在90年代的纪录片中是失效的。
无声的拥抱,很有感染力。
没有人为割裂有声和无声世界,而是考虑怎样把它们并置在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摄影机去体验那种那种生活。没有人为干涉,只有用日常的方式才可以理解并抵达聋哑的世界。
算是比较早关注特殊教育的纪录片了,聋哑孩子们很可爱。
最害羞的小朋友最爱撇镜头
8.0。通過幾乎摒棄一切有聲對白來建立觀眾的聽覺隔離,但整體上尚缺乏一個更為明晰有效的剪輯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