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中南医院妇产科,形形色色的故事上演从没有停过,5万块钱能救一大两小三条人命,手里只有5千元的丈夫,借钱、贷款、抵押房产此时都行不通,“拯救小凤之女”变得不可能完成;李家福——“拆弹部队”首领,面对夏锦菊保住子宫的请求,露出艰难而犹豫的眼神。心脏两次停跳,换血2万毫升,他如何剪断“炸弹”上的红蓝线,她又能否在“鬼门关”前转身?命悬一线之际,“生死时速”让人目不转睛。年轻妈妈李双双腹中的胎儿,引产似乎已被当地优生科判定,李家福团队却提出实施刨宫产,抢救微弱的性命。救,可能倾家荡产,一生背负沉重的负担;不救,可自己的骨肉,如何走上内心的审判厅。年轻的爸爸该如何踏上这段产房的“釜山行”。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女人本色老广的味道第六季献给棒球部的花束众里寻他撕心裂爱邻居富家穷路第六季欲无罪乌龙山剿匪记迷因杀机CRISIS 公安机动搜查队特搜组伦敦杀戮第二季朝政无名指骨灵怦然心动2010东陵大盗2游园惊梦1960一天(剧版)鸡毛蒜皮也是事非常公民王者游戏·觉醒错位教育新男孩2023主席第一季碰撞2022死亡交易1977(德语版)
长篇影评
1 ) 就是说点啥
我一般不看医疗剧,但这记录片的相对真实性,给予五颗星。 一个家庭是社会的小单元,医院又是个小社会,有悲欢,有离合,众生百态。一些事件可以成为社会现象级。 我所遇到的,就以生产来说,在医院可以算是喜吧,呱呱坠地这一骄傲的啼哭宣告一个生命的独立,带来了生气。 那还有没能啼哭的呢?比如剖腹取胎,产妇孕期发现胎盘植入膀胱,必须终止妊娠取出20周的胎儿,保大人的命;也比如检查发育畸形,放弃继续妊娠。在做这类手术的时候,我尽量避开看那孩子,心里过不去。 也遇到过,把产妇送出手术室,一家人都去病房守着婴儿了,而产妇在门口无人守候,默默流泪。 如果你听到,“孩子早产,正在抢救,需要转院进一步治疗,需要你签字。”而得到孩子爸爸的回应是:“是男孩还是女孩?是女孩就不救了。”会不会有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二十多岁的姑娘产后大出血,危及生命,子宫切除。
连续生了几个女儿,这次又是女儿,产妇问我们:“这孩子你们要不要?”面对这问题,我们能怎么回答?
一位48岁的妇女来做手术,告诉我她一直还没生过孩子,这是她做的第18次试管婴儿,年纪大了,卵子是别人捐献的,现在12周。我的确有些愕然,问她:“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她说:“我不甘心啊!”
男女平等吗?不。光从体骼上来说就已不平等,男性天生就会比女性强壮。在某些行业领域男女分工就会不同。
然后就是生孩子这事,从一个胚胎的着床,到胎心的搏动,然后发育到胎儿跳动,再到分娩。从早孕呕吐食之无味,到小腹便便,双脚水肿,到足月难以起身、下蹲弯腰,再到忍受剧痛宫口开全甚至侧切剖宫产下婴儿,这其中应是喜悦,兴奋,难受,怨念,痛苦相行的。这男性体会不到,怎能不爱惜。
男女可能平等吗?能。就像一部电影《隐藏人物》,价值认同,这就是平等。
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生孩子是一种使命还是义务?是不是真是自然规律?这个问题,我也还不知道。
2 ) 关于《生门》背后 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看完之后找了很久这部片子的资料,找到一篇很深入的报道,分享给大家。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生门》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三年后,纪录片走进影院。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不定时炸弹 武汉人管宝宝叫“毛毛”。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1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按照医生的说法,本应长在子宫后壁、前壁或侧壁的胎盘,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 他42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刚满29周,离足月还有8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2/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她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1分钟5滴”。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很长时间。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仍会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做产科医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输400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块钱,“5万块钱,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20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观众纳闷,“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25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11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2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鬼门关” 除了钱,死亡本身也显得虎视眈眈。 夏锦菊是真正走过一趟鬼门关的“战士”。她在ICU睁开眼时,静谧的蓝光笼罩了一切。穿白衣的护士在一排排机器中间走来走去,气氛肃杀。她想说话,嘴里插了胃管,发不出一点声音。 力气远离了她。甚至,连眼球的转动也要耗费半数体力。术后3天,她总共失血1.8万ml,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4遍。 那是2013年,她33岁。供给胎儿营养的胎盘,长在了前两次剖腹产的疤痕上。不仅如此,胎盘穿透子宫肌层,植入了膀胱。 这是典型的凶险性前置胎盘。当胎盘像大树一样被拔掉时,“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在宝宝分娩出来的一瞬间,“失血达2000ml”。57岁的摄像师赵骅把镜头推上去,能从镜头里看到针线一样细的血,喷向不同方向。 怀孕3个多月时,夏锦菊从广州回到老家黄梅保胎。小县城的妇产医生天天往外赶她,“你就是个定时炸弹,”医生劝她打掉孩子,否则到时候大出血就像自来水管,关都关不住,“人财两空。”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人财两空”。即使在第一次心脏停跳前,还在请求医生,帮她保留子宫。 心电监护仪显示过两次直线。在那个家人被要求“准备后事”的夜晚,她的腹部被止血纱布填满,等待最后ICU的介入治疗。 疼痛吞噬了她的记忆。银幕上,父亲一遍遍揉着她因疼痛而痉挛的手,抚摸她的额头。三年后,她对这段观众的“泪点”完全没有印象。 她唯一记得的是,穿着麻质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锦菊,你想不想见毛毛?” 她点头。 “想见就要坚持下去。” 她又点头。 她是产科的奇迹。 事后,好多医生护士跟她聊“八卦”,“在ICU有没有看到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她说,“蓝色的ICU大概就是阎王殿、鬼门关的样子。” 阎王殿最终没有召唤她。11天后,她转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眷顾了“陈小凤”。 孩子抱出来时,护士冲着郑清明喊:“恭喜你,一对姐妹花”。 “恭喜啥,我一点高兴不起来。”他担心的是“陈小凤”。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经历和40公斤不到的体重,害怕起来——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 那一晚,他盯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一宿没合眼。 天亮时,42岁的他,觉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在成为专业妇产科医生之前,李家福做过5年乡镇全科医生。1988年之前,他接生过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三个婴儿。 那时,他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接生。 到了2000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动员产妇到医院生孩子,以降低死亡率。2014年,中国提前一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1.7/10万,较1990年的88.8/10万下降了约四分之三。 在死亡率之外,他逐渐看到了比纪录片“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25年来,他见过数以万计的孕产妇。有做了8次试管才怀上的孕妇,也有14岁就当妈妈的产妇。有陪着小三偷偷来生孩子的,还有带着几个男的来生孩子的,因为不确定哪个是孩子的父亲。 他还常跟警察打交道。2013年的除夕,120送来一个“三无”产妇。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亲人陪护,没有钱。她有的只是一个死在肚子里的孩子和不断的哀嚎。李家福报了警。最终,在警察的见证下,为她做了手术。 最让他惊喜的有两个。一个是三腔心脏的产妇。三腔心脏的宝宝,一般来说活不到2岁。那位产妇不但长大了,还怀孕了。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宝宝出生,“是个奇迹”。还有一个是“瓷娃娃”的妈妈,骨头脆得像玻璃。她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像“陈小凤”一样,随时可能大出血。更可怕的是,她是RHA阴性“熊猫血”。她身材只有89厘米长,29公斤重,最后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宝宝。 社会对缺陷儿的容忍度也在增强。 他曾接生过一个特纳综合征宝宝。她比正常宝宝少一条x染色体。宝宝的临床表现可能是长大以后没有子宫、没有正常的卵巢和阴道,这意味着她将来无法怀孕。她的个子会低于150厘米,智力接近正常。 家属选择要了。 还有一个唇腭裂的婴儿。家属说,“我们一定要,生下来是猫是狗我们都要。”这样的事例总是让医生欣喜。“过去很多人都放弃了,你善待这个生命会有好报。” 最让他有感触的是,在他科室产下先天愚型(唐氏综合征)的一位意大利人。出院后,有一次,产妇把全家7口人的照片拿给李家福看,照片上,孩子笑得很甜。 “在我们国家,类似的情况,产筛出来就是要引产的,但他们看中的是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快乐。”李家福觉得这当中既有生命观的差异,也有福利制度的差异。 《生门》中,李双双一家因为孩子检查不到胎动,加上优生优育的咨询结果不理想,希望引产。“这是因为万一孩子有问题,家庭将来无力负担,社会支持也跟不上。” 从子宫,到阴道。从温暖的羊水,到大气层。在李家福看来,就像两个星轨的转换,宝宝会面临很多未知。有一部分会窒息而死,还有一部分内脏畸形在超声上检查不出来。这是医疗的局限。 在与死神持久的战斗后,妈妈们伤痕累累。 夏锦菊出院时,儿子刚满月。长期卧床使她的腿部肌肉萎缩,剖腹产的刀口限制了她的活动半径——走不出200米,就腹痛难忍。术后半年,儿子都不得不放在妹妹家托管。 “陈小凤”的两个女儿,一个1.6千克,一个1.61千克。“两个加起来,都没别人一个重。”孩子肺发育不好,体质差,医生保守估计,“需要20万治疗费用。” 求子不得的父母闻讯而来,通过护工来打探消息。他们愿意负担孩子的医疗费,并抱养其中一个。 “陈小凤”话不多,只管一直哭。郑清明心一横,拒绝了抱养孩子的人,两个全都抱回家,“生死由命。” 满月时,村里的乡亲去看,没一个觉得能养活。到郑清明家串门儿的妇女,至今记得孩子的“手脚像鸡爪子。” 别人都是两手抱孩子,郑清明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落在手掌里,头枕在他小臂上。冬天寒风呼啸,到了晚上他就把女儿放在胸口,“害怕她们冷,更怕一翻身压死了。” “战争”的奖赏 三年后,当夏锦菊和“陈小凤”作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时,在真实生活中,她们已经带着上一次“战争”的奖赏,投入新的“战场”。 郑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自己瘦了20斤。他天天到村庄附近打零工,盖房子、修路、掏猪圈,来者不拒。即使如此,两个孩子喝奶粉的钱,“还欠一万多。” 他读书读到四年级,认识的字有限。一个“愁”字拆开,成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郑秋、郑心。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郑清明,一手抱起一个女儿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炉子里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烧起来。他揽紧两个女儿,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这是郑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更多时候,两个孩子黏着“陈小凤”。她们比同龄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样抓紧她,把她扯得东倒西歪。孩子调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着哄。只要摩托声在家门前响起,妈妈就暂时解脱了。 夏锦菊成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一个“标志性病例”。 2014年,李家福把她的病例拿到武汉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后来还拿到全国性会议上讨论。 “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变化是,随着二胎孕产妇的增加,疤痕子宫、前置胎盘、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前2500个病例才有一个胎盘植入,现在250个病人里就有一个是胎盘植入。” 除了孕产妇高龄,李家福用高剖宫产率解释这一现象。 “以前只生一个孩子,为了保险或怕疼,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剖宫产率达50%以上。”等到怀二胎时,类似凶险性前置胎盘成了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 夏锦菊一直与李家福保持联系。 因为术后大量输血,她最近刚去“把心肝肺都查了查”,还特意做了艾滋病检测。 夏锦菊1米5的个儿,三年过去,从术后的70斤长到92斤。抱着50多斤的儿子爬楼梯,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 4月份,在县城一家酒楼,她和老公为儿子举办了三周岁喜宴。儿子聪明讨喜,指着不同人的衣服,能准确说出,black,green,purple…… 没有儿子之前,夏锦菊是一个“像骆驼一样”的人。她务实、能干。她和老公在广州做服装辅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红红火火。 为了儿子和青春期的女儿,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职妈妈。 像郑秋和郑心一样,3岁半的儿子无比依恋妈妈。夏锦菊上厕所的时间,他会哭着找妈妈。 理解生育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摄像师赵骅60岁了。 一枚小小的老花镜,腿上绑了黑绳,挂在胸前。两年中,磕磕碰碰,他戴坏了4副老花镜。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没眼镜的时候,全靠在武汉市电视台几十年的经验对焦。拍完《生门》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 他把几十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夫人,撂下大话,“你爱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 1983年,夫人在中南医院生下女儿时,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他没有细腻的体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三十年后,他从中南医院扛回摄像机,妻子看得入神,连“眼睛都不眨”。 一个40多岁的的士司机,老来得子。赵骅跟着他返乡报喜,男人“上山祭祖,鸣鞭。”家族繁衍的仪式感令他动容。 还有一个早产的母亲,通过医院找到赵骅,想看看孩子出生时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赵骅拍下的是那个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这个被他视为女性本能的自然过程,突然变得值得敬畏。“正是这种被忽视的本能,才使我们得以繁衍。”赵骅说。 生育也让走失多年的“陈小凤”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她十几岁时被拐卖,因为不识字,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只记得村外的茶园和门口的大井。 命运诡谲。她冒用的“陈小凤”不但未能给减免负担,还成了孩子上户口的障碍。 她的两个女儿,是“陈小凤”之女。如果要更改出生证明,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并经过亲子鉴定,才能更改。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寻找她出生时的户口,成了解开这个问题的唯一一把钥匙。 导演陈为军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想法。足够多的观众通过《生门》,会达成一种广泛的交流。在电影票房允许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探索成立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救助“陈小凤”一样的困难家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和风险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
3 ) “何不食肉糜”,你需要这样的片子
影片以“命悬”“筹钱”“生男”“引产”四个主题,交叉讲述了产房中四个危急的故事。
“命悬”讲述的是,产妇夏锦菊生产时大出血,面对她要保留子宫的恳求,主刀医生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夏锦菊在手术中,心脏两次停止跳动,最终被医生救活过来。这个故事中,我印象较深的对话是,医生对夏锦菊说:“你丈夫真爱你,听说情况危急,立马从广东飞了回来。”夏锦菊情况好转后,医生说:“你这辈子不会忘了我,我这辈子也不会忘了你。”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但却是情理之中。另外,夏锦菊恳求保留子宫的时候说:“我才32岁,如果是四五十岁的话,也就无所谓了……”我想,如果不是她这么恳求,后来的情况可能还不至于搞到心脏两次停止跳动那么危急。
“筹钱”讲述的是,怀了双胞胎的产妇小凤,面临早产难产的危急情况,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元,而她和她丈夫的家庭是没有多少经济来源的农民家庭,手上只有5千元。一大两小三条人命,医生也想尽快救助,可是不缴费,患者资料都无法联网,更何谈手术。正值村里所有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都是没有什么钱的老幼妇孺,借钱很难。小凤的丈夫以及丈夫的哥哥,走遍了村中的每一户人家,大家把手上的钱大张小张连同钢镚都掏出来了,借到的钱仍然远远不够。其中还有2万块,是20天后某村民就要给儿子娶媳妇用的钱,也借出来救急了。想去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可是至少有两套房才可以抵押贷款,只有一套自住房是不可以抵押贷款的。至于无抵押贷款,需要做过信用评级才可以,这条路也行不通了。最后,还是民间高利贷应急了,但是利息真是不低啊!看到种种这些,我都忍住没哭,知道最后,临床的家属一位大妈,走之前还塞了红包给小凤的丈夫,我就忍不住流泪了。
最终,手术费凑齐了,双胞胎也平安出了危急监控室,一家人高高兴兴回家了。但是,那些债务怎么偿还呢?影片没有说。
“生男”讲述的是,产妇曾宪春已经生过两个女儿了,这次风险很大的生产,因为是男孩,所以一定要冒死生下来。她说:“我们农村和你们城里不一样,如果家里没有一个儿子,哪儿一定会被看不起的。”时至21世纪,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严重,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引产”这个故事中,产妇李双双的家庭是经济情况看起来比较好的,但是他们面临的情况是,优生科医生建议他们将孩子引产,妇产科医生建议他们保留孩子。孩子生下来了,情况不妙,救的话可能人财两空,不救的话,该如何面对今后回想这一线希望时良心的拷问?
在影片结束后的主创交流提问环节中,有个男生对“筹钱”那个故事产生质疑:“现在还有这么穷的人家吗?就几万块钱能把他们愁成那样。我除了去云南的时候看到过一些贫穷的人家,其他的不会这样吧……”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听到他这番话,心里想,又是一个天真地问“何不食肉糜”的蜜罐中的孩子。导演回答,陈小凤正是来自云南,而且她的丈夫是大龄未婚,很艰难地才从云南将她娶过来,婚后还没来得及办新农合医保,就迅速怀孕,并且还是双胞胎面临难产。如果他们家之前办了医保,那么情况会好很多。
我心想,即使有医保,但是在报销之前,也需要自己垫付资金的。在农村,几万块真的是可以急死人的,因为大部分农民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在北京待久了,真是会经常忘了,其他地方还有那么贫困的情况。我甚至很多时候都忘记了,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中文系一年的学费才4800元(远远低于现在某些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然而我和我的父母根本交不出这笔钱,幸好有助学贷款,我才得以读完大学四年,也幸好我考上奖学金,幸运地读完了三年研究生。
看了“筹钱”这个故事,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何不食肉糜”的我们,非常需要这类影片。
今天我又刚读到梁文道《味道》一书中的《贪食恶之首》,其中讲到我们浪费粮食与非洲饥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把饭菜吃完了,地球另一边上挨饿的人就能吃饱了吗?”
再长大一点,我才晓得祖父母那一辈都是经过战乱的人,就算自己没有饿过肚子,也见识过灾荒。如今我们不仅吃得饱,且犹有余裕看美食杂志,寻找最新最奇的饮食信息,恐怕很难想到我们这几代香港人是何其幸运。读一点历史,就知道几十年没战乱没灾荒,大体上没人饿死的时候和地方实在不多,而你和我恰好就活在这样的年代和地点。
全球食物价格为什么会上涨?因为供不应求,我们高价买回的食物,若都是必需的,那还叫情有可原。
每一餐我们吃不下的食物,每一天厨房里过期的菜肉,每一晚超市丢弃的卖剩的货品,全是我们用十亿贫民和许多国际救援组织付不起的价钱抢回来的。如果我们只买自己需要的分量,食物或许不会那么贵,那些濒临死亡的灾民或许就能多活几天……
情况就像一个穿着皮衣的富人和一个赤身露体的穷人在争购一匹布,富人买下了那块布,却在冷得全身颤抖的穷人面前好整以暇地放一把火将它烧成灰烬。
关心现实世界不同境况中的人们,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认清现实,才能更好地认清自我。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影片虽然是纪录片,却有着故事片般的惊心动魄。
导演陈为军曾受BBC、NHK邀请导演纪录片,他的作品《请为我投票》于2007年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另一作品《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曾在海外多次获奖。
剪辑更是由著名的电影剪辑师萧汝冠担纲,萧老师因王小帅电影《十七岁的单车》获台北金马影展最佳剪辑提名。
强强联合,这部影片非常值得观看。只是,观看的时候,需要勇气,以及纸巾。
现实生活远比想象中复杂与残酷,精彩与令人感叹!
母爱是勇气。拍摄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也是勇气。
我已有勇气看完这样一部记录片,你有勇气看吗?
4 ) 生门一道苦一道愁
先从夏锦菊讲起,怪不得李医生喜欢她啊,真的是个超可爱的女人。莫名其妙的言论是女人生孩子是为了男人生的,女人生孩子就是为了自己生的。夏雏菊要死了还要保子宫,哪里在为丈夫和家人的考虑。她只是想要自己再生孩子而已。因为生孩子给了她们满足感和意义感仅此而已。我相信夏锦菊当时恳求李医生的时候并非真的是想保孩子,她只是高看了自己命太好,相信可以两全而不会出危险而已。当然,她命虽然没她想象中那么好,但也真的挺好的233
李双双被优生科建议引产,全家人没有人想要这个孩子,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母爱不是无私的?有些女人就是不会因为怀孕而生出与现实抗拒的勇气。所以再吐槽一句陈导演最后的煽情是不是互相矛盾。在李医生讲完拒绝引产的理由之后,镜头给了李双双年轻的丈夫,从到这里我都相信导演是客观的。我对这个家庭是理解的。因为生和不生是由人自己决定的,我从不相信这里面有什么道德标准。但李双双儿子剖腹出生,陈导演给的音乐实在是有些不该有的主观和略显矫情。尽管最后我改变了对这个家庭的看法。孩子出生,没有动摇他们致孩子于死地的决心,面对生命太过于轻易的放弃。就象医生说的那样,真的不会后悔吗?当然,我的猜测是不会。这个家庭尽管并不富裕但从特写的他爸爸的金戒指上可以说并没有太重的负担。不愿意承担风险而放弃,到了这一步这个家庭已经不值得被同情。
徐小凤的情况应该是里面最困难的。那些说穷人不该生孩子的我真是好尴尬。但是,从徐小凤生孩子的开始这个家庭似乎会永远贫困下去以致下一代。徐小凤所讨论的不是穷人是否该生孩子,而是农村群体阶级固化的一个缩影。我并不认为这里面丈夫的角色都显得有些不尽责,至少我对徐小凤的丈夫还是很同情的,他真的是尽力了。但是穷人的影子在他的身上显现的时候,这个群体阶级的难以上升也被体现的很明显。现实的重压导致他们没有长远的考虑,没有长远的考虑导致对下一代生长资源的匮乏,下一代成长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继续留在农村踏父辈的老路。不幸的是,这的确是农村群体的缩影啊。但我依然揪心与希望他们的孩子活下去,至少没有人钱两空。而关心与农村人没有权利生孩子的,看一看医疗费,大人和孩子都保住至少要20w,我想这个费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笔很重的花费吧。里面有没有明显的制度问题?有的,徐小凤为什么没有医保,因为她是云南人没有来得及办,可是她嫁过来结婚证房产证邻里这些都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非要用走制度的框架去框住。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机械的制度要负责。
至于那对为了要儿子面对风险的。我没有什么批判态度,我愿意相信他们不是为了偏心儿子而要儿子,只是惧怕流言蜚语。但嘲讽的是,徐小凤丈夫的哥哥出去借钱,借来最贵的两万块是朋友儿子娶媳妇的钱来周转。我想说就是有了太多像这样的夫妻,才导致了那两万块为何借来不易。
5 ) 李医生,别来无恙
第一次在豆瓣上评论,为此特地注册账号。 老婆说是她看过的流过眼泪最多的电影,没有之一。原因无它,老婆怀孕时患中央型前置胎盘,大出血入院三次,儿子31周早产,第二次入院就是在中南医院李家福医生手下,对剧中很多病例感同身受。 我是在武昌群星城银兴影城vip厅看的电影,居然全场坐满(当然全场也没几个座位),不知道其他看电影的人是抱着何种心态,反正我是被重新带入到六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中,看完已经是泪流满面,生命不易,且行且珍惜!再次被医护工作者的伟大所感动!
6 ) 生而为人,一定要善良。
几乎是哭着看完全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看到农村的那家因为没钱男人在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行了。还好家里有个大哥撑着,大哥大嫂真的是很仁义的人。农村那家对比那个四眼仔,真的是同样都是人,对待生命对待妻子的差别看着真是让人心寒。农村那个男人在小孩出生以后还是站在产房门口等着老婆。那个死四眼仔孩子出生以后一家三口全都跑去拥孩子,产房门口一个人都没有。这种人真的是活该。电影上面写着小孩不幸夭折,是真的不幸么??就是男的一家人不想救而已。对比那个农村的夫妻,真的想说善良的人可能老天都在帮助他。而那个戴着两个大金戒指还不愿意救自己孙子的人真的是活该。电影最后陈小凤的丈夫去儿科接两个宝宝的时候,下意识把衣服脱下来把孩子裹里那个小心翼翼又喜悦的样子真的是让我泪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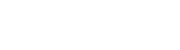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在中国没有钱真是活的太艰难了。
我如果是在生孩子之前看这个影片,我是绝对不会生的...这一扇血淋淋的门,可能通往新生,也可能是通往死亡,回想起来以“上下五千年所有的女人们都能生,我也能生”给自己打气的我,真是年少无畏啊,后怕。
生养不过是本能,神圣伟大个屁!心跳停跳两次都要保住子宫,都他妈6孕2产了还要生,父亲从头到尾都没见人,要生!没钱凑钱,要生!没有儿子,要生!所有女人都失能失智一样躺在病床上麻木或抹眼泪,没有一个女人能为自己说一句话,做一个决定,坚强镇定的说:对我自己生命有危险的事,我不干!
通篇看完,感受到的不是母亲之苦,而是医疗资源的不均衡之苦,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之苦,制度的不完善之苦,普世价值愚昧之苦。在钱与命之间的苦苦权衡,是是时代之苦社会之苦,是如此社会中的穷人之苦。
完美的谨慎婚育教育片,现实意义大于电影本身,没有血腥的镜头,可我中途被吓哭很多次。贫穷和繁殖本能交织在一起,我没有看到任何伟大勇敢,我看见的只有不幸和悲哀。片子里,产妇不切除子宫就可能保不住性命的时候,她居然还让医生保住子宫。简直太基霸吓人了!关于生孩子,你生我支持,让生我不生。
迟到四十分钟。生而为人之前就已经很痛苦。
说到底是没钱…但为什么没钱,太复杂了,电影打开了一个疑问的缺口,照进了这个国家最底层的部分 @2017-06-28 21:33:06
期待了一年终于看到了,没有想到小小产房里外如此多的故事,生之伟大,也有命悬一线。母亲确实不容易,生一次孩子犹如重生,全片克制隐忍,但仍然有不少紧张刺激甚至泪点,也有不少极具现实意味的内容,农村的生育观,产房外的人性时刻,人情冷暖战胜金钱
有人看出母亲伟大,有人看出制度落后。但作为女性更多的是恐惧。陈为军是拍过《请为我投票》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导演,我真诚地不相信他的三观有那么“正”。明显反映出你国两性观和生育观很大问题,片尾一转“母爱光辉”,没有人试图哪怕说一句“这样不对”。受害者有罪论和受害者伟大论一样可怕。
这种片子越多走上最大众化的荧幕 那种短视近利戴着金戒指要引产的傻逼就越少
看着看着看哭了,哭完之后想了想,还是多挣点钱好
人这一生啊,总要做点什么困难的事。
若要论院线大银幕电影的尺度,《生门》无疑是近几年现实主义电影里走得最远的。这个庞杂国度惊人的社会分层、医保体系的滑稽、乡间村落的凋敝、人伦道德的反思,甚至延伸出银幕前观看与被观看的伦理探讨。他同样也是一记对现实版“罗尔事件”的响亮耳光,煽醒整天沉醉于朋友圈自我谄媚的伪中产情怀。
我是含着泪看完的影片,每时每刻无不在惊叹于导演捕捉到了这些无比真实、生动、动人、震撼的影像,从中能感受到了医生的、家人的、宝宝的、陌生人的、以及创作者的温度,这些一同构成了影片的温度。这份温度,是创作的意义,也是生活的意义。
挑的例子够典型,可见花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取原始素材。剪辑的手法也好,把孕产医护拍出了故事性。全程不置入观点(片尾什么情况?)不进行评述,冷静而克制。李主任小天使。PS:前几天才听了一个女方拒生二胎而离婚的故事。同事言“何苦在垃圾堆里找老公”。我问“你指给我周遭哪里不是垃圾堆?”
做丈夫的都不够格,第一个开始有生意走不开,老婆心跳停止了才赶过来?第二个没钱,先斩后奏…第三个怕人才两空,还真应验了…第四个家里就是想要个男孩,生了第三次了, 太多荒唐的事情,表面人性的善面,母爱的光辉掩盖不了存在的问题,女性是伟大的,丈夫请呵护自己的另一半,对每一个生命负责。
生育是一扇门:有人拼命想推开,从此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你一辈子忘不了我;有人死活也推不开,能在肚子里多呆一天,总比在温箱便宜一点;有人想尽办法破门,农村素质低,没有男孩人家就欺负你;有人进了门又想出去,你们拿人性劝我,好像我的道德低人一等。看到新生刹那眼泪奔涌,但太像电视民生纪实。
相信本片能够培养出一批恐婚族,中国式传宗接代实在是太可怕了,口头上说母爱是多么伟大多么充满光辉,然而为奴隶的母亲们却以如此毫无尊严毫不体面的方式迎接新生命的诞生,让人不胜唏嘘。诚然社会在呼唤男女平等,但从性别决定的那一刻起,人生就充满了不平等,没有子宫的男人永远也无法理解女人之殇
每个人都是被动来到这个世界的,家庭除了考虑自身条件,也要想清楚当下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时代的阶层固化。对女性而言更多的是要承担育儿之苦甚至面临死亡的风险。反正我的建议是谨慎要孩子,尤其是二胎。那种不管几个非要男孩不可的都是TM的神经病。最后,致敬片子里的母亲和医生,以及制作。8.8
整个片子看得非常揪心,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真的。生活二字,生与活都很难。同时,又透过生,去看到更多的东西,由于大家立场不同,经验不同,每个人也会得出很多不同的感悟。若说不满足,就是音乐太刻意煽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