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一百年前,黑白默片风靡日本,大人小孩都为之著迷。俊太郎(成田凌 饰)常常鑽进戏院偷听免费电影,不管是邦片还是洋片,总能将辩士的口吻模仿得唯妙唯肖,「旁白辩士」是俊太郎自幼的梦想,长大后却沦落为「冒牌辩士」,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再让小偷趁机闯空门。在某次差点穿帮的过程中,他带著赃款逃到小镇戏院「青木馆」,戏院裡有醉汉辩士、花美男辩士还有肥宅辩士等各种不同风格的辩士,加上电影放映师、乐师以及小气老闆夫妻带他畅游电影幕后世界,但小偷集团、热血警察紧追不捨,童年一起看电影的初恋女孩也跟著现身,还有镇上那新开幕的时髦戏院,老闆的女儿也疯狂地爱上了他,俊太郎的青春恋爱梦该何去何从……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吸血鬼学院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特别篇镇魂曲之九霄琴绝地战警:疾速追击小芳的故事一夜新娘第二季再见危情24小时时髦老爹大雨成灾圣诞快乐快乐之后囧西游之荒村客栈游戏男孩第二季停不了的爱2002冷血坏特工冒牌侦探鱼跃在花见赛琳娜2014野火春风斗古城她的业余爱好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少妇安吉娜欢乐合唱团
长篇影评
1 ) 喜剧之双刃剑
如果说真正喜欢电影的人都会奉《天堂电影院》为神作,那么这部电影就是一部低配版的《天堂》 低配之所以为低配,就在于喜剧这一标签从中作梗。喜剧标签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它成就了许多电影,默片时代的卓别林、基顿,库布里克的讽刺经典《奇爱博士》,还有日本的一系列脱力系电影。但却也毁掉了更多电影的封神之路,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典范中的典范。 不必要的戏剧性冲突,喜剧的过大比重,拍得不够深入,这是阻碍这部电影成功的几个原因。最显著的是临近结尾的那段追逐,镜头分散割裂跳跃,节奏明显已经被喜剧完全带偏,格调一瞬间落入尘俗,可以说是极其失败。 但这部片子的内核还是相当优秀的,对电影历史流变的感慨,对人生无常历程的感悟。还有烧毁影院,储存胶卷等情节,都依稀可以看见《天堂电影院》的影子。 另外这部电影的精彩之处还在于电影虚幻与生活现实的交融。尚且不谈电影最后打破第四面墙的精彩操作,就是男主声音沙哑时和女主的那段联合解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消除影视与现实距离的伟大尝试。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瑕不掩瑜,但明显值得更好。
2 ) 《默片解说员》:新冠下的迷影,这部喜剧给多少人看哭了

从各种短评可见《默片解说员》(カツベン!,2019)给大多数人带来的直观感受都是相近:大呼过瘾。一般又以两种情况为普遍,一种是对于情节高潮迭起莫不拍案叫绝,另一种则带有浓厚的乡愁意味,从片中感受到对于电影的热爱,当然,也看到了某个时期电影发展的情况/奇观。

一段广为人似知非知的电影历史
作为一部致敬早期“辩士”文化的影片,很自然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对电影进行了反身式的检讨。这个检视脉络由永濑正敏所扮演的名辩士(弁士)山冈秋声为主体:作为一位名气大过影片的辩士,山冈曾是影片主人公染谷俊太郎(成年后的染谷由成田凌饰演)的偶像,他长大后有一段时间也以假冒山冈来招摇撞骗,作为同伙行窃的声东击西、转移注意力的道具。待到这帮匪徒遭到警方通缉而染谷侥幸逃亡之后,躲到一家风光不再的影院“青木馆”,重逢山冈本人时,才发现大家误以为堕落的山冈,实际上是“体会到默片本身的魅力不应该被辩士的口才与表演给喧宾夺主”后,才以佛系方式讲解。
不过,本片编导周防正行显然也意不在为辩士历史做出评论,因此山冈的“抵抗”也是相对消极: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消除传奇辩士的传奇。为此,周防安排了一位低调的青年导演二川文太郎(池松壮亮饰演这位戏份不多但重要性不低的角色)作为补充:他在山冈的一次重要的“演出”,即长大后的染谷第一次看到他的“同事”上台解说的场面,山冈仅在他觉得必要之处,小声讲解,这让染谷深受打击,却在散场时,得到二川的掌声。同样地,二川在(为逃避警方通缉而改名为国定天声的)染谷一次成功的解说之后,来到后台一方面夸染谷的解说功力了得,但同时也请染谷高抬贵手,不要以这种方式毁了他的作品。不过,这场成功的解说也正凸显了辩士这个“元素”的力量。

就在国定(染谷)一次救(山冈的)场中得到众人对他自称的解说才能产生认同后,山冈不满地批评国定只在模仿他人,并因此下了严正的批评:“这个世界上不需要两个一样的解说员”,此所以国定才在那场“成功的”解说场,将一部凄美的爱情片讲成喜剧片,也因此才会有二川迂回批评他毁掉一部作品的场面。
不过,在将山冈写成这种自我放弃的酒鬼的同时,还安排了另一位重要的对照人物:青山馆这时的台柱辩士茂木贵之(高良健吾饰演),这位利用他的男色吸引观众的辩士,可说是半吊子版的山冈,只不过刚好拥有著青春的肉体而拥有优势;实际上,他的存在也是一个时代性的符号,他曾抱怨当时(1925年前后)的电影节奏太快,他跟不上,因此,放映师甚至要配合他,减慢放映速度。这也可是看成山冈转变的隐性动机。
于是,可以看出上述几个主要的辩士在片中的功能性,让周防能以不同的角度带入对辩士的现代立场之思考。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于默片本身的独立性(这是在因有伴奏而让音乐成为必然的前提下),以及它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这也会回到影片开始时,1915年的时代背景下,染谷闯入拍摄现场的情况:拍摄活动的匆忙与不严谨,正是因为剧组基本上已将依赖辩士视为习惯,NG画面也能被硬拗成情节的跌宕。而这个独立性层面也顺便讨论默片在叙事上的能力,并且派生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经过十年的发展,默片在装载故事信息的能力大大提升,其前提应该也是观众看电影的敏感度之提升,并且以此回头再去充实默片的独立性。

简单来说,辩士的存在,是基于这个职业必然要在默片作为依据下又要背离它的前提。此所以面对同一部影片,不同的辩士应该存在不同的解说。突出辩士的个人魅力是必然且必须的路径。这才使得影片的主要戏剧冲突得以展现:作为对手的“橘”影院即使拥有更新的硬件设备与资金,却还是得想方设法到青木馆来挖角,举凡乐手,以及更重要的,无可替代与复制的辩士。
说来矛盾,但也正是辩士这个文化,让人们理解声画关系能走到怎么样的极端,几乎要在影片故事时代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在《印度之歌》(India Songs,1974)以及随后的《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Son nom de Venise dans Calcutta désert,1976)展示同一部影片中能让声音跟画面分述不同故事的可能性(这两部片用的是一样的声轨,包括所有的台词、音效与音乐,但影像则是完全不同的;且,即使在《印度之歌》中,声音跟画面已经是在讲述不同的故事了);或者像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和阿侬(Marcel Hanoun)比较不那么极端但却持续地钻研音画离合的可能性——阿侬实际上比杜拉斯更早开始这类尝试,比如1966年的《卡尔·伊曼努埃尔·容克的真正诉讼》(L'authentique procès de Carl-Emmanuel Jung)。
一场让人目不暇给的叙事蒙太奇

然而,即使依旧定调为喜剧片,但本片在剧情发展上可谓峰回路转,基本上用一长段文字恐怕都难简述故事发展。
可以理解周防为了将一段不短且涉及面广的历史,浓缩进两个小时的故事,确实需要加大故事的密度,它的转调之快,会让人在许多看似要落入俗套之处进行新的转折;而在整体构思上,撇除因为过于卡通化而显得太滑稽、不自然的特点(姑且不说是“问题”),回头再想,也基本没有太大的剧作毛病。就好比染谷与栗原梅子(长大后改名泽井松子,由黑岛结菜饰演)重逢的戏,可以预期两人在相认后,应该要聊起十年前的失约以及随后的遭遇,甚至两人值得拥有的一次灿烂的私奔(毕竟染谷藏著一笔钜额的赃款)——哪怕真的发生了倒要困惑后续那么大篇幅的片长要演些什么——等俗套始终都没有发生。
事实上,本片的剧作功力也正在此:透过异种类型的拼贴组合,制造出高反差的情绪转折,完成高密度的调性转换。这里既有成长故事,有爱情成分,也有秘辛揭露,还有犯罪集团与必然的警匪追逐,亦有商业竞争和同行相轻,有逐梦的过程,有缠斗、枪战场面,追根究底,还是一个励志的、关于艺术家的故事。

这种具有转调功能的类型杂揉,其实更在呼应片中一段基本看过都难忘的戏:青木馆遭到破坏之后,老板建议将还能用的胶片接成一部作品,以极大地发挥国定的功力,除了他再没谁能担任这部“混剪影片”的解说员。
这也是必然的,毕竟,国定凭藉著几乎与戈达尔(Jean-Luc Godard)相同的程序,完美体现了“影像书写”的理想。一对在海边离情依依的男女,能在对话中任意插入金发女郎的画面,也可以安插歌舞伎的舞台戏剧片画面,当然跳接钟楼怪人也没什么不可以,只要国定的对白能够牵引出这些画面所对应的意义——有时作为台词的图解,有时是人物内心活动的外化——就可以了。
而这正充分体现了电影的诗学潜能:就像在里尔克一首关于“秋”的诗,一下子讲落叶,然后意象转到手势,再到(殒落的)群星,作为秋之提喻的落叶是理所当然,而它所暗示的重力则引出关于大地与殒星的联想,至于落叶的造型则类聚了最终转喻为从消极到积极之情感的手。

这些八竿子打不著的影像因国定文学性的语言与动情的说白得以撞击出一个完整的宇宙。
周防在这部谈论影史的影片,参考了戈达尔的程序(尽管放映混剪片的篇幅不大),可谓一次成功且低调的致敬;而同时又能藉由剧作的起伏串联起各种电影类型,谁还会特别在意表达情感时过于失真的问题?类型的在场已经确保了典型性人物存在的实质。
这还不说作为后设电影必然会有的套层结构,让片中片跟人物遭遇起到怎么样的互文关系,尤其,影片中直接提及的影片不下二十部,这对熟悉电影史的观众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附加乐趣:得以从互文中去读出正文的层次,尤其在对应到染谷与栗原的爱情上,默片版《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23)——跟有声版一样都是戴米尔(Cecil B. DeMille)执导——的存在绝非只是为了点出故事年代,就像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在片中只是被提到(与被模仿了动作)而一个画面也没看到。这种片中片趣味就跟《默片解说员》的更详细故事,都一并留给读者自己去感受、享受,毕竟本片虽然因像一部压缩过的日剧而饱满甚至超载,但是它仍按周防一贯的作法:化高专于通俗。

不难想像《默片解说员》是如何既掳获喜欢通俗剧的观众,同时又满足严厉的影迷。周防毕竟最早是从戏仿小津出道,也说出似是而非、听起来很像透晰小津的言论:“小津只拍喜剧”,我们理所当然认为周防深黯小津的艺术之道,《默片》中的蹩脚警察,难道不会让我们想起在小津默片中担纲要角的斋藤达雄吗?同样地,周防也深黯不露声色的批判手法,尽管前述表示周防“不在为辩士历史做出评论”,然而,影片最后两位山冈(落魄的本尊与历劫的仿货)的下场,大概也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辩士的某种看法。
3 ) 我们还需要电影吗

/淹然
新冠疫情下看这部〈默片解说员〉,意味非凡。它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有多需要电影,有多需要电影院?
在日本,默片解说员名为「活动辩士」,按电影学者四方田犬彦的说法,「在大城市里,观众是否去看一部电影与其说取决于影片内容,还不如说取决于是哪个辩士解说。」
故事的开始,少年俊太郎与少女梅子穿梭于金黄的树林,这是浪漫的大正时代。他们误闯片场,但这段「节外生技」却被收进正片,当时的辩士大牛山冈秋声将其完美编织进情节序列,套用四方田犬彦的说辞,黑暗里的俊太郎与梅子,与其说是被大银幕上突然跑出来的自己所震到,不如说是被山冈的「辩才」所折服。
这就是辩士的特殊所在。辩士为角色配音,为剧情旁白,又为故事「添柴加火」。他们并非忠实的转译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完成者。电影里有个细节,为了配合辩士的解说速度,放映员还会调整影片的放映速率。似乎相比银幕上超凡渺远的大明星,辩士才是黑暗里近在咫尺的神明。影片的高潮塑造得近乎「神迹」,辩士俊太郎面对不同胶片混剪而成的影片,靠一张嘴巧妙揉捏,抹消掉所有拼接的裂缝。
有人说,放映间孔洞里射出的那束光,宛如上帝之光。迈入花甲之年的导演周防正行,向来对特定技艺和场域抱着浓烈兴趣,〈五个光头少年〉〈五个相扑少年〉〈谈谈情,跳跳舞〉……这些片名本身已泄露出导演的好奇目光。这次的〈默片解说员〉当然也一样,就像人们说的,这是献给默片的情书。
这些年,〈雨果〉〈艺术家〉纷纷向电影告白,〈默片解说员〉又特别在哪儿呢?在这里,电影院像个温暖的子宫,庶民众生得到抚慰。
俊太郎买不起牛奶糖只能用偷的,梅子天天目击陌生的男人出入自己家门,但穷苦的生活没有将少年们打翻在地,因为还有电影,还有电影院。俊太郎与梅子被黑暗里的光拯救,一个立志要做辩士,一个立志要做演员。透过大银幕,少年成功从现实里偷渡,彼岸是电影的光。
十年后,长大成人的俊太郎果然成为辩士,从假冒辩士成功晋级为独当一面的王牌辩士,美人胚子梅子也变成镜头里的纤纤伊人。不变的是,电影院还是热闹鲜辣,人们在其中狠狠地笑,狠狠地哭。帅气辩士茂木登场,少女为他疯狂应援。群体性的致幻与癫狂弥散开来,好像生活的疼痛因在场的一百个观众而稀释掉,从电影领受的快感又因在场的观众而放大了一百倍。
俊太郎被仇家陷害,弄哑了嗓子,勉强上台解说引来嘘声一片。梅子适时登场,为俊太郎卸掉重担,两人配合默契。银幕上演着凄美的爱,黑漆漆的电影院擦亮二人内心的火光,想象的爱与现实的爱,镜头内外遥相呼应,周防正行把此处拍的就像个盛满祝福的教堂。
显而易见,导演想要在最大程度还原默片灵韵,充满温润的怀旧之光。这里流动着一种久违的童年目光,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靠人物动作引发喜剧(比如俊太郎与茂木的抽屉攻防战,比如俊太郎滑稽地骑行着缺少踏板的单车),让人找回看一代笑匠巴斯特·基顿的快感。不过,正所谓情深不寿,柔光背后,危机四伏。
俊太郎多年后重逢偶像,这时的山冈沦为臭熏熏的酒鬼,但正是这个被酒精浸泡得迷迷糊糊的人,却是罕见的清醒者。他批判俊太郎塞进了过剩的解说词,电影的迷人之处正在于通过画面与镜头完成无声的自我解说。此处的情节发生设定在1925年,距离1930年代有声电影登台、辩士制度化为历史尘埃已不远,但大部分人对即将到来的衰亡还浑然不觉。
山冈发出了本片最悲丧的宣言,辩士离不开电影,但电影却可以没有辩士。
一切都在默默滑向坏毁。俊太郎与梅子没有走到最后,俊太郎为当年的偷盗之罪而黯然入狱,梅子等不到爱人赴约,独自踏上滚滚向前的时代列车,摇身变为独自闪亮的明星。
所以,要说是给电影的情书,周防正行的字里行间也不单是一腔激情的热昏,还有向着现实的隐忧。比较少人知道,周防正行是靠着拍粉红片闯出一片天的,〈变态家族〉是小津的情欲变体,将洁净饭桌下的隐秘暗流统统端上来。
人人知道辩士制度不复存在,而俊太郎与梅子的爱情也归于寂灭,这些在全片对旧时代的明亮赞颂里,是挥不去的暗沉杂音。或许,周防正行也在借默片与辩士的死亡,隐隐诉说着镜头外的隐患。
四方田犬彦认为,九十年代的日本电影迎来某种复兴:1998年观众人次超过一亿五千万,宫崎骏在前一年凭〈幽灵公主〉创造票房纪录,同时,日本也自五十年代后,再度在久违了的国际电影节上屡获殊荣,比如今村昌平的〈鳗鱼〉,北野武的〈花火〉。而这一时段,周防正行的〈谈谈情,跳跳舞〉和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也在海外取得发行成功。
周防正行曾感叹,「那时工作机会少,当粉红电影副导演都算是抓住了机会,要感激涕零。粉红电影如今没落了,现在的年轻人啊,甚至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整个日本似乎都进入了一种惫懒的超稳定状态,电影界还有像是枝裕和、三池崇史这样不同类型创作人汇成的多元化生态,老一辈的山田洋次也还在持久耕耘,但就是少了九十年代那股生猛活泼,束手束脚的保守也是清晰可见的。
追念过去,是向现在发话。〈默片解说员〉最后以稻垣浩的话做结,「因为有辩士的存在,日本从未有过真正的默片时代」,周防正行或许借此想问的是,现在的电影发出的声音何在? 原载〈北京青年报〉

4 ) 闹剧包装之下的理性回眸
电影史有过默片时代。 但是日本电影没有真正的默片,因为那时日本有一个特殊的职业——解说员。 解说员不是配音演员,不是只念旁白和对白,而是在现场乐队伴奏下,看着影片讲故事,有点像动版的看图说话,或者是配了画面的说书人。至于讲什么,怎么讲,都由着解说员自由发挥。所以把凄美爱情片讲成滑稽搞笑片也是可以的,只要观众高兴。 那时日本的“影迷”,很多是“解说员迷”。他们不是来看电影的,是来听解说的。为了配合解说员的发挥,电影被剪裁,倍速或者慢速播放,也都是可以的。 讲老电影情怀的,远有“天堂电影院”,近有“一秒钟”。这次周防正行把感怀包在了喜剧里。喜剧效果很好,也很日本——那种傻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骗子、盗窃集团、警察,三个各有特色的前辈解说员,还有男主的想当演员的初恋、迷上了男主的戏院老板的女儿,影院老板和老板娘、乐队……看这阵仗就够热闹的。 热闹多了,片子的“情怀感”就不那么明显。高光时刻本来应该是男主染谷俊太郎解说“杂拼片”,但是观感上,之后的那场追逐戏才是高潮,因为实在是太好笑了(此处其实致敬了卓别林和基顿的喜剧默片)。 本片确实没有别的情怀电影那么多让人感伤的点,但是我觉得导演的目的也并不是做一部感性的电影,喜剧外壳下,对旧日时光的缅怀、对解说员的致敬,都是很理性的。 胸怀梦想的俊太郎是喜剧的感性的那个壳,俊太郎的儿时偶像——解说员山冈秋声则是内里理性的那个“意”。山冈昔日名噪一时,现在终日买醉,最后转身离去。他说:没有解说员,电影还是电影,但是没有了电影,解说员什么都不是。这是他对这个职业前景的清醒认识,也是对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解说员变为表演的中心,对于电影是不是一种干扰和不尊重。所以尽管他能用七种声线演绎一部电影,却宁愿只在必要时低声地寥寥讲解几句。 我猜导演是认可这种质疑的,片中那个小角色——青年电影导演,似乎代表着导演本人。山冈低调的解说引起了观众(听众)的不满,他却鼓掌。俊太郎用颠覆式演绎把全场观众逗的人仰马翻,他一面赞扬俊太郎演出精彩,一面请俊太郎高抬贵手,不要毁了他自己的作品。那种毁坏式的重构,我都有些目瞪口呆,恐怕没有哪个导演会愿意自己的作品被这样搞。 不过山冈本人也是矛盾的,俊太郎的第一次解说,被他批评是“模仿”,说世界上不需要两个一模一样的解说员,似乎是对“再创造”的一种鼓励。正是在这种鼓励下,才有了俊太郎下一场的颠覆式表演。解说依附于电影,其要自我发展又会逾越和破坏电影,就像藤本植物绞杀宿主植物。 片中确实有一场脱离了电影的解说,影院的片子都被盗窃集团毁掉,大家把支离破碎的胶片粘在一起,再由俊太郎用激情澎湃天马行空的“意象式”解说把毫无关联的影像串联起来。串联的秘诀在于抛弃影像所有的表层信息,直抵其背后的意义或情感。哀就是哀,爱就是爱,不管银幕上出现的角色是钟楼怪人,还是农夫或者艺伎。 如果没有解说,戈达尔也没法这么拍。这是导演对解说员的才华的最高致意吧。 既肯定解说对于电影发展的积极作用,赞赏解说员的才华,又质疑其破坏和消极的一面。对于这个特殊的存在,导演的态度是很客观的。整部片子其实是外表浮夸,内里持重的。 影片最后,因为旧日罪行入狱的俊太郎在监狱里绘声绘色解说着,没有影片在播放。隔壁,已经跟着青年导演去拍电影了的昔日恋人听着会心地笑了,没有见面就离开了。仿佛历史的车轮向前驶去,解说员被留在了旧日尘埃里。现实中,有声电影的到来,彻底终结了解说员的时代,解说员们都改做他行。尽管注定结束,但是感激和怀念还在,就像他之于她。 2020.12.25 日本电影展@东方广场百老汇
5 ) 有关弁士的一部电影
很多人评论这部电影又想拍情怀,又想做成喜剧,所以各占一头,然后都没有骚到痒处。我反而是觉得将喜剧和历史融合的这种方式挺好的,让观众很能看进去,如果仅仅是写默片解说员,又会不会稍微显得有点无聊呢?
故事背景是1910s到1920s,是处于默片的时代,有的国家就光放默片就完了,毕竟其实也能看懂,但是日本有一个叫弁士的职业,也就是电影的名字——默片解说员,弁士不仅要现场为电影里面的人物配音,还要配旁白,不过由于字幕很快就普及了,所以弁士主要是在日本非常流行,就像一种特有的文化一样,准确的说都不叫电影,那个时候叫写真活动,电影院也叫xx馆,比如此片中的橘馆和青木馆。
男主染谷俊太郎和他的青梅竹马栗原梅子小时候经常偷偷溜进戏院听免费电影,10年后,男主由于有当解说员的天赋,被拉入伙,可惜碰到了坏人,他只是个冒牌的解说员负责吸引注意力,其他人负责偷东西。后来男主逃到了青木馆开启了新的生活......
我想到了去年上映的《一秒钟》,里面满满包含着张艺谋对胶片时代的情怀,这部电影也一样,也有着对默片时代的怀念,并且还夹杂了许多细节,这部电影说明了弁士不仅仅要讲台词,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风格,可以自己发挥让观众有更好的理解,影片中提到模仿一词,因为男主模仿能力极强,但别人说他应该用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开始了一种非常俏皮,非常搞笑的解说,把故事讲的生动形象,这个可以类比唱歌,有的人模仿能力强可以模仿有的歌手的唱法,但那不是自己的。
周防正行并没有用一种特别严肃的方式拍这部电影,其中有许多的闹剧许多的笑点,让人忍俊不禁,特别到电影高潮部分,就整个跟喜剧片一样,其实这是要卖座所需要的,所以我并不反感这种做法,在笑声中同时了解了那个时代,了解了这种职业,有何不好呢?
6 )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电影版释义

2019日本喜剧片《默片解说员》,豆瓣评分7.7,时光网评分7.4,IMDb评分6.2。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电影版释义。
一部题材非常新颖的喜剧片,有些像《天堂电影院》,是一封献给老式电影年代的情书。以默片讲解员为题材的电影,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很开眼界,通过本片了解到了在有声电影之前的默片时代的特殊职业。
默片解说员可以说是配音演员的雏形,但与配音演员不同的是,默片讲解员负责整部影片,独挑大梁,既要给角色配音,还有负责过场讲解,这很像说评书,可以说是与影像画面同步的评书,评书和配音的混合体。
一个好的默片解说员,可以赋予平淡的影片以新的魅力,也可能将优秀的影片化为平淡,是默片电影院的灵魂人物,可以让电影院起死回生,也可以让电影院由盛到衰,本片将默片解说员对电影的作用、对电影院的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有两个喜剧桥段非常好笑,一个是柜子抽屉桥段,构思新颖,前所未见,笑点突出。另一个是片尾混乱高潮戏。在混乱高潮戏之前,影片是轻喜剧风格,混乱高潮戏则将影片推向令人捧腹的爆笑风格。
女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童年女主还是成年女主,选角都非常的质朴,不算漂亮,但是非常淳朴,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相貌,让人看着很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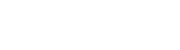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欢乐度和迷影度都卡在一个有点尴尬的位置,没搔到痒处。
勉强三星半,挺好的一个题材,可惜拍成了轻喜剧,挺闹的,挺浮的,滑稽大于情怀,人和电影的情感没出来,没有动人的地方,外景部分调色太过了,饱和度失真,田野、植被黄苍苍的,有一种数码的廉价感,整部片子应该是在某个影视基地拍的,服化道凑合,城镇、街巷、屋宇都太新,没有居住的“人气”和生活痕迹,浓浓横店风那种。同样是拍关于电影的故事,深作欣二《蒲田进行曲》、山田洋次《电影天地》那种就高明很多,周防正行这一代导演去拍大正故事、昭和男儿之类还是差很多功底。
女主有点像二宫和也
讲述一个电影解说博主转型电影混剪博主的故事。唉,没什么意义,就像山冈所说,解说博主是依附电影而活的,电影则可以独立于解说而存在。针对这一议题的解决方式竟然是转行做电影混剪,可混剪不也是依赖于电影而活吗?除非你去当导演编剧和演员呀?爱电影的是模仿别人风格的男主角吗?竹野内丰演的警察,偷偷剪下喜欢片段收藏的放映师,最后慢慢远去的山冈,他们才是真正爱电影的人吧。
这是一部活动弁士的童话,选题和剧本有三谷幸喜的调子。优点是抓住了几位不同风格的活动弁士的特点,声优演绎声情并茂。故事后期,就像老弁士和警察所说的那样:“电影已经很完整了,我们的解说对于电影来说是必要的吗?”及“电影在银幕上完结了,但人生还可以有续集。”可惜只是落在台词上,并没有展开去表现这些论点。喜剧风格倒是让人乐在其中,我能够在每个细节上感受到对电影的热情,尤其对弁士这个职业工种的演绎。但是人物塑造还是很脸谱化,结尾剧情处理过于闹腾,动作戏想要营造的默片感处理地并不理想。彩蛋是日本经典默片《雄吕血》,巧的是去年在海南节看过日本弁士名家、古典钢琴和琵琶的现场演绎,与今年看这部片形成了一种互文。
1、那时,默片还不叫电影,叫“活动卡片”,解说员动之以情的旁白使无声的黑白影像充满感染力,不过这终究被技术的发展湮没在影史档案里尘封遗忘。所以,本片的取材就显得尤为珍贵,狭义上是对默片解说员这份职业的崇敬,广义上是对整个电影史的致敬。虽然本片很多笑料既巧合又闹腾,但这恰恰也是致敬许多老默片里滑稽可笑的段落。2、成田凌从街拍男模转行男演员,虽然有点小发福,但演技那是杠杠的!太可爱太秀逗啦!会大红!3、看完,想尝焦糖牛奶糖的味道~
周防正行新作,聚焦大正年间影院中的职业辩士,对电影童年时期的一次充满深情的回望。影片或许不够深刻,也不无套路,但足以值满五星。辩士的确能让默片变得更有魅力,甚至能用比影像更强势的文本来重塑电影,至于是否属于”创造性误读“,便见仁见智了。但这个职业注定短命,一如影片结尾的没落与新生。致敬多部经典默片(多为文学改编,可见早期故事片尚依赖于文学),放映员的私藏宝贝+混剪胶片+影院起火似[天堂电影院]变奏。黑岛结菜(真的不是松冈茉优双胞胎吗)的救场模糊了辩士与演员的边界,而在银幕裂开之处的不自觉表演又冲破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银幕中的角色恍若遁入现实。警察、匪首与俊太郎分坐人力车、三轮车与无脚踏板单车的追逐戏太喜感了。牛奶糖是幸福之源~ (8.8/10)
#24th Busan IFF# 亚洲电影之窗世界首映。今年釜山的最后一部。迷影情怀片,故事嘛编得还算圆,看看就行,残片混剪解说那段简直要笑死了(其实也有些cue[天堂电影院]的意思了);最有趣的是导演用了很多模仿默片打闹喜剧的桥段,调度乃至运镜方式都很像,看得相当愉悦。最后专门致敬了[雄吕血],不仅片尾调用了影像,片中还专门给二川文太郎写了一个角色。
12月29日晚,约小学妹出来看展,她第一次在上海看展,也是第一次来大光明,电影很好笑,这是个快乐的两小时。在回来的地铁上,她不说话,也不看我,也不看手机,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也没鼓起勇气拉着她的手…希望以后不要后悔自己没做很多事情。
“电影曾经是无声的,但在日本几乎没有这个阶段,因为有弁士的解说。”怪不得日本配音行业这么发达,原来早在默片时代,电影放映时就有专人进行现场配音,而且会像落语家一样一人分饰多角讲故事,这群人被称为“弁士”。2019BIFF
电影恒久远,弁士永流传。周防正行的《天堂电影院》,比山田洋次的《电影天地》更好,临近结尾的一段混剪太好了。银幕上的人在看默片,我们在看他们,那么多套娃视角,百分百为了影迷。只是没想到拍成了喜剧,手法也致敬了卓别林的滑稽喜剧,但结局还是落了地,从电影梦里走出来,“电影在银幕上完结了,但人生可以写续集”,解说员的悲梦,女演员的圆满,我以为在看性转版沟口健二,笑到泪流满面。
《変態家族》多年後再向日本電影開玩笑,說默片時代,憶起的反而是90年代那些善解人意,固守電影是娛樂又追求藝術和風格的導演們,愉悅觀眾,那是北野周防黑澤岩井的年代(令人懷念在戲院內欣賞這群導演的體驗),而不是河瀨青山是枝多少曲高和寡的作者類型,但當去到最後青年和女演員無法開花結果才意識到,這是周防正行的電影,失敗論者的周防,如宿命一樣要一次又一次推向令人失落的結果,但如果這成為恆常甚至執迷不悟地要一次又一次發生,這究竟是體悟人生失敗,還是失敗只不過作為「作者色彩」的操作而要如此這般地做下去?《Shall we ダンス?》讓人笑中有淚是對中年人危機的觸覺和無奈,《それでもボクはやってない》是現實的荒謬和真實壓倒虛構的對抗,《カツベン》對失敗發生的必要,反有一種他的時代已經過去的感概...
千人场爆笑,迷影梗永远击中心扉,大量默片痕迹(还魂基顿动人)圈粉太厉害,古早混剪+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之开挂剧本目瞪口呆,全员卡司可爱,几乎重拾对日影的信心。四方田犬彦在《日本110年》中写:“辩士绝不仅是老实地复述电影的故事,作为表演的主体,他还积极地介入叙事。辩士或者按照自己的讲解内容随心所欲地调节电影的放映速度,或者对故事本身评头论足,夹叙夹议地提示观众应该如何理解。 ”即使在辩士保留期更长的日本,遭遇有声时代仍是大考验;所有未完成的心愿,相遇又分散的人,通通在电影中重逢,在画框内外交汇,梦境从银幕延续到现实,周防正行竟然在新世纪20年代前夕回春了。
电影太可爱了,也有很多感动,我觉得它不只是写给日本电影默片时代更是写给世界电影默片时代的一封情书。它癫狂又如何,那时的电影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在真实人生中,你可以继续拍续集。”
永濑正敏的角色很有趣,但是这个角色不是展开的重点。导演在动作戏上加入了默片元素,娱乐性不错。
【2nd HIIFF】轻松幽默酣畅淋漓,导演了解了默片解说员这个职业后又加了很多故事逻辑上去,在模仿中致敬了默片时代的转场等表现形式和叙事风格,又在后来“混剪”中让一百年前的人做了现在我们在B站做的事情。最后一段追逐戏非常有意思,又融入了日本民族天生的可爱幽默气质。爱了!
又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对电影院的爱。默片的,辩士的,在当下,尤其感动。
4.5 个人的周防正行的最佳。可以看作年代更早的《魔幻时刻》,闹剧的语法看似疯癫却又有所节制,讲述天真悲壮的赤子迷影情结,到最后生发出一种必定走向悲情的宿命感,的确产生了够震慑的效果。最有力量的就是那些俗套的错位、互文和闹腾的喜剧段落,处理得酣畅淋漓的同时又特别微妙。成田凌饰演的这个把口红印当血的男主角,一定是近年最有趣、最值得铭记的日影角色之一。
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田凌,浮夸又万人迷的高良君,从默片里的第一次露面美到最后蒙着黑纱侧颜的小结菜,高段位粉丝井上Mao,以及藏在默片里的隐藏卡司上白石萌音&成田优。最高的解说,“入画”和“混剪”。俊太郎说,就算太阳有不再升起的一天,男女之情也不会消失。我想说,就算永远不谈恋爱,也无法停止看电影。梅子说,幸福是焦糖牛奶糖的味道。而我想,对影迷而言,幸福是座位最后方投射到眼前的那一束束光,由接续的胶片在黑暗中显影的那一个个瞬间。要永远爱电影啊,直至生命枯竭。
【北京电影节展映】辩士,一种曾在日本与日治台湾兴盛的影院解说职业,如今早已消亡。辩士可以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令默片剧情更加生动感人。也能狗尾续貂画蛇添足,肆意篡改糟蹋剧情。本片即是向这一行业致敬的挽歌,用荒唐喜剧的形式去呈现其最后的黄金岁月。高潮戏份过于日式夸张闹腾的拍法冲淡了情绪,令致敬变成闹剧,遗憾。反派女子那一吻,竟让我穿越到几天前看的《黑客帝国2》中莫妮卡·贝鲁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