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埃里克森牧师在瑞典一小镇宣扬基督的爱,认为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但围绕在他身边发生的事却弥漫着世界末日的气息,因为他与人全无沟通。上承《犹在镜中》,下启《沉默》的《信仰三部曲》中间作品,场景集中(室内剧形式),时间短促(发生在一天内),虽然简洁但传递出深刻的涵义。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沉睡魔咒天下第一情良缘知己东方秃鹰粤语猎犬2020千年白狐2018大侦探波洛第七季女子美味汉堡部海底大揭秘第五季向日葵之丘·1983年夏鸭去京都:老字号旅馆的女老板日记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塑料海洋伪梦迷情禁止吸烟2014孤注一掷:托特纳姆热刺爱在希腊海岸线交通警察宝葫芦的秘密粤语修复生命纸牌屋第二季墨东绮谭帝都神魔传阿尔菲石榴树上结樱桃终有一天2019生命的火花
长篇影评
1 ) 影像的延遲
這部電影有兩條線索,它們相互交錯,相互拖延、啃咬著對方。一條線索有關上帝的存在,或生存意義的問題,另一條線索則是愛的問題。我們暫且稱第一條線索為A主題,第二條線索為B主題。
A主題首先出現在患有憂鬱症的男子及其妻子前來尋求牧師幫助的時候,面對一個處在信仰危機之中的教徒,牧師將約談時間定在半小時後,並焦慮於自己是否只能說出一些空洞無意義的話。這種焦慮暴露了牧師本人跟求助者一樣,對於上帝並無真正的信心,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困擾他的是「上帝的沉默」,是上帝與人間事務的隔絕。
然而A主題的發展被打斷了,在等待與求助男子會面的過程中,牧師的情人瑪塔來找牧師,雖然牧師以生硬的態度拒絕了瑪塔,但瑪塔留下的長信讓牧師深深震動。這封信向我們初步呈現了B主題,瑪塔不棄不離地愛著牧師,並將對牧師的愛作為其人生的唯一目的。我們都知道「上帝即是愛」這一基督教觀念,然而B主題在此卻是跟A主題隔絕開的。換言之,如果愛正是對上帝之存在的確證,那麼尋求確證上帝的牧師卻恰恰極為固執地拒絕了來自瑪塔的愛,與此同時,展現出這種愛的瑪塔卻又是一個對上帝持懷疑態度的非教徒。
在牧師剛讀完長信而處在B主題的震撼(與抗拒)時,又馬上被A主題打斷。對人生意義感到絕望的男子來訪了,然而面對這個求助者,牧師竟傾吐起了自身對於信仰的懷疑。在這裡初步顯示出B主題對於A主題的影響,實際上正是瑪塔所展示的愛的力量,格外讓牧師感受到了自身對上帝之信仰的脆弱。求助者與救助者的位置瞬間顛倒了。來訪的焦慮男子不知所措,奪門而出。
緊接著,B主題又再度出現,不棄不離的瑪塔希望追隨牧師一起去另一處佈道場,但牧師仍試圖拒絕。就在這膠著的時刻,A主題忽然以強力而極端的形式回歸,有人來通報求助男子的死訊。求助男子可以說是在求助牧師無望的心境下自殺的,他的死亡意味著A主題的崩塌,牧師的事業徹底失敗了。
有趣的是,在牧師趕往事發現場,並幫忙守護屍體的過程中,影片有意讓有些誇張的溪水聲淹沒了絕大部分的人物對話,而牧師的形象亦僅僅被從遠景的角度處理為一個生硬的剪影。在此,影像與話語的同步性被切斷,之前一直極為緊張、迫切的凝視被抹除、延遲。然而這段情節卻是全片隱秘的高潮,在守護屍體的時候,牧師的內心世界無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種變化接下來通過牧師的爆發而顯現。牧師向來對於瑪塔的追隨,只是勉強而生硬地予以敷衍,然而這時卻突然爆發了,並以極為直接的語言傷害了瑪塔的一片真心。在此我們領悟到,在那影像延遲的高潮中,實際上發生的是A主題對B主題的入侵。確切來說,牧師向來是一方面僵硬地維持著對上帝的空洞信仰,另一方面則生硬地拒絕著瑪塔的愛,這兩者是共生並存的,於是當上帝的堡壘驟然崩塌,那麼牧師就不得不直面後者,因而笨拙地採取了粗暴的形式。
不過,固然粗暴,卻畢竟是面對了。於是當一切似乎都要結束的時候,牧師卻奇蹟般地、卻又好像是極其自然地轉過身,主動向瑪塔發出同行的邀請。
在電影最後的場景中,牧師和瑪塔各自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們都遭遇到了懷疑論者對宗教意義的嘲諷。牧師所聽到的是耶穌臨死前被眾人拋棄的孤獨處境,而瑪塔所聽到的,是對上帝即是愛這一誡命的調侃。換言之,A主題在牧師那裡被剝離為絕望的虛無,而B主題與A主題發生連接的可能性則在瑪塔面前被被棄置。
最終那個帶著和解色彩的佈道儀式不應被簡單解讀為A主題與B主題的融合,亦即上帝就是愛這一命題的證成。牧師對上帝存在、對生命意義的探求與瑪塔對牧師的愛,都是單向而無望的,我們不應通過將兩者直接同化而自認為解決了問題。牧師在失去對上帝信心的狀況下仍然主持了佈道,而瑪塔則在樂師對宗教意義的嘲弄下,成為唯一的聽眾。在此,佈道儀式不再作為對上帝存在的確證,而是成為一個純粹的場所。
A與B應該在這儀式的場所中真正相遇,儘管結果充滿未知。
2 ) 当信仰丢失了时
研究生时,上男神的课被男神问到为什么会选择和电影相关的课程,答曰,只是想要看懂那些我看不懂的电影。博格曼的电影位居前列。这次终于有机会在电影院看了冬日之光。
最近在看一些电影的时候总是在想,内地究竟有没有对应上的风格。比如看完《东京物语》包括侯孝贤的作品时就在想内地有没有相关的,平静记述的这种类型的电影,这次看完冬日之光,也在考虑我们是否有拍过信仰缺失的电影,想来,作为一个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的国家,可能信仰最缺失的时候也就是在文革吧,又刚好遇到文化管制。这个点日后可以好好挖一下。
3 ) 上帝失声
上帝失声
“信仰三部曲”是伯格曼电影生涯中的又一座高峰,独立成章时能在宗教思辨与人性哲思上独当一面,串联成片后又在同一主题下汇聚出强劲的穿透力。虽然承上启下的《冬日之光》在评奖上未能承继《犹在镜中》的好运,但并不能否认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
这部电影的瑞士原名“Nattvardsgästerna”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英文名片“冬日之光”,二是指在圣餐典礼间的心境,或者直译为“受圣餐的人”、“教友”或“信使”,也不无不可。
既然要探讨上帝存在与否,以中世纪戏剧为雏形的《冬日之光》索性把故事背景架设在瑞典小镇的教堂里,由御用男演员甘纳尔·布耶恩施特兰德担纲主角牧师托马斯。托马斯身上有着强烈的矛盾性,作为神职人员,他向信众布道,主持圣餐礼,还要为人解惑,但另一方面,当妻子去世后,最初因为家人才当上牧师的他逐渐丧失了对主的信仰,深陷重重怀疑,备受折磨。甚至,当深受中国研究原子弹困扰的约拿在妻子建议下咨询托马斯,对方反而向他大吐自己怀疑的苦水,最终约拿走向自杀之路,这一段极尽无奈的嘲讽。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托马斯迷失的同时,他身边最紧密的三个人都看得清透,对于信仰的思量,也有了不同的参照体系。
依恋他的玛塔并无强烈的宗教信仰,前往教堂只为托马斯。但这份感情是不对等的,哪怕玛塔愿意做他“顺从的奴仆”,以此作为“生命的意义”,托马斯对此只感到强烈的厌恶。他丧失了爱人的能力,枯萎死寂的心境让人惊恐。最终玛塔说出了真相,托马斯没有办法活得下去,因为什么事都没法救他,他只会把自己恨死。后来教堂的琴师在玛塔面前说,恰是“爱”毁掉了托马斯,这种论调嘲讽的正是“上帝是爱,爱是上帝”,顺理成章地接续了《犹在镜中》的辩题,尽管持了相悖的方向。
而托马斯的助手艾格特最后所谈及的疑惑充实、固话甚至升华了全片的思考。艾格特新近读《圣经》,觉得每天与耶稣在一起生活的人都不理解他,还在最后弃他而去。耶稣死前,天问没有得到上帝回应,最终,耶稣在怀疑中死去。这一说法也呼应了托马斯长久思忖的困境,两个角色的重叠,带出沉痛感与无力感。而跳脱出宗教主题,这种世俗命理还是能够唤起现代人的共鸣。
在已拍摄的众多电影中,《冬日之光》是伯格曼的最爱。他曾表示,即便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再回头看《冬日之光》,仍然令人满意。那种“完整,没有变质”的论断,指向的便是这种超越时空的对话可能性。
电影拍摄之前,伯格曼在斯德哥尔摩剧院,努力研究美籍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圣诗交响曲》,他觉得这部作品相当了不起,而《冬日之光》也受其启发。早春时期伯格曼开始筹备《冬日之光》,他常在乌帕岭那一带去探寻各家教堂,在那坐上几个小时,思索如何为电影收尾。那时伯格曼的母亲因为心脏病发作而住院,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但即便需要借助于拐杖与矫形鞋,他还是会竭尽所能在皇家礼拜堂内履行职责。某天伯格曼带着父亲前往教堂,结果牧师因病迟到,并说只能做一个短礼拜,不领圣餐,伯格曼的父亲愤而争辩,继而协助主持。当唱完圣诗,他转向所有人平静念到:“神圣的主啊!天地之间充满你的荣耀。荣耀归于你,噢!至高无上的主!”恰是这一幕,给了《冬日之光》绝好的结局。
《冬日之光》的剧本从7月初写到了7月28日,效率非常高,毕竟,这部电影虽然看似很简单,但是包圆在促狭空间中的故事相当复杂。
在最初,伯格曼想过场景会是一座废弃教堂,大门常闭,内里放置一架破旧的风琴,长椅间有老鼠四处流窜,而主角则被自己锁在此间,面对种种幻觉。这种于死寂中对峙的设置,在伯格曼看来,也许更像是剧场的模式,而非电影的做派。但从《犹在镜中》那种信仰的质问转到《冬日之光》这种世俗的诘问,伯格曼觉得还是要选用不一样的场景和光线。
他急于表明这两部电影有着极大差异,并在《伯格曼论电影》中评论说,“充满着虚矫的《犹在镜中》,具有浪漫而且卖弄风骚的调性。没有人敢说《冬日之光》也有同样的缺点。两部电影之间唯一的关联,就是前者是后者的起点。那个时候我已强烈地想摒弃《犹在镜中》,只是尚未对外宣布而已。”兴许,这也是为何伯格曼并不赞同把他这两部作品连同《沉默》一起并称为三部曲。
然而,伯格曼当时还罕见地为《犹在镜中》摇旗呐喊,说是这部电影无论是技术还是戏剧角度去看的话,都无可指责。对比来看,伯格曼自身趣味与思辨角度的更变,其实非常迅疾。不过,当时《冬日之光》被外界排斥的程度反而很高。对伯格曼来说,正巧制片组的负责人患病,他获得了随心调配资源的权力,于是愿意破釜沉舟地拍摄《冬日之光》。这是一名电影人的坚持,哪怕他长久以来都在努力讨观众的欢心,但当《冬日之光》需要冒险的时候,仍会决定放手一搏。
这种情况下,老搭档布耶恩施特兰德也经受了不少煎熬。托马斯缺乏同情心,布耶恩施特兰德在诠释的过程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甚至会出现记不清台词的状况,对于身体抱恙的他来说,确实不易。为迁就他的身体状况,伯格曼选在在白天拍摄不长的时间。而镜头架设在阴霾与雾气之下,反倒造就出迷蒙但特殊的氛围,这样萎靡的气质,恰好契合托马斯本人,甚至现实的绝境。
诚如伯格曼当时的妻子凯比·拉雷特所说,“这是一部杰作。但这是一部沉郁的杰作。”
(连载于《看电影》)
主要参考来源:
《魔灯:伯格曼自传》
《伯格曼论电影》
《英格玛·伯格曼》
Google、Wiki
IMDb、豆瓣、时光等电影网站
4 ) 光线穿过《冬之光》
《冬之光》保持着伯格曼“室内剧”的特性,人物关系单纯,故事结构单一,以内景为主,对白冗长,主要人物都内心丰盈。但是,我一向就觉得,室内剧场景的单一,并不意味着画面或者镜头的单调。在伯格曼的电影中,一些细节的处理,让室内剧的场景和人物细腻的内心化的表演相映成趣,既增加了画面的层次和内容,也丰富了主题的表达。在《冬之光》中,这样的细节元素非“光”莫属。
整个电影的故事,都是发生在瑞典冬日的一天,纬度高,不到3点天就黑了,因为下雪,天气阴沉。奠定基调的是2分26秒至2分40秒的两个镜头(CC一区版),灰暗的雪野、布满鸟窝的大树、冰楞措综的河道,映着不知来自何处的光。而1小时8分50秒1小时9分15秒牧师和恋人在车内的长镜头,摄像机细致地捕捉到了极昼地区黄昏的天际。然后二人来到第二个教堂的外景,灰色调层次极其丰富,可以媲美《乡愁》中最美丽的段落。这些有限的外景中,光感是一种若有若无的荒凉,有着永世将临的调子。
而内景中细腻的光线,尤为让人感念大师的辞世。
在第一个组合段中,教堂的光线来自四面八方窗户,人物有些黯淡的影子。在领受圣体那一节,人物脸部的光,来自上方,显得光洁明丽,喻示着虚假的上帝之光。在10分37秒处,一个老人站在窗前,光从外面照进来,窗台上光影斑驳,而且,窗户上能看见雨滴滑落!注意了,一会就能看见,在高纬度的冬日,一边下雨,一边有阳光的景像了。在13分53秒处,牧师趴到窗台上咳嗽,也出现了光影斑驳的窗台。后来在这个房间中进行的第二组合段和第四组合段(牧师与渔夫谈话)中,光源全来自这个窗户,用得相当整齐。
比较厉害的地方是第四组合段结束时,43分左右开始,牧师站在窗前的带胸小特写,推成大特写,再拉成小特写,光线慢慢变亮。咋看起来不太好理解,接着我们就发现,是太阳出来了,所以光线变亮了。牧师还朝窗外看了一眼。光线的变化相当好地略微嘲弄了牧师的信仰:在感觉上帝抛弃自己,确认了信仰的丢失后,阳光出现了……
44分8秒的时侯,阳光穿过玻璃,照在女主角脸上。44分17秒,光线射入黑暗,隐约可见。光线成为这个组合段的主角,牧师走过扶廊,光线从高大的拱窗中照进来,是信仰之光,也是怀疑之光,很有点“天地不仁”的意味。他说出了他的怀疑,在阳光中,他说他自由了,可是他并没有。
渔夫的死马上让阳光淡去。接下来一个组合段中,溪水轰鸣,淹没了内心的声音。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满天飘飞的雪花,而同时,河面上依然映着淡淡阳光,这一段的影像和音响都相当狂暴。预示着接下来一个组合段(学校争吵)的狂暴和牧师内心在丢失信仰、得到自由后的另一种焦渴。
再下一个组合段(探访渔夫的妻子)中,最重要的场景发生在门厅的楼梯上,牧师怀孕的妻子是在顶部光源的照射下,陷入平静的痛苦。这是继牧师和渔夫之外,第三个在信与疑之间挣扎的形象,所以享有了跟牧师一样的用光。
接下来,1小时8分50秒附近,牧师走过渔夫家阴暗的庭院,有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在门外,一滩水面映着斜阳,像个电影屏幕,怎么也无法穿越黑暗的所在。
最后一个组合段中,1小时11分,我们看见了同题材电影中最常见的烛光。在《乡愁》中,烛光的信仰的标志物。在这里,烛光却含义暧昧,似乎是喻指虚弱的信仰(还是次品)。在这一段中,我们还能欣赏到女主角坐在窗户是唯一光源的长椅上的画面,以及光线打出的她的侧面轮廓,实际上,爱也不能成为信仰,爱是怀疑,信也是怀疑。
礼拜开始后,我们有了最后一组光线效果,代着非常强的嘲讽色彩,灯坐的蜡烛亮了,教堂亮了,庄严的音乐响起了。在信仰被怀疑的时代,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坚守?
在《冬之逛》中,很多场景的切换,都用了“溶”这种并不是很为艺术电影所采用的古典技法,应该也是为了配合光影的变化吧。
5 ) 冬之光
电影截取了一个牧师在早晚两次布道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几件事情。这部电影不像《犹在镜中》那样所有人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主题是通过人物关系的转变而被推动,《冬之光》中的牧师成为了绝对的主角,他总是试图向别人表达一种上帝沉默的思想,包括求助于他的渔夫,他的情人和一个教堂的管理人员。他不仅怀疑自己信仰的力量,而且将这种思想作为自己自私虚伪的借口。下面我要引用电影中一段对白:
“现在我读到耶稣受难那部分了,那部分使我停了下来,所以我想和您讨论一下,艾里克森牧师,我觉得,对于耶稣的受难,他的痛苦,您说过于强调是不是全错了?这个对于肉体痛苦的强调,其实有些专横,或者并没有那么坏。以我的愚见,我受到的肉体痛苦也有耶稣这么多,而他的痛苦非常短,我想那大约持续了四个小时。我觉得他在另一方面受到的苦要深地多。也许是我想错了,但想一下蒙难地,牧师,耶稣的门徒都睡着了,他们不明白最后的晚餐的意义。当执法者出现时,他们都跑了,还有人否定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而耶稣却被人出卖了。耶稣已经认识他的门徒三年了,他们一天到晚住在一起,却不知道耶稣说的做的什么意思,门徒们抛弃了他,全部都这样。他被抛下一个人了,意识到没有人明白他,当他需要人依靠时却被抛弃了。那一定是无比的痛苦,但最糟糕的还没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吊在那里受苦时,他叫到:“神,神啊,你为什么抛弃我?”他有多大声叫多大声。他以为他神圣的父亲抛弃了他,他觉得自己鼓吹的都是谎言,在他临死前他都怀疑。这不是他最大的痛苦么?上帝的沉默!”
假使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然而在任何事件发生过程中(就好像耶稣的受难),他都是沉默的,他不为信仰他的人指明道路,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神迹来补偿,那么信仰就是一种痛苦的事情,因为在信仰的过程中,并不知道信仰是否有效。在电影中的牧师,已经丧失了信仰的能力,他却试图通过祈祷(祈祷应该建立在信仰之上),重新获得信仰的能力,或者可以说,试图通过祈祷可以从上帝那里寻求祈祷的理由。
6 ) 伯格曼电影笔记之《冬日之光》:宝藏
1,第一场戏里埋下了很多线索,不只是情节的引信,更是人物内心和性格的伏笔。
这些线索藏在各个人物的表情和动作里。
渔夫的不屑——他总是垂着眼,拒绝与任何人或者上帝交流。
渔夫妻子的单纯虔诚——目光温顺地直视耶稣和托马斯。
玛塔对宗教的淡漠对托马斯的关切————其中有一组镜头是这样剪接的:(在第一次唱颂歌时)近景,玛塔抬眼看向前方;特写,托马斯手中的圣餐,耶稣的肉体;远景,站在台上的托马斯手持圣餐;近景,玛塔看着前方,又垂下头去。这一段剪接的重点在于第二个镜头,圣餐的特写,在这里它既暗示又隔绝了玛塔和托马斯的关系。英格丽图林是个多好的演员啊,光从眼神里就能清晰看到玛塔的怜悯,在这场戏里表现最好的就是她,好几处她只依靠着眼睛就展现了丰富情感。
2,渔夫夫妇来找托马斯时,伯格曼也有一个使我十二分喜爱的处理,我发现他把空间和时间同时进行了一种奇特的压缩,变得很紧凑,真非常厉害,我需要用截图将它记录下来。
3,我要先按着我的思路捋一下整个故事,这很有必要。
托马斯带领众人做礼拜。回到休息室渔夫乔纳斯夫妇来找他,乔纳斯的妻子希望托马斯能解救自己丈夫,托马斯让乔纳斯送妻子回家后回来。托马斯想读玛塔的信又放弃,从休息室走进教堂。玛塔来看他,一场并不顺利和成功的交流,玛塔离开后他又感到心慌,拿出去世妻子的照片来慰藉自己。然后开始读玛塔的信,这里就是长达八九分钟的玛塔面对摄影机的倾诉。有意思的是一开始托马斯放弃读玛塔的信,而在玛塔来到他身边又离去之后他又愿意来读这封信,是她的主动到来和被迫离开竟使他感到了他对她的需要。渔夫乔纳斯来找托马斯,这时本该是托马斯要挽救渔夫的心灵,却演变成托马斯把他看成救命稻草倾诉对象。就这样,从电影开始到这里,伯格曼用了三个步骤,托马斯灵魂的虚弱一步步被揭示出来。乔纳斯离开,托马斯侧身站在窗前,光亮起,照在他身后,神来一笔。玛塔又回到教堂,托马斯走到教堂的祭台下,弯腰蹲下,玛塔拥抱他亲吻他,他哭泣。乔纳斯自杀的消息传来,托马斯赶到现场,在一条河边,后来当留下他一人守着尸体时,“他清楚地检视自己生命中种种永难忘怀的失败”,伯格曼是这样解释的,但我却觉得电影里那个场景对这句话的表现力不足。托马斯开车送玛塔回家,在教室里两人有了一次惨烈的交流。托马斯和玛塔去了渔夫家,将渔夫死讯告诉了那位妻子。驱车至铁路旁时,面对呼啸而过的火车托马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心里话。两人去到教堂,阿尔戈特跟托马斯讨论了自己对耶稣受难的思考。托马斯开始做礼拜,有了玛塔的陪伴。
4,再来看看托马斯与玛塔的几次相处和交流,也可以说是交锋。
开始是在教堂里做礼拜时,在这里的两人关系表现主要是玛塔对于托马斯的,而且伯格曼还是用相当隐蔽的方式。前面说过了。
接下来是在休息室里,托马斯开始倾诉,玛塔轻轻尝试从上帝那里拉他到自己身边,被拒。托马斯出来找她,她已离开。这一段伯格曼就把那些隐蔽的关系给说出来了,在这里玛塔处于主动托马斯处于被动,托马斯的被动胜利了,但他已经在她面前泄露了软弱。
玛塔在信里对托马斯的陈述,伯格曼让英格丽图林直面摄影机这种如此坦白的方式来处理这段坦白的情节。这段很关键,它将托马斯和玛塔的矛盾冲突纠葛完全展现。玛塔坦白的内容使托马斯感到愤怒羞愧无力,所以接下来当乔纳斯来到时他竟然要向乔纳斯求助。
玛塔回来看托马斯,在祭台下拥抱亲吻,给他温暖依靠。这是一段短暂缓冲。
在教室里的两人交流,我说那是惨烈,在于它的彻底性,在脸上和言语里装满冷酷的托马斯却是在退缩着,“你会恨自己至死”,玛塔一句话使他暴怒也使他明白自己需要她,所以终于他还是要求她跟自己一起离开。
在火车的轰鸣声里,托马斯告诉玛塔自己当牧师完全是父母的意愿,然后他们到了教堂。我一直在设想这个结尾里伯格曼的态度,由于他在电影里表现出的对现世生活的肯定对上帝的反抗曾使我迷惑,迷惑的地方是为何结尾还要安排一场礼拜,领取圣餐,现在我所能做出的解释是,安插进去的阿尔戈特和托马斯的谈话在这里起了作用,宗教是现世的宗教上帝是现世的上帝人生是现世的人生,能使自己相信的只有身处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感受,这是不需假设的。所以伯格曼才说“一切都显得异常清晰起来,他终于面临第一个新生的机会”。
阿尔戈特向托马斯阐述自己的思考时,伯格曼将两人放进同一画面,然后镜头从阿尔戈特摇到托马斯再摇到阿尔戈特再摇回托马斯,让两人共享阿尔戈特表述的那个灵魂充满怀疑的痛苦。而接下去玛塔跪地祈祷“只要我们感觉安全,敢展现彼此的弱点,只要我们有某种信仰,只要我们相信”,说最后一句话时镜头切到了休息室里的托马斯,相似的景别和动作,相同的心声,信仰就在真实的生活里。
5,伯格曼在这个宗教色彩浓重的电影里却是让宗教退居了次位,人的内心情感和现世生活才是诉说的核心。
对于基督教,我是不怎么瞧得上的,它与我奉守的文化差异太大,伯格曼是从那个环境里浸染而出的,但他却在一步步洗脱,从他的电影来说,到了《芬妮与亚历山大》就洗的差不多了,在态度上已经很接近于儒家文化,肯定此世的生命,无论欢愉或悲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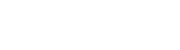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宗教仪式越是庄严肃穆,与会者们的小动作越是放大得明显。而后大部分时间里,几乎只有大段大段的台词文本,缺乏肢体语言和表情,甚至连镜头都不移动。吊诡的是,不动镜头的摄影竟然广受赞美(不可否认光的运用确实是亮点)。在这样一部仅有81分钟却模糊了故事性的电影里,伯格曼就是在利用电影做文学。
神的语言是沉默,我想其实人不是在跟神对话,而是跟自己对话;每个人都跟你对话,或者是神的意旨,或者根本只是自己的臆想;而这些对话都发生在法罗岛。
没有了《犹在镜中》的复杂外景调度,室内景加戏剧化的表演简直就是神学课,主题是深邃了,可供玩味的余韵就不多。几位主演撑起了全片。西班牙内战、丧偶、伤残……这就是神创造出来的不完美的世界啊。中国人应该自豪吧,我们当年造出原子弹的新闻至少吓死了一个瑞典佬。
百子湾2016.2.26.7pm 首尾仪式的截然不同与相互映照。可以窥见冷战的重大影响(“中国人要造原子弹”并不对瑞典小镇造成直接威胁,却毁灭了他们对于人的无限发展进步的想象),上帝的沉默与情感无力的结构性仿佛。
柏格曼最叫人厭斥的要素集大成…….為什麼自私的男人在他的電影(總)是如此受女人寵愛?
相比《犹在镜中》,对上帝的直观讨论减少了些,但还是浓重于《沉默》
4星半,微弱的信仰残烛,宗教性强于《犹在镜中》更为阴冷而封闭,伯格曼将自己前一部影片中的理论“上帝存在于爱中”的反复思索、质疑、甚至推翻。能够切身感受到对于信仰崩塌以及众人背离的悲观绝望,虽然在结尾,“上帝存在”这一理论和信仰仍然维系,但已经摇摇欲坠,亟待解构
《犹在镜中》探讨了“上帝是爱,爱是上帝”,《冬日之光》则嘲讽了这观点。同属“信仰三部曲”,延续了上帝是否存在的探讨,但比前作的癫狂更绝望,心如死灰的牧师再无装载盛情的可能,反向信众倾吐苦水。管家说,耶稣被钉死前使徒离弃,上帝不应,在怀疑中死去最痛苦。谈及中国原子弹威胁,有意思。
对白写得真好。两个很棒的段落:Lundberg女士念信,直面镜头难以逃脱;神父与Lundberg在铁轨前停车,神父说是他父母期望他成为神职人员,此时火车喷着蒸汽,头也不回地往前驶去。
#重看#古典、简洁、沉默、肃穆,德莱叶与布列松隐约可见;冬日之微光惨淡稀薄,恰如信仰之岌岌可危,光线变化折射勾连心理转变;构图与镜头都很工整,与牧师职业&教堂氛围契合;他永远在书写亲情的疏离、神性的质疑,父亲的阴影像冬日的雪彻骨一生。
在信念终于垮塌的黑暗时分,一束[冬日之光]倏忽照亮了牧师的脸。呵!上帝不是爱,爱亦不是上帝,怀疑才是。当结尾的钟声敲响,女主角跪下去祈求哪怕一丁点的信仰,我们很难不为之动容。这就是人类吧,在疑惑中苦苦寻觅着光亮。伯格曼不仅用他高超的语言、更用他的沉默轻松地摧毁了我。那是上帝的沉默。
伯格曼一生不断地相信、质疑、否认、肯定、幸福、痛苦的回环纠缠和激荡,在他和上帝的“摔跤”过程中,他通过影片来表现他幽冥晦暗处的驳杂思想和宗教浩渺感:世人痛苦焦灼、上帝神秘莫测、灵魂低语无奈,许多潜伏在幽冥深处的哲学玄妙通过他的不可言说的混沌和丰富多彩的影像表达出来。
1.冬日之光,虽然明亮却显得苍白无力,虽然仍有热量却无法温暖人心;2.上帝即是爱,若失所爱,心中的上帝是否还在?信仰的动摇,焦虑的世界,上帝在沉默。
信仰像冬日阳光一样惨白无力,牧师也困惑其中。中国无神论者的胜利严重的打击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电影里表现出来的)。信仰三部曲的中间作品,伯格曼这是叫人信基督还是反基督啊--
在充斥着「中国」威胁论调,看似严肃神圣实则滑稽可笑的《冬日之光》里,爱是「上帝」许诺给渴望被爱之人的礼物,可惜,这种轻易就能被中国人感同身受的甜蜜之爱既成了西方男性精神上逃避着的责任,也成了西方女性腹中怀揣着的负担与绝望。这套「叙事」话语明显是擅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把戏的马戏团小丑抑或《魔术师》伯格曼忽悠抑或安慰「老弱病残孕幼」群体的谎言。接近甚至可以「以假乱真」扮演上帝的神父自己是一个不信上帝的「爱无能」患者。在主动释放「结婚」信号的情人抑或爱人面前,他高大上的伟岸形象被灵肉分离导致的精神分裂折磨得不成样子。宛如一根不幸的阳具,无法满足这个让女主感到安全的乞求。然而,他婴儿般的示弱(示爱)却能召唤母亲般的怜爱。他顺势将责任推卸给父母,并把自己背叛上帝或者婚姻不忠归咎于他们的呼唤和期待。
上帝都是沉默的,他不为信仰他的人指明道路,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神迹来补偿,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信仰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渔民的自杀代表着希望的苍白,信仰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伯格曼摧毁了上帝代表安全感、上帝即爱的概念,这样的上帝形象不过是人的心理投射,应该予以革命,予以背叛。
太残忍。教堂里的各怀心事,对上帝的各取所需。牧师是否其实是在聆听世俗的同时为自我的困惑寻找出口?然而当对自我都无法坦诚相见,自我的祷告和施予世俗的祷告是否成为了逃避懦弱的山洞,教堂也已经不再是寻找答案的避难所?这样看来牧师眼中的凡夫俗子或许对于爱的理解其实更加真挚深刻。
"神之默示"三部曲中篇。1.风格极简而质朴,布光精妙,以静止镜头和小景别为主,摄影机对人脸的凝注一如既往。2.冷漠、疏离、傲慢、信仰动摇的牧师解答不了苦难与生死问题(由中国即将研制成功核弹引发的焦虑),亦无法接受玛塔对自己的爱。3.片尾教堂司事自承对耶稣受难时高喊的“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见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后两福音书则无此细节)的思考发人深省,身心的苦难与信-疑的纠结溢于言表。4.八分钟的玛塔对镜读信段落情真意切,中途插入的手中溃烂皮疹镜头则同质于耶稣圣痕。5.牧师发出天问后的一刹那,窗外耀眼的光线兀自笼罩了他,一如马力克[通往仙境]结尾的那道神秘圣光。6.牧师说,每当直面上帝,祂就会变成某种丑陋恶心的东西,如蜘蛛——恍若[犹在镜中]变奏。7.首礼拜详尽展示,末尾则仅有非信徒玛塔一人。(9.0/10)
【中国电影资料馆展映】大部分场景在室内,摄影和构图非常讲究。观影时状态不佳,有待重看。三星半
那個愛著牧師的女人,給我一種除了牧師其他人都看不見她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