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电影《豆满江》描述了从朝鲜偷渡图们江来到中国边境小村庄(吉林省图们市江沿乡新田村)的少年脱北者的故事。豆满江,在中国被称为图们江,位于中朝边界。影片主人公是12岁的少年昌浩,他有个哑巴姐姐顺熙、年迈的爷爷以及远在韩国挣钱的母亲,父亲则在当年为救落水的姐姐而在豆满江里丧生。昌浩与一位过河而来的热爱足球的朝鲜少年郑真成了朋友。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大象女王黄金时代1946神殿2019朕的刺客女友远古入侵第五季对影闪点行动第五季一人露营伊甸之东我很喜欢你,那你呢?同族内阁作战室 反叛 第三季双腿生风皮囊之下2021好汉两个半 第三季第三只眼坏家伙2024代码211死刑犯女人的船以爱之名:同志矫正治疗爱的故事酒吧篇越狱大逃亡第一季黄蜂蜇消防厅旁警察厅 第二季新上海滩(国语版)
长篇影评
1 ) 图们江
今晚看了张律导演的《图们江》。讲的是东北边界的事情。长镜头缓慢,全部采用自然光。台词很少。没有一张笑脸出现。没有背景音乐。中间穿插了几首童谣。
脱北者与边民之间,由于亲缘关系,暗通款曲;可物质的匮乏,又破坏了这种微妙的关系。酷寒、饥饿和政治宣传,才是电影的主角。所有的人物,都是配角。
电影还间接涉及到了韩国,不过,那多半只是导演给予观众的一份缥缈的希冀。
2 ) 若即若离的远方
看这部片子时不禁想到的锡兰的《远方》。张律导演的镜头虽没有锡兰拍摄土耳其的冬天所带来的惊艳,但干净明澈,看着非常舒服。夜间的暗和雪景的白的突然切换,转过晃动的镜头出现的两个孩子,都带来了惊喜。
小镇地处中朝边境,冬天在图们江冻上以后,就有饥寒交迫的朝鲜人偷渡过来。当地人们同情他们,给他们吃喝,帮助他们偷渡,不然,他们就会饿死。但其实,当地人的生活也并不好过,人们去韩国打工赚钱,很辛苦,药也要从当地寄到韩国,因为那里的药太贵。当地人是善良的,朝鲜人其实也是善良的,但就像片中的小孩所说的:“因为饥饿,连父母都会不认。”好心救助的朝鲜人一边磕头,一边对顺熙下毒手,看到电视里,朝鲜媒体宣扬人民生活幸福抱头痛哭,画面中,金主席微笑着挥手,人们热烈鼓掌,而他们濒临饿死,多么讽刺。做豆腐的女人和村长私 通,却又照顾父亲被抓走的孩子。昌浩和朝鲜来的郑真成了好朋友,因为朝鲜人扰乱当地生活又打他,又和好,然而因为好友的告发,偷渡的郑真要被抓走。昌浩想救好友,从房顶上跳下。
事实上,我们很难说谁错了。为了活下去,朝鲜人偷渡。为了当地治安,公安抓脱北者。因为父亲帮助脱北者被抓,孩子作为报复告发朝鲜人郑真。一切的起因,都是饥饿。个人认为导演有指责朝鲜政府之意,若是他们能使人们吃饱,那人们也不用冒着冻死的风险渡江。总想回到北边的老年痴呆的奶奶,幻想着有一座桥,从上面返回。而现实中,无数人度过图们江,到中国求生路。
作为朝鲜族导演,张律关注着被大众忽视的家乡。一方面,当地有工业化,一方面,人们又守着传统。唱歌,晒明太鱼,这是这个地方独有的风景。
顺熙真是干净啊,像是《雪国》中的叶子,忧伤,善良,不染一丝尘埃。那穿着红色衬衫,粉色毛衣的身影,是如同天使般的模样。
3 ) 论·谈之“那边的风景”--马然
201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春梦》(A Quiet Dream,2016)中,三名成天混迹于首尔市区“水色洞”老街区的“失败者”庭凡、益准和钟彬(年轻一代的韩国男性导演朴庭凡、梁益准和尹钟彬各自用本名演出)无一例外地拜倒在女主角艺璃(韩艺璃扮演)裙下──这个三人组经常聚在艺璃经营的一间名为“故乡酒幕”的小酒吧里消耗酒精与时光,并偶尔在和艺璃的嬉笑怒骂中反省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
作为中国朝鲜族导演张律的第九部剧情片,虽题名为《春梦》,作品只是散漫地点缀着浪漫的前情与后续(如庭凡与前女友的重聚),却并没有执著于对主角们的爱情生活一探究竟。黑白画面所带出的淡淡感伤与怀念,总是未及积累、爆发为某种有指向的情绪,就已被三人的插科打诨冲淡、覆盖。同时,片中大量的镜像(如镜子的出现)与主客观镜头的自由切换不断拉扯、分离并重新组合着影片看似即兴生成的日常段落,由此生出另外的时空,暧昧地与水色洞驳杂的都市空间互相对应,混淆着观众对作品的现实主义体验,让人人都仿若做了一场久久无法被遗忘的大梦一般欲罢不能。
如果可以尝试为张律的创作分期,也许我们可以将他2012年移居韩国首尔作为分野,从两个阶段来审视他在延边、北京(他的家人生活的地方)与首尔之间跨地移动的创作轨迹。张律生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并在此成长,他的祖父辈与母亲都是在上世纪初(分别是在1919年与20世纪30年代)从朝鲜半岛(庆尚北道,如今属韩国的东南部地区)迁徙到如今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族移民。张律曾经在延边大学教授中文,在80年代后期来到北京。2000年,他自筹资金,在对电影拍摄、执导的认识完全为零的基础上,靠一班电影学院的学生支持,在北京郊区取景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片《11岁》(Eleven),并随即凭借这部对白几乎为零的胶片作品进入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短片开篇,是寒冷季节中一对貌似父子的陌生人来到某处毫无生气的工业区。看来内向沉默的“儿子”找到一群伙伴踢足球,却被大家孤立,末了只能独自一人踢着看不见的足球玩耍。在极简的现代主义配乐渲染下,片末是“父亲”坐在室外的藤椅上打盹的镜头,让人不由得质疑这究竟是父子的故事,还是已经孤独长大的“他”,在做有关自己童年的诡异的梦。
从2003年张律的首部长片《唐诗》(Tang Poetry)开始,导演就与韩国制作方合作。到了他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芒种》(Grain in Ear,2005),张律开始将镜头对准(延边)朝鲜族的平凡人物与日常生活。除了《重庆》(Chongqing,2008),此后完成的影片对白大多以朝鲜语为主,而他的拍摄轨迹也从延边延伸到了蒙古和韩国境内[如2008年的《里里》(Lri)]。《春梦》和《庆州》(Gyeongju,2014)以及张律从短片发展而来的《胶片时代的爱情》(Love and …,2015)一样,都可以被看作是他于2012年移居首尔之后在韩国当代社会文化的语境内,从文艺小品的样式入手所展开的新探索。不过较之《庆州》,在《春梦》中,张律似乎更有意识地通过几名徘徊在首尔边缘街区的边缘人的故事,来继续思考他自身(作为有在中国、韩国社会生活经验的朝鲜族人)与电影创作在多重国家、民族、身份政治的话语之间的定位,和他从这些话语的交汇边缘开辟美学与政治空间的可能性。
《春梦》中,庭凡是一名脱北者,因为长期被工厂老板拖欠工资,每天例行公事地为讨要薪酬而在老板的轿车前鞠躬。而艺璃作为韩国父亲与中国朝鲜族人母亲的私生子,在中学时代就来首尔与父亲重聚……好景不长,艺璃的父亲很快就患上重病,每天只能如植物人一般瘫坐于轮椅上,需要她的独力看护。在艺璃用汉语吟诵李白《静夜思》的同时,她手边的一册小说正是韩国作家安寿吉的《北间岛》(1959―1967)。这本尚未有华语译本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朝鲜族移民在日本殖民时期的“满洲”统治下在“间岛”(彼时图们江以北朝鲜族聚居地的名称)的生活。
如果说《春梦》所着眼的是离散的主体“越境”之后的人生的话,张律在2012年以前的三部作品,即剧情片《沙漠之梦》(Desert Dream,2008)、《豆满江》(Dooman River,又译《图们江》,2010),以及他在移居首尔之后完成的首部纪录长片《风景》(Scenery,2013),更是集中地在流动性(mobilities)与地域性(localities)的框架下,从“边界/边境”出发,去重新思考有关“故乡”“身份”和“归属感”的问题,为我们研究中国独立电影(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或是朝鲜语离散电影(Korean diaspora cinema)的身份、流动性与地域性,以及规模关系(scale relations)等提供了新的角度。虽然张律从未特意命名,这里我想暂时将这三部作品称为“越境三部作”。
《沙漠之梦》于蒙古实景拍摄,它还有一个蒙古语片名叫做“Hyazgar”,据说这个单词特指沙漠与植被的边界。片中的男主角杭盖与妻女一同住在远离城市的蒙古包中,他自己成天忙于在沙漠边缘种植树苗。当杭盖得知妻子要带有听力障碍的女儿去城里看病时,决意独自一人留在蒙古包中,继续对抗沙漠化的西西弗斯般的努力。此时一对穿越戈壁沙漠经蒙古逃离朝鲜的脱北者母子崔顺姬与昌浩到访,并请求他收留。影片虽以脱北者为主人公,也偶有出现边界巡逻的坦克的画面,片中对顺姬母子的逃离过程只是一带而过,并无意渲染脱北者的惨况,或从宏观的地缘政治角度讨论边界局势。不过,看陌生人的到来是如何打破某种封闭的平衡关系,似乎是张律自处女作短片《11岁》就开始迷恋的叙事主题。在无名的蒙古一隅,杭盖与两位客人虽然语言不通,却总能够通过手势、歌曲、绘画甚至是沉默相互交流,并临时地结成一种类似于家庭的同盟。当杭盖去乌兰巴托的现代住宅区寻找妻女时,他让朝鲜母子看护自己的蒙古包,自己却骑着白马迷失在乌兰巴托的都市风景中,不知身归何处。在这部作品中,张律将自己对政治难民(脱北者)流离失所境遇的关注,与亚洲语境下现代主体在都市化进程中所造成的身份错位、归属感的丧失并置,令“脱北者”不再仅被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抽象议题来讨论,而能够在与其他的亚洲地点(place)的跨国、跨境关联中,重新被赋予政治与美学的可能。
同时,这部以“蒙古族”入题的作品,也让人联想到在2007年与张律的影片一同进入柏林影展竞赛单元的金熊奖作品《图雅的婚事》(Tuya’s Marriage,2006)。尽管在《图雅》中,包括余男在内的所有演员说的都是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蒙古语(歌曲)也只是作为模糊的文化背景出现,我们也许不应该仅仅从二元的身份政治(汉族或少数民族)出发来阐释作者性和他们在作品中的身份表达,因为《图雅》也通过一名倔强的女性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寻找可靠的男子和自己一同照顾已经瘫痪的丈夫的故事,以某种跨地性(尽管只是在中国境内)的视角来观察所谓中国中心以外的人群、他们的共同体与生活方式在都市化和现代化面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某种程度上,这种对“迷失”的思考与《沙漠之梦》殊途同归。
张律认为《豆满江》是他一生最想完成的作品。影片在延边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村庄拍摄,除了略有表演经验的几位本地舞台演员,全片几乎都是毫无任何影视演出经验的村民们的本色出演。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昌浩的母亲在韩国打工,他在这座东北的小村庄和爷爷还有因年少时的事故而失音的姐姐一起生活。冬天的时候,他认识了为获得食物而从图们江对岸涉险而来的朝鲜少年郑真,并成为好友。当这个小村庄发现河对岸的不速之客已经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时,昌浩的姐姐意外被他们一家热心救助的朝鲜难民侮辱,于是昌浩决心展开报复……接近片末,因为其他小伙伴告密,郑真被警察带走,目睹一切的昌浩央求放人无果,他最终爬上废屋的顶层纵身一跃。他的自杀或许是村民对逐渐变得疯狂的“邻居”所作出的无怨无悔的宣告,但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爆发,是当昌浩发现自己终究无法和冒险跨越国界赴约的郑真结成任何基于情感或者是身份的同盟时,用自己的身体所宣泄的绝望、不满与愤怒。
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张律对边界的探索并不止于昌浩决绝的一跳,还有片中始终无法实现的返乡之旅。片中有一位貌似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白发老妇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年轻人回忆自己年幼的时候,是如何牵着大人的手,越过图们江上的大桥,来到如今的延边境内。她的讲述让人想起侯孝贤《童年往事》中在台湾乡下总是带着包裹想要沿着铁路返回广东的奶奶,同时也是张律对自己家族史的感伤投射。片末字幕的段落是一个画面开阔的远景长镜头:冰雪覆盖的图们江上有一座幻象一般的大桥,上面有一个移动极其缓慢的小黑点,似乎是那位总是在寻找回家的路的老妇人。对张律而言,讲述图们江两岸、三地(包括昌浩的妈妈和其他村民们,都在韩国打工)的越境者以及界河、边界村落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歌颂离散人群的同根同源,相反正是为了质询任何本质化意义上的、同一化的“祖国”,或“民族归属”。
有心人会注意到,在驳杂的中国独立电影创作中,近年有不少少数民族题材的佳作在世界影展受到瞩目──例如李睿珺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River Road,2014)是裕固族少年的骆驼之旅,或是王学博与宁夏回族社群有关的作品《清水里的刀子》(Knife in the Clear Water,2016)。如果去思考张律的作品是如何与(由大量非少数民族导演构成的)中国独立电影的话语和实践对话的话,我们的落脚点似乎应当在于观察《豆满江》是如何以“边界”(包括如《豆满江》中的界河、边界村落等)去构建某种“从地点出发的想象”(place-based imagination),用朝鲜族的社群、他们的语言与故事去延伸和改写中国独立电影的地域想象,并去批判性地审视独立创作中本已存在的汉族中心话语。
《豆满江》完成之后本已无意执导新作的张律,2013年应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三人三色”(Jeonju Digital Project)的数码短片单元之邀,拍摄了一部以在首尔周边生活、工作的外籍劳工为主体的纪录片,名为《在那边》(Over There),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纪录长片《风景》。作为张律的第一次纪录片尝试,这部作品也标志着他将跨地域的视角从中国延边、朝鲜以及韩国三个朝鲜语族群互相交会的边界,转移到了生活在韩国社会边缘的流动人群。按照导演的说法,所谓“风景”,也就是街道上陌生人的聚合。《风景》一方面以大量静止机位的长镜头搜集并并置了首尔及其周边的都会空间中驳杂而毫无特色的“非地方”(non-place):外籍劳工们的工作空间(如车间、办公室、温室、屠宰场等),私人空间(宿舍与家),集会与社交的空间(如教堂聚会、礼拜堂、市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等),还有机场和车站这样中转交通与移动的节点。另外一方面,作品采取貌似常规的采访对谈方式,以工人们工作或休息的空间为背景,邀请他们面对摄像镜头侃侃而谈。然而,对话的主题却是关于每个人在异乡最难忘的一场梦境。如果说“说话的脑袋”(talking heads)这种纪录风格以景框刻意强调了被访者受限的空间性,让人联想到韩国社会对外来劳工和移民的限制,以及普通民众对外籍劳工的刻板印象的话,“说梦”作为机制则调动了受访者去进行叙述与表演,混淆了现实与虚构、个人与集体的分野,也让受访者和观众有可能去想象异类的时间性、地点与经验。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风景》中,很多工人的梦境都与故乡以及自己的家族、朋友和爱人有关,有时这些梦境也和他们在异乡的抱负相互对应、重叠。这种纪录片方法清楚地表明,在个人身份构建中,“地点”是随着主体流动的,它是不断被重构的身体性的经验;而“边界”也是如此伴随离散主体疼痛生长的事物──这对片中的受访者而言如此,大概对张律亦然。尽管这部纪录片并没有从行动主义的角度抗议全球资本制度下的跨国劳工状态,也没有刻意渲染移民和外籍劳动者在异乡漂泊奋斗的苦境让多愁善感的(但很可能是屈尊俯就的)观众掬一把同情泪,《风景》以“说梦”为方法去聚焦受访者的日常经验与感受,却赋予了同一化、僵硬、疏离的都市风景某种柔软但并不廉价的内核,并如此突破甚至颠覆了纪录片题材与政治性关联的窠臼。或许也正因为对这种“说梦”的实践心有灵犀,作为观众的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庆州》《胶片时代的爱情》与《春梦》中的层层梦境,就算迷失,但总可以再返回。
文转自:论·谈之“那边的风景”--马然 侵删
文转自:论·谈之“那边的风景”--马然 侵删
文转自:论·谈之“那边的风景”--马然 侵删
4 ) 为什么你们看到的只是恶?
YouTube上有一位韩国记者采访导演到片段。(‘영화'두만강'장률 감독’),导演说他拍摄到那个村庄里实际上没有任何人举报过脱北者,没有任何人主动举报过。(发生事故而被警察调查的情况另说。)显然,导演想表达完全不是所谓‘人性之恶’或‘农夫与蛇’这样的寓言故事(不过导演的意图不是特别重要),然而我们多数观众看到的却只是这个(?)
我们任何人,当处在一个极其恶劣环境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够做出我们平时无法想象事情,尽管这并不是作恶的借口。我相信人确实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唤醒内心恶的一面,那个该死的强奸犯当然要千刀万剐;但是人也能在恶劣的情况下维持其善的,好的一面。那个会踢球的朝鲜小孩子,他用他的守信表达他了的感激和友谊,即使在无法带邮票的情况下也用其他东西弥补了他的诺言,并且在后来冒着危险来完成他的许诺,帮助昌豪他们踢球。

YouToube上有一些朝鲜族同胞们对于北朝鲜人申请韩国政治避难在政府的有待过下日子非常不满,(实际上大多数脱北者在韩国情况非常糟糕,基于文化,语言,歧视等众多因素。)就像在西方国家一些人厌恶难民们来到他们国家白吃白喝一样,似乎他们总是在享受着某种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表达着对这一个群体的嫉妒和嫌弃;然而这种心态实际上是病态的。就像纳粹德国人看到犹太人占有着好多钱,又勾搭他们纯情的德国姑娘们,越看他们越邪恶一样,我们这种看待脱北者的视角(gaze)本身是带有一种恶的。韩国电影《春,夏,秋,冬,春》中脱俗的和尚谋杀了对他不忠的女友。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面对伴侣的不忠我们不至于走这样的极端,然而对那个和尚而言这种行为无法忍受,极其邪恶,而窥视这种‘恶’的凝视的目光本身就是恶。而我们看到电影中脱北者的‘恶’的观众们或许应该反思,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也居住着这样的‘恶’,所以才能看到他们‘恶(?)
我们从电影中本应该看到的还有;那个冒着风险帮助北朝鲜人脱北的商店老板的善良,那沉默寡言的爷爷(非常典型的朝鲜族爷爷的形象),还有善良的哑巴姐姐,以及最后在面对同伴的抓捕,为了尊严,为了人格从屋顶上一跃而下的昌浩。
另外,故事中的所有人都是从江的对面过来的。
5 ) 豆满江:朝鲜族少年的魔幻漂流
豆满江、图们江、土门江,不同的名字指向的是同一条河流。这条发源自长白山脚下,全长500多公里的河流从15世纪开始就成为了中国和朝鲜的天然边界线。
2010年,中国朝鲜族导演张律携自己的第10部影片参加了同年的柏林电影节,并荣获水晶熊奖。这部讲述中朝两国少年在边界线上成为朋友的电影,名字就叫作《豆满江》。和张律的其他作品一样,本片仅在国际影展及韩国上映,无缘大陆院线。

「脱北者」一直是韩国电影所热衷的元素。作为朝鲜一衣带水的邻邦,逃向中国的脱北者数量巨大,而国内官方却三缄其口,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报道。
中国人——或者说是朝鲜族们,会如何看待这批渡江而来、说着共同语言的同胞?我们也许可以从这部电影里找到答案。

电影以一个长达两分多钟的长镜头作为开场,结冰的江面与远处的群山巍然不动,只有狂风在耳边呼啸。在冷色调的加持下,这里犹如一片没有生命的土地,只有无以言语的冷清和压抑——直到影片结束,这种情绪都将盘旋在你的脑中,久久不能释怀。


冬天的豆满江上经常会出现脱北者的尸体,当地人对于这种事情早已见怪不怪。江边的村子里,朝鲜族少年昌浩和哑巴姐姐以及爷爷相依为命,他们的妈妈和其他人一样跑去了韩国打工,爸爸则丧命于多年前的豆满江洪灾。
整个村子里除了老人孩子就是整天醉醺醺的酒鬼,没有一点生机。即便如此,这里还是不乏好人的存在。比如开货车的叔叔就经常帮脱北者捎上一段路,躲避岗哨盘查。
大家心知肚明,一旦遇到查岗的军人,被带走的脱北者往往凶多吉少。


故事开始于一个漆黑的夜晚,昌浩和他的小伙伴们发现了几个躲在空房子里烤火取暖的北韩少年。孩子们决定偷送些食物给他们,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让北韩少年们陪自己踢足球。
孩子的世界简单纯净,大人嘴里的政治立场和国家利益并没有渗透进他们的思想。能玩到一起,自然就成了朋友。



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被一场意外打破,一个男性脱北者在深夜敲开了昌浩家的大门,好心的爷爷同意让他留宿一晚。

爷爷带着昌浩出门了,姐姐则给脱北者准备了一桌饭菜。酒足饭饱的男人偶然看到了电视上的朝鲜新闻,先是痛哭流涕,随即把目光投向了面前的少女,在呆滞了几秒之后,朝她扑了过去......
镜头缓慢推向电视机,屏幕里的将军意气风发,就连姐姐挣扎反抗的声音,也逐渐淹没在了主持人昂扬的讲话和群众响亮的掌声里。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场景。原本处于弱势的脱北者因为看到了北韩节目上的最高领袖,内心的矛盾不安被彻底激化,将面前的恩人当作了发泄的对象。屏幕内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讽刺。
程耳在他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里也设计了一个相似的场景:浅野忠信扮演的日本间谍在荒郊野外遇到了满载日军士兵的卡车,随即停车枪杀了司机并强暴了同行的女伴。
浅野忠信与章子怡在片中有大篇幅的情欲戏,其中野忠信送章子怡离开上海那段,半路上与章子怡发生的情欲戏,是浅野忠信计划好的吗? 程耳:我作为观众之一,我不认为浅野是处心积虑的,他是临时起意。第一,装满士兵开往前线的军车刺激到了他;第二,子怡戴的耳环正好是朵樱花,所以正好是这两点刺激到他作为一个长期的卧底,他的内心产生了波动。


《豆满江》里的这段强暴戏,不仅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更是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阴暗:受害者与施暴者可以是一体,羔羊也能变成恶狼。
脱北者是否值得我们去帮助?这是电影带给观众的现实问题。



村子里的粮食不断被人偷走,每天的广播都在呼吁大家举报脱北者领取奖金。广播之后没过多久,开货车的叔叔就被带走了。警车渐行渐远,只留下年幼女儿的哭喊声回荡在雪地里。
大家对脱北者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就连孩子们也开始用棍棒砖头驱赶那些小朝鲜人。大人们犯下的过错,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报应。



在那群小脱北者中,一个名叫郑真的孩子和昌浩走得最近。他们不仅一起踢过足球,还多次交换过邮票。夜晚,脸上带着伤的郑真带着礼物来到了昌浩家里,和他约定会来参加明天的足球比赛。

翌日,接到孩子举报的警察在球场上逮住了郑真。目睹这一幕的昌浩爬上屋顶,朝警察大吼放人。


随后,几乎没有犹豫地从房顶上一跃而下。

没有人知道他从屋檐跳下的一瞬间,心里在想什么。是愤怒、伤心,还是急于自证清白的压力?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在旁人眼里,昌浩的自杀注定是没有意义的,何况是为了一个脱北者朋友的人情信义。
电影到这里似乎就夏然而止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片长里,镜头始终保持着冷静克制,以旁观者的视角审视着这片雪地里发生的一切。没有过多的台词和背景音乐,只保留最基本的自然环境音,反而给人一种别样的真实感。
在所有角色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一位只出现过三次的老奶奶。她从小跟着妈妈从对岸走来,如今却想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结尾处,奶奶手拄拐杖走上了那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大桥,在镜头的注视下缓缓走向故乡。导演在这里用了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完成了朝鲜族人精神上的回归,以虚幻的桥梁连接起了两岸人民对于身份的认同。
这么一想,这个场景倒是显得有些残酷了。


多年前昌浩的父亲被豆满江的洪水卷走,多年后他也为了对岸的朋友而死。这条沉默的河流在无意间左右着无数家庭的命运,不论愿意与否,他们都被卷入了这场魔幻的漂流之中。
豆满江会迎来冰雪消融的那一天吗?
他们在等,我们也在等。
如果你的口味和我很像
欢迎关注一个看心情更新的的公众号

6 ) 图们江 豆满江
朝鲜语的豆满江就是图们江,它发源于中朝边境长白山山脉,江水由南向北流经中国境内的四个县市,其中珲春与朝鲜隔江相望。故事就发生在江边的村落里,讲述作为同宗同源的北逃者与中国境内朝鲜族之间的故事。
此片为小成本的作者电影。一开篇,空镜与人物渐进的长镜头就明确的表达了作者意图,孤独阴郁感凸显了影片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与情节的展开形成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的对立。对立保持于全片,呈现了统一连续性的整体。看作者性如此强的电影,本身就容易产生偏见,因为作者论(auteurism)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抛弃结构主义,打破规则重建系统,观看者个人的喜好容易凌驾在松动的标准之上,左右着电影的评价。所以我就单纯且主观的说说喜欢它的原因吧。
我喜欢影片的那种撕裂感。什么是撕裂感?这是一种有可能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的状态。表示物质之间并没有分离,却已经变了形态,就好像塑料的折痕,抹不掉也回不去。如果作用于人,那么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疼痛。影片通篇给予我的正是这种疼痛,无论是大到民族意识与国家层面,还是小到个体的人性与道德的描写,都做到了让人在精神上产生类似生理疼痛的臆想。片中重复出现的仓库,时常与景框形成封闭空间,由此只能由空窗望向风景,限定了观众的视域。这可以被解读为片中人物的内心,所谓残垣断壁不禁风雨。这也是导演深层思想的自述,观众无法将这撕裂感进行缝合,便实实在在感受着又与之共情。
其实回想,说到底《豆满江》主要想呈现的是阴暗与无奈,但它也没有忽略人性的闪光。影片给观众出了一道大题,随着解题不断产生出有关于人的反思。像结尾处昌浩的屋顶坠落,面对众人的冷淡,让人看到的是孩子的仗义、刚烈。但同时带来的情绪又是那么的绝望,少年竟然以如此直观的方式进行反抗。克制的收尾拍摄手法没有让结局戛然而止,反而来的更加讽刺、残酷。对影片深入辨析,不难发现作者鲜明的态度,面对时间与空间,面对欲望与恐惧,很难将人性分出界限,所谓的审判,可能无力也无用。人的复杂性被准确的诠释出来,赋予了电影自身多层次的表意。
影片的摄影与情节相互平衡形成基点,使叙事性的写实能够贯穿其中。节奏异于常规,缓慢中稍带变奏。人物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表演,很难演,也确实演的不行,像是说话没有音调又拉长了音,明明结束了还显出未尽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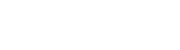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柏林2010 Generation 14plus-水晶熊Special Mention。张律“跨境民族”题材中对“脱北者”表达最直接的一部,两国边界上边民的关系很是复杂,整个悲剧故事也写出两国边民关系-中朝关系的转变(友邦→恶邻),也特别好地写出了少年的逻辑。摄影非常棒,结尾真挺神的(画→《童年往事》式的老太太“回家”,姐姐突然说话)。
3.5 很多处透过窗框,并辅以工整的构图拍人,仿佛是在营造一种第三者视点。开头的空镜也是如此。接着是对居民的刻画,用麻木来形容似乎不当,那便作不外露吧。从中并未觉得在文化身份认同的探讨上有切中要点,更多地是关注那种自发自生的天然的欲望(感情)。收尾漂亮。
从这部开始喜欢张律。列入最爱的华语导演之一。
影像上非常漂亮,统一的色调是气候帮了大忙。往延边之路的河流与道路曲线的透视感,跟聚居地垂直墙面正向拍摄所形成的方正线条/景框的滞感,构成迥异的反差。两场性描写都很厉害,北韩人性侵姐姐一场是借着电视播出北韩新闻的“政治春药”;村长与豆腐娘通奸一场,要设置在做豆腐的案板上,性与生计被捆绑在一起。更多的政治隐喻与身份焦虑都跃然纸上,而两者都成立,得益于故事本身被密集聚合在一块的村庄模型。
极度冰冷,不动声色,滴水不漏。鱼干、跳绳和图们江简直是绝妙的隐喻:我们和他们尝试着跨过界线却又停留在原地。整体影调清冷而红色的局部色相穿插得恰到好处。摄影构图的空间对话和张力简直令人窒息。生存残酷的呈现而非政治观点的生硬表达。一切都已在豆满江的洪水中毁灭殆尽。第一部张律太喜欢了。
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张律都是目前最牛逼的华/韩语导演
大概是张律作品中情绪最溢出的一部,几处声画分离场景尤其强烈(如金正日阅兵-强奸、ending处哑巴姐姐在画外的呼喊);但也恰恰因此反而会显得过于工整,较之《春梦》反倒落了下乘。镜头还是以固定视角和简单的运动镜头为主,却也有明显能看出影像自觉的地方:对白与人物身份相当契合,趋于极简,人物的内在情绪主要通过其outer behavior来呈现。
一江有双名,朝鲜叫豆满,中国称图们。一江连两国,一江,既是一衣带水,又是天各一方;两国,既似情同手足,又像水火不容。作为为数不多的朝鲜族导演张律,虽身在韩国,然心系东亚,一直致力于依托影像实现民族共情,通过影像洞悉朝鲜族人情感,在《豆满江》中,脱北者在逼仄的空间苦苦寻求一丝归属感,一座桥它曾经存在过,现在也还在,但已经不同了。画面如真似幻,故事痛美并存,《豆满江》无疑是脱北者最真实的写照,亦是张律巅峰之作。
4.5;一江相隔的两个国度,在血缘和地缘上都有一种奇妙、微妙的勾连,片中以不少窗框分割的视野表现两岸的对峙及融合,且呈现宏观政局和个人微观情感层面的动荡;脱北者与归乡者的对照,无论身处何地,都是难以安放的身心,难以确认的家国归属。故事略有戏剧化,令人心碎。结尾印证“我梦见姐姐能说话了”,张律一以贯之的超现实意味之笔法。
一条江,隔断了联系,却封不住回忆。每个人都住在心灵的围城,在逼仄的现实中苦苦寻找归属感。白雪藏不住原始的欲望。小男孩的纵身一跳,留住了人性最单纯的美好。结尾奶奶走上虚幻的桥,踏上心灵的归乡之旅,写实主义中的一抹超现实色彩。
电影表象平静无波,人生的无奈与从容,人性的善与恶,政治的光明与黑暗却涌动其中。纵身一跃的反抗,超现实的友谊桥,张律电影的结尾堪比安东尼奥尼般深刻有力,且具有独特的东方韵味。第一次看反映中朝边境的电影,《图门江》至少为华人电影的多元性做出了贡献。
北朝鲜难民与一江之隔的吉林某村落,及对后者日常生活的影响(或者说超越日常的影响)。边界、饥饿、尊严、兽性、背叛、绝望,透过少年昌镐的眼睛展开。张律作品里最有力的一部。几乎他所有电影里都有一个被强暴的女性来见证人类劣行和悲剧;要走回对岸的奶奶令人想起《童年往事》里的祖母,虚幻的桥。
6/10。开篇两分多种的固定机位对准冰封江面上装扮尸体的昌浩,村长和老板娘走进时他一溜烟跑了,这其中流淌的悲伤情绪源自无法缝合想象与现实的桥梁纽带:村长老妈几番尝试过从桥梁渡江,江上意味着想象中的归乡。而现实中姐姐被脱北者强暴的昌浩守在江边用木棒击打准备上岸的脱北者,甚至对郑真送礼物的态度也发生粗暴转变。理想的祖国出现裂痕,是新闻里播出赞美金将军的讲话对应脱北者突发的性暴力,村民们食物被频繁来往的脱北者偷也动摇了孩子的同情心,愿意伸出援手的同时也带着防备手段和领政府奖励的告发心态,居住国与祖国的微妙情感关系,投注在藏身废墟里的踢球游戏和昌浩跃下房顶的死亡选择。只拍摄无关事物的留白不能饱满人物的情感,显得空洞无意义,姐姐身体成为男性的泄欲工具和怀孕的圣母情结,以及昌浩结尾的殉道体现了观念的公式化。
人生就同一树花,随风而落,有的飘在茵席上,有的落在粪坑里;一江图们水,两岸乡愁情,白雪盖大地,痛苦亦平静
影片开始的一个长镜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镜头,它涵盖了该片的节奏、基调、角色动机和故事延展,这一镜处理的和许多伟大流逼的导演一样,见功底。然而,它并不炫耀,而是内敛的理智,值得反复体味。
一种围城,北韩人想进来,本地人想出去,更多的人留在这里…老一辈对脱北者的坚定接受和友善,中年一辈的缺席和出走,年轻一辈的游离和困惑。开头昌浩装成尸体隐喻了结局,脱北者们吃饭的样子,对死亡的习以为常,受害者瞬间成为施暴者…只能送出破碎的火箭作为礼物,也只能接受无法起飞/逃离的命运;弟弟的纵身一跃和姐姐的突然说话,一边是跳楼,一边是堕胎,双重的毁灭/死亡…有没有那样一座桥…倒回去补看张律的早期作品,粗粝冰冷,让人噎住的沉重...导演说他拍摄的村庄实际没有任何人举报过脱北者
被强奸的哑女,从屋顶跳下的昌浩,自始至终平静的爷爷…复杂地缘、渺小个体、言近旨远。会讲故事的导演从不忌惮于冒犯观众,但又不同于某些乐此不疲地沉浸在自己艺术小天地且为之洋洋得意的导演。如果说另外几部还一直被和洪尚秀放一起说事儿的话,那么拍出这部《豆满江》的张律,恐怕李沧东也比不了。
张律是我特别偏爱的一个导演,他的作品有文人气质,是以文学入了电影的,这在后来的《庆州》《春梦》中尤甚。《豆满江》表现的主题更大些,脱北者相关的题材也比较猎奇,但影片的气质极为冷静,角色的表情仿佛被吉林的冬天给冻住了,全部是僵僵的,以此表现出村民对脱北者的复杂情绪。
一江之隔,两个国度,三种归属。大爷家的哥哥年轻时去韩国打工回来给我们讲一个月一次假期如何在灯红酒绿间想念故乡。四姨和大姨家的哥哥则会时常讲述在延边大学的求学以及懵懂的爱情。种族,国家,宗教,信仰,在最原始的状态下都是狗屎,我们是有道德的人类,我们也是最可怖的动物。
喂喂我是村长,宣布一个好消息,老朴家商店来了一车明太鱼,没现金的赊账也行,春天会高价收购明太鱼干,快来拿些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