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这部传记电影的一开场,主人公安迪·考夫曼(金·凯瑞 Jim Carrey 饰)却向观众开了一个谢幕的玩笑。安迪自幼喜爱表演,成年后顺理成章成为饭店驻场演员,但事业并不顺利,一次他模仿猫王的表演引起好莱坞经纪人乔治注意,后者将他引荐到电视界。上镜前安迪从东方修行课上得到幽默的秘诀:沉默。安迪凭独特的表演风格得到观众青睐,进入了他颇为鄙视的情景喜剧领域。他创造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物托尼·克里夫,然后借克里夫的身份实现他和搭档的疯狂点子,和女人们进行的摔跤比赛更把他的疯狂推向了巅峰,安迪不断的戏弄、激怒观众,直至他患上癌症却没人相信,但安迪不在乎,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无止尽的玩笑……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爱在日出前鲁菜 第一季数分钟的赞歌小偷阿星袭击第一季镖王太阳高照645爱情猎杀陨落流氓警察1990汤之国哥们儿2022被爱的人银河战将女侠黑蝴蝶法钱最后一搏2024失踪的女人 上(国语版)怦然心动的小姐姐降魔传我是你的小幂phone外星神犬非常城市汉斯·季默:好莱坞的反叛者
长篇影评
1 ) 狂欢梦境与荒诞现实的交互融合
——评《月亮上的男人》场面调度 视听语言 这是一部极具游戏感与荒诞意味的一部传记片。以风格化的视听,结合怪诞的表现手法和叙述角度,引领观众来回游走在悲喜两种情绪之中,交织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别出心裁地展现了喜剧演员安迪考夫曼短暂却传奇的一生,让人犹如经历了一场盛大的整蛊狂欢,冲击十足。 主角安迪在一个黑白色调,颗粒感质感十足的画面下出场了,他神经质地冲着镜头不知所云。在巧妙打破第四堵墙的同时也向观众发出了参与这狂欢的邀请函,无形中营造了一种压抑中带有诡异的古怪氛围。而在观众迷茫之时,他又随着背景音乐的节点反复拨动唱片机,录像中的字幕名单随着他的动作上下移动,这样风格化的处理大大拉进了观众与安迪的距离,也增强了影片的趣味性。在将近15秒的黑场过后,安迪的再次出现使观众的惊喜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画面也从黑白转向彩色,在放映机视角的小框架构图下,昭告着这一场整蛊狂欢正式开始。 在这一场由安迪亲手编织的癫狂的梦境中,他首先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者,永远领先于影片中的观众。无论是和粗鄙狂躁的“恶棍”托尼携手在舞台整蛊观众,还是和大力士拳击手策划一场闹剧引起观众的愤怒,他都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掌控欣赏着观众们意料之中的反应。在拳击场摔跤的场景中,安迪的对手面容一个又一个叠化模糊,自然地推进了时间跨度,高密度剪辑点下粗鲁原始的打斗动作却搭配上优雅轻快的配乐,镜头也由低机位逐渐升高,最终定格于俯拍,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和荒诞气息。此类实验性的蒙太奇运用,令多处戏剧性情节的有机串联,通过相似场景的再现,台词的重复,自然地转场,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 安迪是不可理喻的,亦是清醒的。他高高端坐于遥远的月亮,镁光灯如同月光一样打在他身上,多处关于舞台的拍摄,安迪作为主体,舞台以暗色幕布突出他的存在,亦是他的伪装和面具,是他与观众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镜头在他与台下观众之间来回高频率的正反打,背景音是场景所带的自然原声,唱片机老久的英腔朗诵声交杂着台下观众不满的叫骂,将这个片段的荒诞诡异推向了顶峰,同时营造了一种高级而有嚼劲的质感。这样鲜明的反应对比更显得讽刺异常。他可以扮成拉特卡,猫王,甚至是伪装成脾气暴虐的托尼。却没有人真正了解真正的安迪究竟是什么模样,毋庸置疑,他是孤独的,也是不被理解的。 而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基调氛围由喜转悲,喜剧与恶作剧意味的幕布被毫不留情的扯下,将之下的荒诞与凄怆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安迪被查出癌症躺在病床上时,随着他主观视角的变化,只有一个医生手部动作的特写,全程没有出现医生的脸。镜头逐渐推进,原来所谓的救赎,也只是自欺欺人,下一幕即是安迪表情的特写——一个又哭又笑,极其复杂的神情,而四周画面一转,他只露出头部,被大红色被单所包围,形成了一个框架对称构图,此时,安迪心中的无措与茫然一览无余。原来他也只是一场狂欢梦境的参与者和牺牲品,而在这一刻,他也真正地从月亮上跌落,活在了他人的恶作剧中。 影片在结尾与开头形成了一个闭环,狂热与悲凉,梦境与现实,以一种恶作剧的狂欢派对的形式,将相对真实的安迪考夫曼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是观众真正所收获的。
2 ) 你若娱乐这世界,这世界也将以娱乐回报你
放羊的小孩子一个接一个的恶作剧断送了大人们对他的信任与耐心,也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很不幸地,安迪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成名之前,为了能赢得在酒店表演的机会,他装口齿不清,他装猫王,他的目的很简单,只为搏君一笑,获取温饱。
然而,成名之后,他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有能量了,于是,一个想法也在他的脑海里萌生:他想要看跟观众们玩一玩,想要看看那些一直看他出丑的观众们出丑的样子。所以,他先试图让观众站起来看看电视是否出问题,接着又大闹现场、把观众们弄得不知所云,最后,他的狂妄达到顶峰,以与女性摔角的形式,获得了他想要的:全世界的唾骂与关注。
我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常常教我们演讲的秘诀:把观众当作傻子,一旦站在台上,就不要有任何惊慌与紧张,只需要想象着自己是对着一群傻子在说故事,不管有多荒谬,只要最终能把一个圈兜圆了就成。
然而,很多年后,我却发现,这句被我一直当作至理的名言,可笑地一塌糊涂。这世界,哪有这么多的傻子,更何况,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一个人,纵然有异于常人的智慧,又怎能百分百保证自己的小伎俩能逃得过所有人的眼光。
在被玩弄、被激怒之初,人们还能抱着看新鲜的态度去看他不合逻辑,不符常理。然而,一次又一次地把观众当傻子,让观众们一再又再一地发现想看小丑的自己变成了被小丑玩弄的人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对他失去了兴趣。
作为一个标准的中国观众,搞不懂他的美式幽默,却看到他声嘶力竭地在角斗台上举着话筒不断地使用挑衅的语句时,就觉得他已在玩火自焚。
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就像是一场表演秀,没谁值得尊重。他觉得自己是为娱乐而生,就也顺带以为所有人都为娱乐而生,在这样的逻辑下,人人都是可以被娱弄的。可是他却忘了,他为娱乐而生是自己和选择和职业,而观众们,只想花钱看笑话,并不想“被”娱乐。
人人都希望自己是世界的重心,没人想要“被”。就连他自己,也曾极度反感被娱乐的日子,所以,面对满座想要看他演小丑的观众,他毅然地决定在短暂的敷衍之后,正儿八经地念一念《了不起的盖茨比》。
如果你本来想去看郭纲德说相声,他却正字腔圆地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新闻连播。你会不会气急败坏、会不会忿忿离场?
唯一一次他想展示自我的机会被观众搞砸了,更确切点,是被人戏不分的自己搞砸的。当他念完最后一页时,无奈的掌声以及寂寥的人影,深深地刺激了他,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疯狂不成魔”的道路。
“当人微笑时,世界爱了他;当他大笑时,世界便怕了他。”
当他的疯狂达到顶峰时,人们对他的热爱早已变成厌恶,他在角斗台上的每一句发言,都引来嘘声不断。
没有人会吃自己厌恶的食物,也没有人会想要看到自己厌恶的人不断出演恶作剧,所以,在电视台去与留的投票中,大部分投了反对票。
世事就是这么地冷漠残酷又因果分明。
他种下娱乐世界的种子,于是,这世界便开出娱乐的花来包裹他。
正当壮年、身体健康、不吸烟的他,居然莫名奇妙得了肺癌,以致于连家人都觉得这不过又是一次娱乐。
跑到菲律宾,想要获得神迹,却发现自己再一次“被”娱乐。
影片的后半断,陡然的宁静与黑色幽默,让人有了思考的空间,烟花之后,黑夜会显得格外重;喧闹过后,安静也显得格外沉。
安迪喋喋不休的语句刚变缓,自己脑子里面的绕舌就冒了出来:
“你若娱乐这世界,这世界也将以娱乐回报你”
最后影片里,安迪曾分饰的角色——托尼•克里夫一年后再次登上了舞台,难道安迪之又是一次被娱乐?满脑质疑的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安迪是真死还是假死。却搜出了一大堆后人加在他身上耀眼的荣光:好莱坞喜剧泰斗、70年代以后美国最著名的喜剧演员、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一个角力运动家,一个喜剧演员,一个民谣歌手……
但,人若已亡,就算给他整个月亮,又能怎样?
3 ) 月亮上的我
(一)月亮上的人 《月亮上的人》。 一部由Jim Carrey主演的电影。 电影讲述了传奇笑星安迪.考夫曼的人生经历。 安迪.考夫曼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5年。就是这短短的35年,却也使人们对他留下了许多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个怀疑论者,是非正统的禅学信仰者;也有人认为他是达达主义式的喜剧演员,第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而考夫曼却宁愿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唱歌跳舞的人”。 按道理,考夫曼对自己的评价应该是最贴切,最到位的。遗憾的是,这个评价显然过于直白和肤浅。而按我自己的看法,考夫曼是一个具有多重和多变性格的人。这些性格是如此冲突激烈不能共存,以至于他不得不借助于演戏--这一可怕的职业。 演戏是一种可怕的职业,我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试想一下,要一个人暂时从自己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剥离开来,去进入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生活场景并要求他表现得一如那个人的自然,这简直像《The Thirteenth Floor》一样荒诞无稽。他完全忽视了人的心灵对周围环境的粘连。当然,戏剧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和心理现象,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的。但可以肯定,演戏作为考夫曼的职业,也恰好给了他舒展各种性格的一个机会,使他能够充分地表现出他的多重性格。同时,既然演戏是他的工作,他就不用在日常生活中去面对自己多种性格冲突的痛苦,而是可以理所当然的借演戏的机会释放出来,既获得了解脱,又心安理得。 比如,在影片中,他除了以考夫曼本人面目出现以外,还多次以一个名叫托尼.可立夫顿的流氓无赖的面目现身。这个可立夫顿,言语粗俗,脾气暴躁,表演节目恣意妄为,胡闹瞎闹,与平日内向拘谨,甚至有点神经质的考夫曼截然不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在的破坏欲,都有一点点流氓无赖,挣脱常理的倾向和冲动,但大多数人都是只有在独处,麻醉或暴怒时才表现一点点。而考夫曼则幸运得多,他可以在工作的同时就把他们表现出来。但他也不幸得多,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只会使本来并不显著的性格分歧一步一步地放大和加深。 他就这样生活着,自得其乐,欣然的接受着在各种不同性格间切换所带来的新奇和刺激。 考夫曼又以哄骗他人为乐。在他与女子进行的摔交比赛中,他被一名男子大力士摔断了脖子。谁知道,这是他和大力士串通好的一次骗局。另有一次,他执意要在节目录像带中加入雪花和上下跳动,只为了让观众们伸手去敲打他们的电视,看看电视是不是坏掉了。 他的恶作剧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当他告诉周围的人他已经身患癌症,不久于人世时,大部分人嗤之以鼻,他的朋友们都好心的劝告他停止这种恶作剧,不要再骗人了。安迪.考夫曼死时,年仅35岁。 二、喜剧与悲剧 这样一部电影,由喜剧明星主演,讲述的是另一个喜剧明星的故事,我们自然有习惯性的期待:即使不是一部纯粹的喜剧,至少也少不了轻松活泼的情节。然而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部正剧,甚至极偏向于悲剧。 这情形倒有点象大话西游。第一次看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部出色的搞笑片;几年之后,每个人都说它是一部爱情悲剧。 那么,看来,喜剧与悲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的界限,甚至两者可以在同一部戏上合而为一。 其实不仅是戏剧本身,作为戏剧物质载体的演员,他们的经历也很难说,是喜剧还是悲剧。 很久以前看过对周星驰的专访。令我惊讶的是,生活中的周星驰与电影中的周星驰差别如此巨大。镜头前的他,表情拘谨,语速迟缓,眉头紧皱,电影中那个放肆乖张,火爆叫跳的周星驰不见了一丝一毫的踪影。 他的头上已经有了丝丝的白发,我宁愿认为那都是疲耗的才思。 搞喜剧和搞悲剧哪个更难?个人认为喜剧更难。喜剧的某些桥段就像对圣斗士使出的招式一样,第二次便失去了作用。而悲剧中相同的生离死别,即使上演多次,却依然能令人触动。于是,喜剧的创作者必须耗尽脑汁,想出新招。 让一个人笑很难,让一个哭却很容易。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这一切都源于人的本性,源于埋藏在人心灵深处的,对于死亡和灾难的巨大恐惧。欢乐总是短暂,痛苦却可以长存。欢乐就像夜空下墨黑海洋上的点点渔火,而一个巨浪就可以把它们轻轻抹去。当你看到别人的死去,你无法不联想到自己。 喜剧演员就好像是一群被追逐者。他们不得不和自己赛跑,因为不能重复自己,也因此而精疲力竭。这是他们的悲剧之一。而正统评论对他们演技的贬抑,是他们的悲剧之二。传统的评论家总是将戏剧演员视为一群只会挤眉弄眼,耍坏作怪的人,不管他们做出了何种努力。 带给人们欢乐的喜剧明星,他们的命运深处竟埋藏着他们自己都无法把握的悲剧之韵。其实何止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我想悲剧总是大于喜剧的。开始是满月酒宴的喧闹,结尾总是葬礼哀乐的悲凉。序幕是喜剧,尾声是悲剧;情节是喜剧,内涵是悲剧;演员是喜剧,观众是悲剧。 在片子的后面,为了寻找挽回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考夫曼远赴菲律宾去寻找所谓的“神医”。他观看了“神医”为几名患者抓出了“肿瘤”,却无意中发现这些“肿瘤”都是“神医”在转身之间偷偷事先藏在手心里的。考夫曼无声地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无比宁静又无比剔透的微笑。那一瞬间他已经大彻大悟。他毕生所做的努力,也不过是在悲哀的大海上企图掀起几朵浪花而已。他的观众和他自己,就像“神医”手下的患者一样,仅仅是甘心受欺骗的一群。生命本短暂,无人可长生。 三、月亮上的我 考夫曼和他的女友躺在床上。 女友:你是一个复杂的人。 考夫曼:这才是真正的我。 女友(笑了):世上没有真正的你。 事实上,两个人都说对了。 对于具有多重性格的人来说,他的性格的复杂度和多变性就是他本身最大的特性,也是他人格的基础。如果你想要把握这个人,恐怕也只有从这一点入手。然而,如果把他的性格分解开来,那么他在某一时刻只可能表现出他性格的唯一一个侧面。既然这些侧面都代表了他,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或许你可以选出几种性格作为一个主导,但哪一种才可堪称为他的代表呢? 你可以选择“都是”,因为这些侧面确实都属于他;你同样可以选择“都不是”,因为其中任何一种都只是单独的一部分。 Sean说过,在生活中和我说话,和在网上看我的文章,感觉就像是两个人。 某mm说过,和我聊天,和看我的文章,差别实在太大。 我想这似乎很滑稽:网外的我和网内的我不一样,聊天的我和写文章的我又不一样。这些毫无疑问全都是我,这些又全都不是我。 那么,我在哪里? 我想,多重性格的人,首先会是一个对生活有着极端感想的人。我们的生活中,有着许多相对的因素:正与邪,对与错,上升与堕落。在一般人,尤其是那些表里如一的人身上已经变得融合了,可以用类似溶液浓度或合金成分一样的概念来衡量他们的人格。而多重性格者则不然,在他们身上,这些属性虽然共存却永远不会打破彼此的界限而融为一体。他们更喜欢以一种单纯的方式去对待生活的每一种单纯的属性:以对为对,以错为错,持正以待正,持邪以待邪。 多重性格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在性格变换的刹那,仿佛跳出了一个人的躯体而进入了另外一个,又可以体验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在单一的人生进程中却能感受多种不同的人生况味,这种诱惑确实无人可以抵挡。 不止一次,我让不同的灵魂进入我的身体。那时我仿佛走在高峻而贫瘠的山崖上,却可以柔软如风般地飘过巨大的断面,黝黑的深渊。在陌生人面前我更喜欢表现出一个并不常见的自己。看着他们可能不会用来对待我的态度,听着他们可能不会对我说的话语,我躲在克立夫顿的躯体里,异常欢喜。 当然,这种欣悦必然会有适当的代价。因为它触动了一个根本的矛盾:人躯体的单纯唯一和性格的变化万千。 不管你以哪种性格说了什么,不管你以哪种性格做了什么,到头来这一切都会着落在你唯一的躯体上。人们永远不会质问你的性格,他们找的只是你。考夫曼在得知自己患癌症之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朋友们。结果除了他的女友因为关心他而神情紧张外,其余的人,包括他最亲密的搭档在内,和不屑一顾,或哭笑不得,要求他不要再继续骗人了。原因当然很明显:考夫曼已经骗过他们那么多次了,这一次他们也只能靠惯性去判断。 应该怪他们吗?当然不能。最不该怪罪的就是他们。 他们的反应绝对正确。 甚至在现实中,类似的故事也在上演。吉姆•凯瑞的两部正剧《Truman Show》和《月亮上的人》票房成绩均不理想,屡遭恶评。然而,他今年重返疯狂搞笑老路的《Me,Melf&Irene》,这样一部无稽的片子,票房却高奏凯歌。理由很简单:观众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老样子,他们不喜欢凯瑞的新行当。他们看不到凯瑞为了获得奥斯卡的承认而付出的努力,他们看不到凯瑞为了演好考夫曼,甚至跑到他的故居去住了几个月。他们要的只是原来的凯瑞,要的只是他的面部扭曲,要的只是他的手舞足蹈。 会有人把我的表现放大到我的人。会有人因为我的狂浪而否定我的责任感,会有人看到我的文章就看不到我的粗鄙。可是,人活着是否意味着必须将自己固化?或许每个人都致力于给别人一个可以确定的印象,或许表里如一是一种美好的品德,而我却想以一个舞蹈中的大跳,甩掉身上贴满的标签。 我可以唯唯诺诺,这样人们不会注意到我。 我可以神采飞扬,这样人们才会注意到我。 我可以好,因为这无所谓。 我可以坏,因为我不在乎。 当一个人踏上了月亮,还需要在意些什么呢。
4 ) 它应得聪明人的赞誉
看完《月亮上的男人》,我记住了两句台词。 "Who should you entertain? You or the audience?"“你该娱乐谁?娱乐你自己还是娱乐观众?” "这也是行为学研究的巅峰。" 《月亮上的男人》太突破了。它打破了——或者保守点说,至少它尝试去打破银幕空间和影院空间之间的界限,把电影院中的观众也拖进——说得礼貌一点,是请进电影中来。他一开始就明确要取悦,不,欺骗,不,玩弄现实中的观众。银幕中的观众被安迪耍得团团转,而银幕外的观众也一样。现实中的观众看着银幕内的观众被戏弄,一点都笑不起来,入戏的时候,会和银幕中的观众一样困惑或愤怒;不入戏的时候,会紧张地防备接下来冷不丁的剧情逆转。无论入不入戏,真实的观众总逃不了被调戏的命运。 因为银幕中还有银幕和剧场这一存在,这部电影的空间结构变得极其复杂。我们看观众看安迪演戏。观众不知道安迪在演。我们知道观众不知道安迪在演。观众以为安迪在演。我们不知道观众以为安迪在演。我们以为观众不知道安迪在演。我们以为观众以为安迪在演。我们不知道观众不知道安迪在演。就算我们以为观众以为安迪在演是事实——总会是事实,我们还是死也摆脱不了模棱两可的怀疑,因为我们不知道安迪何时会揭开他在演的真相,每一次小起伏时我们都会随着银幕中的观众不禁怀疑,是不是我们错了?是不是这次安迪在演的其实是真的。 安迪这个角色在影片中打破了观众的界限,把所有的剧中人都变成了可能的观众。对于现实中的观众来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剧中谁到底才是观众,甚至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把自己看做观众什么时候又不是。剧中严肃的ABC老总突然灵机一动摇身一变就宣称刚才在舞台上发生的殴打事故是一次表演,结果安迪告诉观众刚才的不是表演,安迪把老总的自作聪明的伪装和自己不留情面的揭穿一起变成了一场表演。我们这些现实中的观众首先搞不清楚殴打事故到底是不是预先安排好的,最后又搞不清楚殴打再掩饰再揭穿这一整套是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聪明的观众一定会觉得自己被耍得团团转的。糊涂的观众只要方便地和剧中的观众一样就好了,被骗的时候真的感到愤怒和鄙夷,被骗过后开心地大笑和鼓掌。 我们的主角安迪·考夫曼Kaufman,难道和欧文·戈夫曼Goffman没有关系吗?《月亮上的男人》探讨的就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或者说是玩了一个社会学的游戏,在文本上做了一次社会学模拟实验。它的主题,比起影片空间的多层嵌套,真伪逻辑的多层嵌套反而是赤裸裸的简单明确: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前台和后台完全混同,结果会是如何?《月亮上的男人》戏谑地提出了一种假想。 但实际上,颠覆戈夫曼的假想根本无法在真实世界里发生。影片中的安迪不可能真正存在,人不可能承受认同的不确定性,观众/公众其实也不可能像影片中那么傻。影片是在假设了有这么一个完全自我的人和一群完全傻掉的观众之后才得以进行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影片把对真实观众的欺骗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银幕内观众的行为和反应其实也只是拙劣的社会表演罢了。银幕中的观众和银幕中的安迪联合起来把我们骗了,现实中哪有这么单面化的观众呢,简直和三流小说一样。能够意识到此的人都不是银幕中的那些。 《月亮上的男人》主题的另一半,和《楚门的世界》是一样的。它没有后者那么直白,因为导演风格的不同,它把讽刺埋在整体的结构中。影片中的观众,他们本是对眼前的粗鲁、歧视、暴力感到愤怒,但当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一场表演之后,他们就能开怀大笑了,好像一经过表演,所有的粗鲁、歧视、暴力就都消解了,粗鲁、歧视、暴力的形式就再不是粗鲁、歧视、暴力,而是用以娱乐的符号。而《月亮上的男人》更加强调的,是这些用以娱乐的符号无时无刻不在小屏幕上播放,小屏幕二次平面化了表演,那些狗屁伦理道德的分子是透不过屏幕的。而且别忘了,最后的最后,所有的影像要通过现实和故事之间的那层银幕,才达到我们的眼睛,这是三次平面化。在这一意义上,影院银幕和我们就是小屏幕和电视观众,影片把现实的影院空间也拖了进来,我们在做的很可能是无形中的自我嘲弄,自我批判。我们很多时候和影片中的观众没什么两样,不仅是行为上,而且在性质上。 安迪的欺骗是越滚越大,剧情层层推进,死亡的结局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本来在喜剧的最后豁然一悲,心生万千感慨,想想,已经足够了吧。谁知屏幕的魔力连死亡都超越了,连死亡都是一场戏。只有娱乐永存。 对了,我还记得一句台词。半场的观众半信半疑地等到演职员表的最后,音乐结束,只等来这句: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tonight!” 到底是真是假,这些都不重要,在屏幕中,在报纸上,在图片里,在舞台上,不管是真是假,相信就好了。反正不会在书里,不会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后现代的境遇。 (对了,影片里有一个捡肥皂的场景,货真价实的表演捡肥皂。而且提示,这部片只适合在电影院看到最后。。)
5 ) 笑话
我有一个微博,我关注那些我想关注的人,可是我从来不说话,在他们的被关注列表中,我是沉默是冗余是不存在的空气。
我喜欢奇奇怪怪的名目,我不喜欢沉闷到死的格调,不喜欢学院派们一眼一板的走位,分毫不差的镜头和色彩,严谨到拘束的表演,和有意心身但又过于沉重的话题。
后来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月亮上的男人》。我看到金凯瑞夸张的面目,我以为又是一部《阿呆和阿瓜》。我以为接下来又是放肆热烈的青春,洒脱自我的时光,没皮没脸一笑而过的一个半小时。后来我发现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那个结局。
我以为漠然的态度是永远地抽离事外,可是那个过度表演的凯瑞先森告诉我说,真正的漠然是完全地投入,纯粹的疯癫。不单要认识到人生不过是场玩笑,更要用力地参与到玩笑里来,还要活得比别人更像一个玩笑。
我觉得安迪先森最适合活在我朝的晋代,嗑药,写词,放浪形骸,还有一包人给你捧臭脚,脚越臭捧得越开心越卖力。或者也可以穿越《唐伯虎点秋香》里,神马“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要是从凯瑞同学嘴里念叨出来,那效果绝壁的离间绝壁的后现代绝壁的有味道。
最后我要灰常第十放映室地总结一句:夸张的表演和荒谬的情节使演员和所扮演的角色之间形成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带来的是观众超越电影情节,寻求表演背后的深意。喜剧大师们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出出人间的悲喜,更是一次次人性的升华。
我的吐槽到此结束,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6 ) 酒极则乱、乐极生悲
Andy Kaufman,一档称为Saturday Night Live节目的主持人。电影中,Jim Carrey纯熟的演技复活了这个舞台上的怪异天才。他的高傲、自负,目中无人,一次次在节目中出言嘲讽观众,然后又在玩过火的时候自我诋毁,取悦观众。他在舞台的镁光灯下迷失了自己,那厚重的帷幕把他的世界包围起来,他成为了月亮上的男人。孤单寂寞。唯有表演……
天才和疯子的界限短的无法丈量。交汇处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大家忽略了他也是个普通人。他病了,陷入了绝症。时日无多,终于向观众做了坦白。但换来的却是一如既往的笑声,Andy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脱口秀主持,大家已经习惯把他的言语当做玩笑。于是他选择了沉默,直到死亡。
在结尾处,才明白,Jim Carrey为什么能如此投入的演戏。原本的喜剧,看到结尾,才悲从中来。嬉笑怒骂、乐极生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
Hello,My name is Andy and this is my poster
You don't know the real me……
可惜,这句话他没有说完……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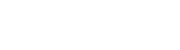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是他太疯癫,还是世人看不穿。
演技有点让人害怕,太棒了!
应需要把电影和真实事件脱离开来,电影完全可以看作是导演对一个“喜剧明星”的自反书写,将之融入好莱坞、综艺节目、脱口秀乃至舞台演出的形式中,一场场如同行为艺术的演出,观众根本无法用常规的观看直觉来看待这些演出,无法分清到底哪些是表演哪些是真实。导演也如同考夫曼一样,让我们在电影面前失去了探究真相的勇气,因为是真是假根本无从分辨,或者说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面对这些谄媚的、精心操控、设计的,刻意的虚假的演出中间离出来,打破那些陈规惯例的形式,用偶然性、模糊性、自反性来刷新被主导的观念形式,这本身就是一次行为艺术。
很好看啊,剧情有深意
美式笑点没GET到,但金凯瑞演技很赞
tbh, i dont get this movie... its attractive, but when its done, i aint know nothing at all...
本片获200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
演技真的超棒了
我曾在新东方面试上表演猫王~当时就是跟学的他那段~很成功~2012.6.4经过近两周中午午餐时间最后看完。片子很好,很喜欢这个敢玩的人,他用自己来玩玩了他周围的世界。好几处都很感动,但眼泪始终流不下来,很奇怪。结尾用电影使这部传记有了超现实的色彩,挺巧妙的。演员就应该有另外的人生呀。
这种不是一分就是十分的电影,评的好辛苦
没太懂这里的幽默
说个笑话纪念我
蛮久以前看过的,剧情有点忘了。但是演的很不错
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谎话只能说三遍。
看得我好痛苦/这就是那种不是给1分就是给10分的电影
电影不错。Dylan Moran的Black Books,John Cleese的Fawlty Towers,Jim Carrey的Andy Kaufman,英美这类用力过猛的喜剧效果真心不是我的菜。
喜剧其实是一种判断,每一个笑话都是一种判断,你必须去判断它。演戏则不然,演戏是一种体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我完全了解……但是我不了解他为什么还不是影帝…
感觉有点讽刺意义啊
人的一生都是假象,甚至这个人给人们的感觉只是个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