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随便扯扯】
我身边不乏这样的朋友,喜欢他们身上那天真烂漫的性情。所谓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儿呀,“思无邪”的宝贝。但他们,如英格丽,会不会有时让人觉得些许的令人讨厌呢?比如她性欲上放荡的那一面。(开头就自述:我赞成滥交,因为人绝非万物之灵。【三地翻译版】)这和大部分人们的想法我一直觉得性欲和艺术无法分离。艺术的最终会上升至性的层面。但若真真抑制住了,也不会有这么多美好的诗句留给我们了吧。他们有时真的会太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以至于太以自我为中心,为世人不容。
但无论如何,都是让人爱恨交加的可人~想起还是会默默笑的吧。
2 ) 病态英格丽:原谅我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
因为人类绝非万物之灵
我支持酗酒,反对动脑
反对那些虚情假意的社交
也反对沉重死寂的堂庙
我支持残穷老弱无忧无惧,抵死而活
我支持对体制的麻木·和精神上的顿悟
支持那些无依无恃的非洲人
支持杀人夺命
死亡正在证明活着有多虚假
劝君忘了正义,世上没有这种东西
忘了手足,都是云烟一场
忘却爱情,它全然没道理
这是南非女诗人英格丽琼蔻的传记片,影片一开头就是诗人这首毁三观的独白,实在让我大吃一惊,接着感叹:朕喜欢你这种臭不要脸的态度。
我实在不敢严肃地讨论她,因为不论是她的政治立场还是爱情生活,讲起来都太痛苦,太沉重了。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他的父亲把持着出版审查制度,而她不断目睹种族间的仇杀和和警察的血腥镇压,成为一个持相反政见的作家,自幼的成长中她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可最后父亲给他的评价是”赞成滥交?你搞遍了你身边的所有人……而这份名单还在不断加长……你这烂货……我不想再见到你!“
她渴望爱情,却缺乏安全感,她一生挚爱的情人是有妇之夫,是的,几乎和那个朋友圈的所有男性交往。她在困顿中挣扎,在警察局和精神病院中辗转,最后孤独地走向大海,结束了32岁的人生。
她是黑色的蝴蝶,想要自由,但是注定要被囚禁,注定要早亡。不是天妒英才,而是她本身就是病态的,但”你是有病的,所以被宠爱,常人难道比疯子可爱?“
3 ) 曼德拉去世了,我纪念的却是她。
我想到的却不只是这首歌,而是一部电影,一个女人,一个南非女诗人——英格丽·琼寇。
当那个晚上独自看这部电影时,仅仅是想了解她,但没想到那里面提到曼德拉读过她的一首诗,以为没留在脑海,在今日得到曼德拉去世讯息时,它浮现了。
我想我还是想说关于她。
和所有诗人一样,她有敏感的神经,特立独行,对诗痴迷,而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也许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即使条件不错,她还依然将幼时住过的小屋当做她的避难地,每当烦闷时,就将自己关在那里。那个不大的空间,泛黄的墙壁之上,写满了她灵光闪烁时迸裂出的诗句,诗是她的武器,她的药,她的魂灵么?
作为一个追求独立、崇尚自由又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性,生在彼时充满种族隔离之痛的南非是不幸的。高压严苛的政治文化桎梏令她窒息,加上一个专制严肃甚至冷酷的父亲,她的心灵自由如蝶,却总被现实的茧重重束缚,连破茧而出的机会都没有。同为女性,对她的怜惜重叠在那些画面中:她写好一首诗,急于想得到父亲的肯定,她心跳如鼓,她狂奔到父亲那里,她那渴求希冀的眼神……但是父亲简单得读了几句,就当她的面撕掉了它。她一直没被承认,一直被压抑。种种不公种种残酷种种迫害,却激发了她的纤敏,她去看,去写,去爱,去孤独……离家出走,带一只箱子,一个和前夫所生的女儿,还有那台斑驳的打字机。她不放弃任何在脑中蹦出的诗句,写在烟纸盒上,写在药品说明书上,写在可以写的一切纸片上,塞在她随身携带的手袋里——她一直珍视着它们,如同珍视自己的孩子一样。
两个男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她爱着却不能与之结合的情人。对于他们,共同的情感是一边渴望亲近,一边却想着逃离。这种矛盾让她煎熬,被否定,被放弃,被冷落,于是她放任、挣扎、自虐……终于不堪忍受,被送进精神病院。
感动的是什么呢?是她深爱着的男人杰克去精神病院探望她。雪白冰冷的墙壁以及病床,瘦得皮包骨的她,却依然有一双迷离的眼。她告诉他,我丢了我们的孩子,这个秘密直到她疯了的时候才告诉给杰克,但结果并没有怎样的不同。就算他们的孩子还在,就算杰克还爱着她,和她一样,无比的爱。
但杰克毕竟拿走了她所有的手稿。在他依海的房子里,那些零碎的纸片铺满了整个地板,接下来就是拼凑、拼凑,拼凑成一本诗集,也拼凑成一个真正不一样的英格丽·琼寇。杰克帮她成为了一个优秀的被人所知的女诗人。
“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飘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一首中国歌这么唱的,也可以是英格丽·琼寇的心声的吗?
出院后,她见到了自己平生第一本诗集,杰克将诗集交到她的手中,但杰克还是杰克,她却不再是她。
总要履行一个告别仪式。暴雨之夜,她穿着雨衣,赤脚走到杰克海边的小屋,她让杰克读出笔记本上抄写的惠特曼的诗:
无论去向,我们一起迎战未知
也许会更好,当然,会更懂事
说不定是你带我,领略诗歌真义
说不定是凡夫如你,在毁灭反复
而今现在,终能永别,再会吾爱。
再然后,她冲出了门,冲进了风雨之中,扑向了无边大海,扑向了毁灭,扑向了黑暗。
总是离不开大海。年少时,赤足的她从潮汐中带着一裙兜的鱼奔回家,接着奶奶去世,她被父亲接走,开始了她叛逆而痛苦的成长期;离异后的她在海中游泳遇险,那个救起她的作家杰克成了她的情人,这场苦痛的爱恋影响她至深;最终,她选择在一个有风暴的暗夜走向大海……这短暂而瑰丽的一生就仿佛对抗命运浪潮的一生,终究,她还是孤独至死。
今天,因为曼德拉,也让我们同时纪念一下这位被曼德拉称赞为南非最优秀的女诗人英格丽·琼寇。
4 ) 《在尼扬加被士兵枪杀的孩子》by英格丽·琼寇
英格丽·琼寇 (Ingrid Jonker)
南非诗人Ingrid Jonker的诗文,不但精笔传书了心灵轨迹,更有历史的血迹与呼吸,《黑蝶漫舞》不只是她的传记电影而已,因为编导选材时,兼具了诗人的气息与红尘的扰攘,因而饶富韵味。
有句老话:「做艺术家之前,要先做人!」把艺术家换上任何的身份名词,这句话都依旧试用。荷兰导演宝拉.凡德.奥斯特(Paula van der Oest)所拍的《黑蝶漫舞(Black Butterflies)》,就是把艺术家换成了诗人。
《黑蝶漫舞》的女主角Ingrid Jonker是南非著名的诗人,在世只短短地活了卅二岁(1933-1965),却因为见証了南非政府施行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的诸多不公不义,曾经写下了《The child who was shot dead by soldiers at Nyanga(在尼杨加被军人射杀的孩子)》等著名诗篇,在诗人之前,先做了南非人,因而备受当时执政的南非国大党排挤,却赢得世人的广泛尊重,其中又以南非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94年的国会演说上,也朗读了Ingrid Jonker的这首诗,有了家乡、土地、政治与人民的背书,更让Ingrid Jonker的文学与人生高度更加特殊。
法国大雕刻家罗丹曾经说:「艺术家不是来解决人生问题,他承接了人生的问题(An artist is not one who has solved life's problems. He is one who accepts life's problems.)。」Ingrid Jonker确实曾经用她的笔记下了时代的脉博与人民的声音,虽然政治人物的背书,让她的诗作有了更浓烈的国族氛围,但是《黑蝶漫舞》并无意突显她的政治意识,更无意大肆批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点到为止的叙描,以及画龙点睛的最终素描,即已足够,《黑蝶漫舞》的目的还是在介绍Ingrid Jonker这位诗人,这位女人。
电影从海开场,亦从海终幕,海与生命的对话,很能注解Ingrid Jonker的生命历程。首先是穷苦童年的靠渔猎维生的青涩记忆,继而是她险些在海洋湾流中溺毙,幸运地文路过的作家Jack Cope所救,但是最后,人生一团混乱的她还是投身大海。全片有关海的意像,都带有浪漫的感伤,从青春冒险、寻欢到混乱,她的爱情向往与幻灭都有了依靠的空间,提供了感性的视觉空间。
男人则是《黑蝶漫舞》最核心的爱恨主题。围绕着Ingrid Jonker生命核心的两位男人分别是父亲Abraham Jonker(由鲁格.豪尔/Rutger Hauer饰演)和男友Jack Cope(由尼恩.康尼翰/Liam Cunningham)。偏偏,这两个人带给她的都是爱恨交织的生命感怀,相互牵扯,也相互激荡,Ingrid的精神异常,有些来自生理遗传(母亲亦曾接受精神治疗),有些则是来自男人带给她的幻灭与失落。
Ingrid的一生都在争取父亲的肯定,却也在对抗父亲的思维。前者在于Ingrid的父母亲早早在Ingrid还在娘胎时就离了婚,Ingrid要到抚养她的外祖父母都往生后,才知道父亲长成什么模样,缺席的父亲与疏离的父亲,让她的家庭拼图永远缺了一大角;更大的遗憾则在于父亲学问渊薄,在政府担任文化高官,Ingrid是多么渴望自己的诗文创作能够得到父亲的肯定,偏偏,Abraham 吝于赞美,更无奈的是眼高于顶的Abraham,公务责任之一就是做思想检察,负责查禁所有「不当」书刊,Ingrid与父亲那段「种族隔离」有如「纳粹」的辩论,就委婉点出了父女之间永远不可能和解的思想距离,父亲的冷漠让她在亲情上备受煎熬,对抗父亲,却让她在理智天平上取得傲人的质量。
《黑蝶漫舞》最动人的两场戏都发生在Ingrid的小房间里,她认识父亲时,Abraham已经再娶,只能教她住进黑人帮佣的小房间里,但亦在那间斗室的墙上,她用炭笔写下了一行接一行灵光闪动的诗句,她在餐桌上受了气,先是父亲来致意,继而是男友来求欢,「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陋室春情,处理得何能动人?!最后则是父女天人永隔时,父亲才又进入小屋,抚摸着小屋墙上的诗文涂鸭,有如此文采的女儿,他理应骄傲,但是父女的心理距离,却比天地更遥,他又怎能无叹?总是一副扑克脸的鲁格.豪尔,依旧用他的冷漠无情来诠释Abraham,却也意外显现了极具说服力的巨大阴影。
Jack Cope则有多重身份,先是救命恩人(免于溺水),继而是晋身文坛,结交文人,又兼政治和人权启蒙的导师,却也是带她挑战世俗礼教的狂野情人,更是真正读懂她诗文创作的知音挚友,当然,亦是最摧折她心肝的自私恋人,她们的爱恨纠缠,只合用世事难两全的轻叹来注解,但是Jack Cope一句:「妳把我掏干了。」的告别心声,亦非常宽广地包含了两人之间极其炽热的性爱、文艺创作和情绪角力的诸多矛盾。电影中的男女交欢情节,其实都是Ingrid 主动燃火,甚至还能写下女性主动的生理反应:「以我的乳临摹你的掌。」都充份显示了她敢于求爱、示爱的主控性格。《黑蝶漫舞》最动人的基调就在于Ingrid的敢爱敢恨。
平心而论,《黑蝶漫舞》对于人生细节的描写,往往失之简略且粗糙,但是关键字都能紧紧捉住,才得以超越《痴情佳人(Lady Caroline Lamb)》和《瓶中美人(Sylvia)》【这个翻译好】的格局,才不致于把一场倾斜不对称爱情,一面倒地怪罪于诗人拜伦或的Ted Hughes寡情薄义,反而让被爱情焚身的Caroline Lamb或Sylvia Plath变得神经兮兮,得不着观众的同情与怜悯了,Ingrid其实是不屑这种廉价的同情的。
《黑蝶漫舞》的开场是由Ingrid Jonker朗诵自己「认同杂交」的诗句开场,时隔五十年了,依旧大胆前卫;《黑蝶漫舞》的终场则是由曼德拉总统朗读她的《The child who was shot dead by soldiers at Nyanga(在尼杨加被军人射杀的孩子)》。前者是诗人的心灵呓语,后者是诗人的理智抗争,诗人的一生,人的选择,就在不同诗文的选读下,完成了塑像浮雕,够让受到诗文感染的观众(或读者)急着想要再多读两首Ingrid Jonker的诗......一部诗人电影能有如此撼动力量,已然足够了。
她是非洲人,也是非洲人。例如,纳尔逊·曼德拉介绍了Ingrid Jonker,他刚刚读了他的诗。他的孩子并没有在1994年第一届民主选举的议会开幕会议上死亡。
乍得诗人尼姆罗德的天赋是将两个不同寻常的命运——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命运——和另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命运联系起来的。在罗本岛救生圈里活下来的那个31岁在岛外自杀的那个。
曼德拉在尼姆罗德的羽毛下,打算从早到晚在火炉里打碎埃及,尘土飞扬,矿渣飞扬。Jonker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孩:她生活在紧张的溪流中。她在一个失衡的母亲和一个怀疑父亲身份的父亲之间留下了艰难的过去。他的傲慢和慷慨使他拒绝种族隔离和他的清教徒主义。
这场悲剧发生在1960年,当时在开普敦以南的一个黑人乡Nyanga举行了一次反对护照的示威。一岁的Wilberforce Mazuli Manjati生病了。他的父母带他去医院郊区的汽车不是劳斯莱斯,而是奇迹般的燃料。他们被困在人群中。他们的车抛锚了。士兵们都在玩忽职守,开火。孩子头部中弹。
英格丽·琼克尔非常激动地与家人见面,随后她写了一首今天著名的诗,总结说:他到处都是想在尼亚加太阳下玩耍的孩子。没有证件。
他的朋友们正承受着不出版这首诗的压力他的父亲,负责审查,他在议会中的怨恨。文本最终在获得文学奖的文集中发行。然而,同一天,这位年轻妇女失去了工作和她的情人André Brink。1965年7月,她自愿淹死,标志着整整一代人。
一句关于诗的后经故事。在曼德拉耳边吹这首诗的人叫Jakes Gerwel。这位讲南非语的梅蒂斯学者给了我种族隔离的时间:迫使我们重申,我们不如他们聪明,白人最终在我们的头脑中灌输了怀疑: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影响。曼德拉选择了这一有文字意义的目标作为办公厅主任,帮助他为梅蒂斯人和非洲人世界搭桥,这并非偶然。
让我们感谢荷兰作家们突出英格丽·琼克尔的形象,并赞扬尼姆罗德为使我们活下来所做的工作。
尼姆罗德,孩子没死布鲁诺·杜伊版,2017年
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的Ingrid Jonker并没有死于Nimrod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女人。她是一位处于社会边缘的非洲诗人,反对脆弱的种族隔离,她以着作激励着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1994年,曼德拉对英格丽·琼克尔说:在绝望中,她庆祝了希望。他在南非第一届民主议会面前这样说。曼德拉是一个经受了27年监禁的人,其中14年是因为他反对种族隔离的思想而被隔离的,他学习了压迫者的语言非洲人,为了维护平等的希望而放弃了一切。因此,他选择在混乱的议员面前朗读一首白人女孩的诗。一篇文章有力地打击和编织了南非青年诗人Nyanga被士兵杀害的孩子留下的未完成的画布。
谁是英格德·琼克尔?最重要的是,像Doris Lessing这样的孩子无法忍受周围的人不给黑人家庭佣工以人的地位,而黑人家庭佣工是一个热爱在男孩区度过时间的小女孩,在那里,她感到自由自在,并受到一个聪明、活泼的环境的刺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内心总是从外面渗透进来:英格丽以思想与语言相适应的速度行驶。使她更接近曼德拉的是他的反种族隔离思想、他的团结愿望、他为了更普遍的理想——人的自由而放弃家庭。使她与他分开的是他对待妥协的态度曼德拉是一个既能在律师事务所秘密运作又能在游击队秘密运作的人。英格丽从小就放弃了,直到不再可能。她拒绝接受朋友们的波希米亚、自由和进步的世界,从而消除了误解,燃烧了善良的意识,把蜂蜜带回蜜蜂,海洋回到海滩,视野变得模糊。英格丽生活的社会边界渗透进她的鼻孔,吸干她的呼吸,进入她的肺部:这些边界以前所未有的暴力侵犯了她。然后,她把自己的胸部拉开,试图团结、修补、团结起来。诗歌诞生了,从小就躺在床上,赤裸着,越来越大胆,勇敢地面对最大的危险:他人。其他人只会伤害她。他的父亲,第一个,议会新闻检查和出版委员会的领导人,公开否认了这一点。她离婚,生孩子,流产,有情人,分手。
反种族隔离会议的诗歌
英格丽喜欢爵士音乐、香烟、酒精、在汽车旅行中迷失方向、冲破障碍、强迫别人完成自己的想法,但她却沉迷于广播信息、孤独的散步、尖叫、激烈的讨论:她的亲人假装看不见她、听她说话、对她海洋的痛苦一无所知,并且是曼德拉用仁慈的勺子收集他的眼泪,是他抓住了他的话的深渊。这名儿童没有在Langa或nyanga/Orlando或sharpe ville/philipi警察局死亡,他在那里头部中弹。不,他没有死,因为他是一个为新的南非挺身而出的孩子,再也不愿意承受痛苦了。当Ingrid Jonker选择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他对国防部队在Nyanga杀害一名20个月大的儿童的感觉时,其目的远不止于文章或短文的见证:在两个世界的斗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时代,Ingrid渴望交流。
事实上,只要他的国家的黑人被剥夺公民权利,被监禁,被谋杀,他的生命也注定会被歪曲,被写在遗嘱里,从而引起社会排斥、断电、失业、女儿被驱逐出境。但是,自从1960年3月21日在约翰内斯堡贫民区Sharpeville发生的事件使她意识到这一点以来,这并不算什么,那里有一万名黑人和平示威者遭到攻击。他们的背上被枪杀,就像牲畜被驱散一样。69人死亡,140人受伤,当时在场,他们只是说,他们再也不能像外国人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旅行,他们的护照上有他们的住址和身份证件。那些继续工作的人被埋在矿井里,埋在希望之下100米之外,而且他们是瞎了眼的。
伯纳德·布列塔尼很高兴对船队关于英格里德·琼克的评论作出回应并向我提供了一个关于南非诗人的小档案。请参阅此处的文章。
//poezibao.typepad.com/poezibao/2014/01/anthologie-permanente-ingrid-jonker.html
L’enfant abattu par des soldats à Nyanga L’enfant n’est pas mort l’enfant lève les poings contre sa mère qui crie Afrika! crie l’odeur de la liberté et du veld dans les ghettos du cœur cerné L’enfant lève les poings contre son père dans la marche des générations qui crie Afrika! crie l’odeur de la justice et du sang dans les rues de sa fierté armée L’enfant n’est pas mort ni à Langa ni à Nyanga ni à Orlando ni à Sharpeville ni au commissariat de Philippi où il gît une balle dans la tête L’enfant est l’ombre noire des soldats en faction avec fusils blindés et matraques l’enfant est de toutes les assemblées de toutes les lois l’enfant regarde par les fenêtres des maisons et dans le cœur des mères l’enfant qui voulait simplement jouer au soleil à Nyanga est partout l’enfant devenu homme arpente toute l’Afrique l’enfant devenu géant voyage dans le monde entier Sans laissez-passer 《The child who was shot dead by soldiers at Nyanga 》 The child is not dead The child lifts his fists against his mother Who shouts Afrika ! shouts the breath Of freedom and the veld In the locations of the cordoned heart The child lifts his fists against his father in the march of the generations who shouts Afrika ! shout the breath of righteousness and blood in the streets of his embattled pride The child is not dead not at Langa nor at Nyanga not at Orlando nor at Sharpeville nor at the police station at Philippi where he lies 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brain The child is the dark shadow of the soldiers on guard with rifles Saracens and batons the child is present at all assemblies and law-givings the child peers through the windows of houses and into the hearts of mothers this child who just wanted to play in the sun at Nyanga is everywhere the child grown to a man treks through all Africa the child grown into a giant journeys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Without a pass
《在尼扬加被士兵枪杀的孩子》 彼得潘耶夫斯基 中译 孩子没死 这孩子举起拳头打他的母亲 喊着阿非利加!呼喊着 自由和草原 在心脏被封锁的地方 这孩子举起拳头打他父亲 在几代人的征程中 喊着阿非利加!呼喊着 正义和鲜血 在他严阵以待的街道上 孩子没死 不是在兰加,也不是在尼扬加 不是在奥兰多,也不是在夏普维尔 菲利皮警察局也没有 他躺在那里,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 孩子是士兵们的阴影 拿着步枪和警棍站岗 孩子出席所有集会和法律会议 孩子透过房子的窗户窥视母亲的心 这个只想在尼扬加阳光下玩耍的孩子无处不在 这个长大成人的孩子走遍了整个非洲 这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穿越整个世界的巨人 没有通行证
1960年3月21日, 夏普维尔 发生了一场屠杀。一股暴力之风吹遍了整个南非。在开普敦,一个躺在母亲怀里的黑人婴儿被白人警察打死。愤怒的Ingrid Jonker来到philippi警察局向尸体鞠躬;她写了这首诗,诗人Matthews uys kriging,他的导师和知己,称赞它是我们文学中最好的自由诗之一。 1994年5月24日,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第一届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上致开幕词时,将这首诗全文翻译成英文。 在阿姆斯特丹等杰克 彼得潘耶夫斯基 中译 我可以说我一直在等你 在西方的夜晚 在公共汽车站 在小巷里 在机场 在运河边 站在泪腺下 你来了 穿越欧洲失落的城市 我认出你了 我做了桌子 用面包酒宽恕 但你却背叛了我 你把你的性别 放在桌子上 然后一言不发 带着对你的微笑 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En attendant Jack à Amsterdam Je peux dire que je t’ai attendu au long des nuits de l’Ouest à des arrêts de bus dans des ruelles sur des aérodromes au bord de canaux au pied du gibet des larmes Tu es venu traversant les villes perdues d’Europe je t’ai reconnu j’ai dressé la table avec du vin du pain mon indulgence mais impassible tu m’as tourné le dos tu as sorti ton sexe l’as posé sur la table puis sans un mot avec ce sourire à toi tu as quitté le monde Ingrid Jonker, L’Enfant n’est pas mort. Traduction de Philippe Safavi. Collection « Poésie » dirigée par Georges-Emmanuel Morali. Éditions Le Thé des écrivains, en coédition avec Zootrope Films, 2012. //poezibao.typepad.com/poezibao/2014/01/anthologie-permanente-ingrid-jonker.html 关于英格丽·琼寇生平的简单摘要 英格丽·琼寇(1933年9月19日-1965年7月19日)(OIS),南非诗人。虽然她用南非荷兰语写作,但她的诗已被广泛翻译成其他语言。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目睹了夏普维尔大屠杀,种族隔离法越来越严厉的执行,以及由政府安全部队和非洲国民大会的准军事组织实施的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琼寇尔选择加入开普敦的种族混合文学波西米亚。在她的诗歌和报纸采访中,琼寇愤怒地谴责执政的国家党的种族政策以及对文学和媒体日益严格的审查。这使她与她父亲公开发生冲突,她父亲是执政党广受尊敬的议员。1965年,琼寇动荡而非传统的爱情生活导致开普敦的文学波西米亚人对她进行社会排斥,导致她的抑郁和自杀。即便如此,琼寇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已经达到了标志性的地位,经常被拿来与西尔维亚·普拉斯和玛丽莲·梦露相提并论。
在这个家庭的两边,英格丽·琼寇的祖先已经在南非生活了几个世纪。她父亲的父亲阿道夫·琼寇是荷兰东印度群岛麦卡萨种植园主的儿子,18世纪初移民到开普殖民地。阿道夫·琼寇成为德拉肯斯坦的学校教师和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看守人。1740年,他娶了雅各布斯·朗维尔的女儿玛丽亚·彼得罗内拉·朗维尔德和一个来自开普敦的陌生女人为妻。英格丽德的父亲亚伯拉罕·琼寇(1905-1966)于1905年4月22日出生在前奥兰治自由州的博斯霍夫区的卡尔方丹农场。1910年,亚伯拉罕因溺水失去了他的姐姐。
正如后来回忆的那样,“我还不到五岁,她在八岁的时候淹死在瓦尔河,就在爱德华七世国王去世的同一天,因为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第二天带着兜帽的马车去镇上取小棺材时,所有的旗帜都是降半旗的——那天我已故的父亲在四点钟叫醒我们,看到哈雷彗星清晰地出现在天空中。我们都觉得很可怕,因为我已故姐姐的小身体还躺在房子里。”
1922年高中毕业后,琼寇在1923年至1930年间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学习。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主修古希腊和荷兰以及神学。然而,琼寇的神学研究更多的是出于取悦父母的愿望,而不是出于真正的兴趣。1928年,琼寇以优异成绩被授予神学候选人文凭。
根据杰克·科普1966年12月在《伦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英格丽德的“母亲比阿特丽斯·西里尔斯来自一个古老的胡格诺派家庭,有几代人的智力造诣。”
尽管西里尔家族的祖先离开法国是为了继续信奉他们的加尔文教,但根据历史学家路易丝·维尔约恩的说法,英格丽德的祖父母对南非的荷兰改革宗教会持“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区不一致”的态度。英格丽德的祖父斯蒂芬妮“史沃特·费尼”(“黑史蒂维”)·西里尔斯(1872-1938)“不爱去教堂,甚至可能被怀疑对宗教漠不关心。”此外,“斯沃特·法尼”有时以机智的漫不经心对待“荷兰归正会威严的牧师”英格丽德的祖母安妮·雷蒂夫·西里尔斯(1873-1957)是一个虔诚的女人,她喜欢向有色人种传教或参加使徒教会,因为他们“活泼快乐”,英格丽德后来写道。
英格丽德的妹妹安娜·琼寇后来写道:“英格丽德一直想听的一个故事是,奥帕是如何嫁给欧玛的。欧玛曾爱上过欧帕的哥哥,但他有像公鸡一样啼叫的习惯——欧玛也会叫,让我们听听它是什么声音——所以她决定嫁给斯沃特·费尼。这个故事总是以‘我以前认为他不会那么愚蠢’结尾”
同样根据安娜·琼寇的说法,“斯沃特·范尼”有“暴躁的脾气”,曾“撕毁文件证明,证明英国人在盎格鲁-布尔战争期间几乎征用了他所有的骡子和马车,并把它们扔回给一名英国军官。”比阿特丽斯·凯瑟琳娜·西里尔斯(1905-1944),是“斯瓦特·费尼”和安娜·西里尔斯的女儿,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学习音乐时遇到了亚伯拉罕·琼寇,并于1930年嫁给了他。
他们结婚后,亚伯拉罕·琼寇首先为国家党做旅行组织者,然后在开普敦为汉堡、迪尔·赫斯诺、琼斯潘和绥德斯特恩等出版物当记者。琼寇尔还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南非荷兰语文学博士学位。他还创办了自己的双语杂志《死亡监测》,用他的话说,他卖掉自己的杂志是为了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新闻和文学。
亚伯拉罕·琼寇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也出版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路易丝·维尔约恩写道,“对他的文学作品的批评反应仍然不冷不热,也许是因为他对受欧洲启发的努韦·萨克利开德(“现代客观性”)的偏好与当时南非荷兰语文学中新流行的忏悔模式大相径庭。英格丽·琼寇的荷兰传记作者亨克·范·沃尔顿(Henk van Woerden)将他塑造成一个世俗的加尔文主义者,并将他描述为一个冷漠、惊慌失措的清教徒。
琼斯夫妇的婚姻也有问题。英格丽德的同父异母兄弟库斯·琼寇后来回忆说,“英格丽德的母亲比阿特丽斯患有幻觉,有时行为不理智——甚至在她离开我父亲之前就这样了。”到1933年,亚伯拉罕和比阿特丽斯·琼寇是开普敦知识分子圈子的一员,他们“加入了讨论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旧开普敦传统。”格拉德斯通
德克勒克后来回忆说,“我想英格丽德在个人层面上找不到任何幸福,这应该从她自己破碎的家庭背景来看。她的父亲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经常变得暴力...我妻子非常清楚地记得英格丽德的母亲在安娜蒂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带着她逃离这所房子的那些夜晚。”
根据英格丽德的姐姐安娜·琼寇的说法,“亚伯拉罕·琼寇并没有像故事所说的那样赶走他的妻子。由于紧张,她已经在瓦尔肯伯格呆了十天,怀孕七个月。他们彼此爱慕,爱得如饥似渴。他嫉妒地指责她说,孩子(英格丽德)可能不是他的。那天晚上她离开了他。她正好三十四岁。”
早年生活
英格丽·琼寇于1933年9月19日出生在她外祖父位于北开普道格拉斯附近的农场。英格丽德出生前不久,她的母亲比阿特丽斯和妹妹安娜离开了亚伯拉罕·琼寇在开普敦郊区弗瑞德霍克的家。碧翠丝和安娜·琼寇首先在邻居J.A史密斯的家里找到了避难所。然后,母女俩去了比阿特丽斯父母的农场,“斯沃特·费尼”和安娜·西里尔斯。
根据路易丝·维尔约恩的说法,“一封信幸存下来,比阿特丽斯坚决拒绝亚伯拉罕关于她回到他身边的请求。”
英格丽德和安娜的童年是在他们祖父拥有的一系列小农场中度过的。
英格丽德后来写道,“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的祖父范尼·西里尔斯(Fanie Cilliers)是一位顶级的笑话讲述者,瘫痪并卧床15年,但我所知道的最机智的人以他自己丰富的方式统治着这个家。”
安娜·琼寇后来写了《斯沃特·范尼》,“他已经瘫痪多年,在最后一年里,他完全卧床不起。但是在那里,在他的大卧室里,门通向阳台,他招待他的朋友,直到烟斗里的烟在空气中变蓝。响亮的笑声、恶作剧、故事吸引了我们这些孩子;英格丽德会爬到欧帕的背后,当故事变得太糟糕时,欧玛会从那里来接她。”
安娜进一步回忆道,“英格丽德一直是欧玛的孩子。欧玛·安妮·雷蒂夫,来自帕尔的漂亮的安妮,一个纤细的女人,绿色的眼睛经常闪闪发光,但有时看起来很严厉。”
琼寇的祖父母搬到了杜尔班维尔附近的一个农场。
安娜后来回忆说,“我想,英格丽德是在德班维尔受洗的。她才三四岁,家人对此感到不安,就像她被起了一个不寻常的名字一样。妈妈在一本书上读到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就像她常说的。这家人常说,妈妈总是与众不同,谁会让一个孩子在花园里受洗呢?英格丽德穿着一件漂亮的白色连衣裙,那里有蛋糕、茶和许多人。我嫉妒得躲在邻居的花园里,隔着栅栏看着这一切。”
年轻时,英格丽德和安娜经常被带去看望祖母富有的亲戚,他们在帕尔拥有葡萄园。安娜后来回忆说,“我们经常去帕尔看望家人。我们认识的最老的人是欧玛的母亲和姑姑,他们住在帕尔的希尔赛德。我们被宏伟的房子淹没了,对我们的清洁程度也感到吃惊。对我们来说,这就像我们每天要洗手100次,只是为了得到一些美味的食物或者最多两三块漂亮的小饼干。曾祖母认为女孩应该是小淑女。我们交叉着小脚踝坐在pouffres上,尽量不去嘲笑这个座位的滑稽名字,而他们则庄严地开始建立家庭纽带。”
安娜还回忆起她的父亲,“亚伯拉罕来德班维尔看我们,但看到他让我母亲非常难过,以至于欧帕说他必须离开。”
在同一次访问中,亚伯拉罕给英格丽德带了一顶红帽子作为礼物,但拒绝承认她的存在。安娜说,“然后流言开始在斯泰伦博斯。英格丽德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英格丽德后来写道:“我记得的那栋房子是在德班维尔的,我们一直住到我五岁左右。我将永远记得,我笑着的祖父是如何鼓励我骑三轮车越骑越快,直到我摔倒——我的祖母会过来让我们冷静下来。哦,费妮,我对你的活泼无能为力吗?看看你是如何怂恿孩子的。她已经像个小恶魔了。”
1938年,她的祖父Fanie Cilliers去世,留下四名妇女一贫如洗。英格丽后来回忆说,“后来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我姐姐来找我说,‘你知道吗?欧帕死了。他的房间里摆满了花环。几年后,我从欧玛那里听说了他的死讯:“巴布斯”(那是我的昵称)‘你祖父去世的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床边说,‘安妮,我爱你,因为你背负了我的负担。"
事后,这家人搬到了斯特兰德。英格丽德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里,斯特兰德只不过是一个渔村。现在我不得不去教堂和主日学校。我没花多长时间就记住了最好的赞美诗。对我来说,这些歌曲包含了诗歌的结构、节奏和神秘。受此启发,在祖母的关爱下,我开始写诗。我的第一首‘诗’出现在校刊上。那时我六岁。欧玛向住在斯特兰德郊区的有色人种社区背诵这些经文,她过去常常在周日放学后去那里教他们圣经课。我仍然记得牵着欧玛的手走在那条长长的土路上是多么艰难,一路上她讲着笑话,当她低头看着我时,她深绿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微光。她自己不可能超过五英尺高。在有色人种社区面前,我会站在她布道坛的一边,当一首又一首激动人心的赞美诗被唱出来时,欧玛、我和全体会众都会以泪洗面。”
安娜后来回忆说,“英格丽德和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多穷。我们知道欧玛必须小心用钱,她的两个儿子,斯泰伦博斯大学的A.C西里尔斯和来自博克堡的律师雅各布叔叔每个月都给她寄钱。我父亲每个月也寄几英镑,后来欧玛拿到了养老金——我记得是一个月十七英镑。妈妈经常很累,长时间躺在床上,但有几次她一次去工作几个月。有一次她在南非广播公司工作,我们取笑她,因为她非常喜欢吉迪恩·罗斯。”
他们后来搬到了戈登湾。1940年,英格丽开始上幼儿园。
根据维尔约恩的说法,“他们的母亲和祖母给了他们比平时更大的自由和行动自由。在戈登湾逗留期间,他们经常在去学校的路上漫步到一片松林里,坐着看书。有一次,他们离开学校太久了,以至于他们的老师认为这家人又搬家了。在这里,他们也被允许饲养小动物,并继续探索草原和海滩。他们从草原上的植物中摘水果,从岩石池塘中收集贝类,在他们房子后面的小溪中与蝌蚪玩耍,并将被称为“秘密”的小物体埋在地下。毫不奇怪,戈登湾是后来在英格丽德的诗歌中获得象征意义的空间之一。”
安娜后来回忆道:“英格丽德和我在地毯上玩耍,妈妈和欧玛在看着我们。英格丽德抬起头,我听到妈妈说,“他怎么能说她不是他的孩子呢?她眼里有着同样心碎的表情。英格丽德大约六七岁。她从未忘记那些话;从来没谈过这件事,但她一定已经开始意识到为什么她是欧玛心痛的孩子。许多年后,在她的精神崩溃期间,精神病医生确定她在情感上只有7岁”
英格丽德母亲日益严重的精神疾病给这段田园诗般的时光蒙上了阴影。当他们住在戈登湾的公寓里时,比阿特丽斯·琼寇精神崩溃了。
安娜后来回忆起她的母亲,“她继续爱着爸爸,从未说过他的坏话,但她不想见到他。有一次,我们在窗口发现了她,她拉着一根绳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翁瑞迪来了”。“翁瑞迪来了。”她被带到瓦尔肯伯格,接受了睡眠疗法。妈妈突然不在的那天,我对英格丽德唯一的记忆就是她那双巨大而惊恐的眼睛。但和往常一样,英格丽德什么也没说,一切都转向了内心。”
这次经历的创伤深深地影响了英格丽德,并加强了她与祖母的联系,祖母是她唯一可以与之交谈的人。
精神崩溃后不久,碧翠丝·琼寇也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安娜后来回忆说,“她想加入战争,她必须先去看医生。那天晚上,她痛哭流涕,欧玛也是。然后妈妈做了一件让欧玛很不高兴的事,但是她不能也不会停下来。妈妈去看天主教神父,经常去他们那里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宗教。英格丽德害怕她会像所有罗马天主教徒一样下地狱。英格丽德和欧玛祈祷并朗读了《圣经》中关于《红字》的内容
在英格丽德弥留之际,她和安娜尽可能多地去看望母亲。他们经常与她分享关于男孩的消息,他们觉得无法与他们虔诚的祖母讨论。比阿特丽斯·琼寇在医院住了两年后,于1944年8月6日死于癌症。
英格丽德后来写道:“我的默德,斯特温德,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热情,如此的热情,如此的热情。”(我母亲,快死了,阳光如瓢虫,充满秘密,令人惊讶,如此温柔。”
安娜·琼寇后来回忆说:“我们四个人,欧玛,叔叔,英格丽德和我,埋葬了妈妈。当时正在下雨
安娜·琼寇后来回忆说:“我们四个人,欧玛,叔叔,英格丽德和我,埋葬了妈妈。天下着雨,还有其他一些穿黑衣服的人,欧玛说他们是殡仪员。”
根据路易丝·维尔约恩的说法,“比阿特丽斯的死结束了英格丽德在母系家庭中的生活。”安娜·琼寇后来写道:“欧玛会照顾我们,直到1944年底爸爸来接我们。对我们来说,他完全是个陌生人。在他到达之前,他让人问我们是否需要什么,我们写了《圣经》。英格丽德真的很想要一本《圣经》,那本《圣经》和她小时候的陀螺是她童年时从爸爸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在他来接我们之前不久,我偷偷写信说我们不能去,因为我们应该和欧玛呆在一起,去霍顿托荷兰或别的地方上学,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漂亮的衣服穿在斗篷上。”
然而,正如安娜所写,“他在1944年底来到这里。我们上了车,英格丽德透过开着的窗户不肯放开欧玛的手。她坐在后面,一直看着欧玛在路边的小黑人。这条路是要穿过我们继母冰冷的房子里的灰色少年岁月,穿过英格丽德成年生活的幻灭。”
在母亲去世之前,安娜和英格丽德与父亲的联系一直很少。在与比阿特丽斯离婚后的几年里,亚伯拉罕·琼寇曾短暂地再婚,第三次婚姻是在1941年与儿童书籍作者露露·布鲁伊斯结婚前。
路路所生的亚伯拉罕的儿子阿道夫·雅各布斯“库斯”琼寇回忆道,“我母亲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她嫁给我父亲时,是个四十一岁的老处女。她和一个朋友一起教了几年书——他们一起去了英国。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新朋友,他和他们一起来到了南非。她不喜欢孩子——我母亲也有类似的强烈倾向。所以我们一直有白人家庭教师。”
库斯·琼寇进一步回忆道,“1944年,当我父亲去接安娜和英格丽德时,隆德博施的房子对全家人来说变得太小了。他们和人住了一段时间……”
安娜解释道:“城市生活并没有那么艰难。我们在坦伯尔斯克洛夫寄宿了几个月,并在赞·范里贝克学校上学。英格丽德上小学,我上高中。
从他们的寄宿处,琼寇女孩可以走到他们的学校,学校坐落在桌山的斜坡上。
每个星期天,亚伯拉罕·琼寇都会从寄宿处接他的女儿,带她们和他、她们的继母露露以及她们年幼的哥哥库斯一起度过一天。有时,露露会和她的丈夫和继女一起晚上开车回坦博尔斯克洛夫。开车时,安娜和英格丽德会靠在露露身上,露露会给他们讲故事。
安娜后来回忆道,“我们很高兴她喜欢我们,我们也很乐意接受她作为母亲。我们不想叫她妈妈,但决定万可儿,她理解我们的态度。”然而,六个月后,亚伯拉罕在普卢斯泰德买了一栋更大的房子,他的女儿们永久地和他住在一起。
几乎立刻,安娜和英格丽德与露露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安娜·琼寇后来回忆说,“露露的母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有非常重要的客人要来吃饭,英格丽德和我应该在厨房吃饭。我们不介意,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和成年人谈论政治。我们很高兴和小家伙们一起在厨房吃饭,他们当时还是婴儿。但后来她走上楼梯说,‘我们觉得——我们觉得——你是在后街长大的。你会让你父亲在餐桌上蒙羞的,”欧玛一直活到英格丽德结婚前,但我们很少见到她。例如,在我们去开普敦居住后不久,她就来普卢斯泰德的大房子拜访我们。但是,就在我们去接欧玛的前一天晚上,我的继母说不行,我们不能去接她,因为她的妈妈也要来开普敦,餐桌上没有足够的空间了!”
Huibrecht Steenkamp夫人后来回忆说,“我很快就发现露露正是我所期望的那种后妈。他们完全被剥夺了,那两个孩子——英格丽德和安娜。他们的父亲当时正忙于政治。他是国会议员,经常不在家。他真的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
根据路易丝·维尔约恩的说法,“虽然亚伯拉罕·琼寇在那些了解他和他女儿之间存在的政治紧张局势的人的心目中被描绘成典型的种族隔离政治家,但他的政治生涯是曲折的
然而,在其他时候,亚伯拉罕·琼寇是他妻子虐待继女的同谋。安娜后来回忆说,“他们坐在桌子的最前面,我们坐在最下面,盐的下面。当他们有一条羊腿时,我们吃老鼠。他们有水果,但我们没有。他们有糖果,但我们不被允许。他们会去参加周日的驾驶活动,但那辆巨大的汽车里没有我们两个的空间。”
斯廷坎普夫人继续说道,“露露只不过是一个不断谴责孩子们的法官。那些孩子非常脆弱——与其说是安娜,不如说她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但英格丽德是完全脆弱的。原因是她知道安娜是最受欢迎的。”
安娜和英格丽德都习惯于独自徘徊,总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据他们继母的朋友埃纳·德克勒克夫人说,“露露想把他们留在家里,保护他们,把他们塑造成一个宗教形象。这导致了她和女孩之间的冲突。与其说她对他们不公平,不如说露露·灯盏花本来就是个好人。安娜和英格丽德是流浪者,他们从小就在海滩上漫游。他们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
然而,据斯廷坎普夫人说,“这就是那些人对孩子们的态度。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被抚养得非常好!他们的母亲抚养他们,她来自帕尔最好的家庭之一!他们怎么能说孩子们是在后街长大的呢?”
英格丽德和安娜住在普卢斯泰德时,在温伯格女子高中上学,那里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而不是南非荷兰语。学校记录显示,英格丽德是一个行为端正但很普通的学生,她更喜欢只专注于自己喜欢的科目。她的作品受到老师们的称赞,她开始为学校杂志写诗。
根据路易丝·维尔约恩的说法,“虽然这两个女孩和她们的继母之间没有失去爱情,但他们和更年轻的继兄弟姐妹库斯和苏珊娜关系很好。
到1951年,英格丽德想搬出去。安娜后来回忆起她是如何从当时工作的约翰内斯堡出发,去帮助英格丽德获得离开普卢斯泰德房子的许可的。在两个女孩都解释说“房子里有空间,但心里没有位置”后,亚伯拉罕·琼寇同意英格丽德搬出去。安娜随后帮她在开普敦市中心的一家寄宿公寓安顿下来
英格丽·琼寇六岁时开始写诗,到十六岁时,她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夏天过后》交给了国家诗社。出版商没有接受,但公司的读者D.J .奥佩尔曼邀请英格丽德来和他讨论她的诗。奥佩尔曼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南非文学中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因此,英格丽德第一次去看他时感到非常害怕。然而,令她振奋的是,奥佩尔曼既认真对待她,又给了她很好的建议。在1951年的两个场合,她再次给他寄去了一些诗歌,对此奥佩尔曼都发表了评论,并敦促她多寄一些。
根据路易丝·维尔约恩的说法,“其中一些诗歌(例如斯克里克和凯斯)含蓄地暗示了浪漫的渴望和觉醒的性欲,这往往是由宗教负罪感主导的。很难在这些诗歌的基础上重建青少年英格丽德的内心生活,因为其中的情感表达仍然受到女学生的礼仪和前一代南非白人诗人的书面修辞的保护和限制。”
英格丽德的许多密友后来都会评论她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事实。一些人把这归咎于她的父亲,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她的继母露露·琼寇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她离开父亲的房子后,亚伯拉罕·琼寇支付了英格丽德参加秘书课程的费用,这使她能够养活自己并独立。
然而,英格丽德真正热爱的是她作为诗人的职业。她后来回忆说,“我成了一名上班族,但我活着的真正目的是写作。”
她继续向流行杂志如Die Huisgenoot、Naweekpos和Rooi Rose以及文学杂志Standpunte发送诗歌。随着她这样做,她的诗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优美。她还学习雕刻、演讲和表演。
根据路易丝·维尔约恩的说法,“当人们听她朗读自己诗歌的录音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清晰的措辞和发音,这并不奇怪。她的声音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的声音,平静而自信。虽然她给人的印象是脆弱和无助,但她的性格中一定也有一定程度的韧性和决心,使她能够克服早年的贫困,在离开父亲的家后在艺术和社会方面得到发展。”****
她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逃离》最终在1956年出版。
持不同政见者
她的父亲已经是一名作家、编辑和国会国家党成员,被任命为负责艺术、出版物和娱乐审查法律的议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令亚伯拉罕·琼寇尴尬的是,他的女儿强烈反对他负责实施的审查法律,他们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了。他在议会发表演讲,否认她是他的女儿。
1961年,因父亲拒绝她和堕胎导致的抑郁迫使英格丽德进入瓦尔肯伯格精神病院。
琼寇的下一部诗集《烟雾与赭石》在出版商的拖延下于1963年出版。虽然这本选集受到了大多数南非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的称赞,但它受到了执政党支持者的冷遇。
此后,英格丽·琼寇被称为“死色虎”(Die Sestigers)组织之一,该组织还包括布雷顿·布雷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亚当·斯莫尔(Adam Small)和巴托·斯密特(Bartho Smit),他们挑战执政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的极端南非白人民族主义。
卢克·奥克获得了琼寇1000南非荷兰语奖(南非荷兰语出版社-书商)文学奖,以及英美公司的奖学金。这笔钱帮助她实现了去欧洲旅行的梦想,她去了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她请杰克·科普陪她,但他拒绝了。琼寇随后邀请安德烈·布林克加入她。他接受了,他们一起去了巴黎和巴塞罗那。在旅途中,布林克决定不离开妻子去琼寇,而是回到了南非。然后,琼寇缩短了行程,回到了开普敦。
琼寇在去世前开始写新的诗集。这些诗歌的选集在康德尔森的文集(《倾覆的太阳》)中死后出版。然后,她目睹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一名黑人婴儿被白人士兵射杀,死在母亲的怀里。她在狄兰·马尔莱斯·托马斯强调:“在第一次死亡之后,就没有其他人了”。她写了《善良的孩子》(wat doodgeskiet是尼扬加的士兵打死的)(《孩子》(在尼扬加被士兵开枪打死))。
个人生活
英格丽·琼寇于1956年与彼得·文特尔结婚,他们的女儿
1965年7月19日晚上,英格丽·琼寇去了开普敦三锚湾的海滩,走进海里,溺水自杀。英格丽德去世的消息震惊了那些认识她的人。杰克·科普和尤斯·克里格被要求辨认尸体。事后,柯普在日记中写道:“亲爱的,我辜负了你。只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缺乏信念,失去勇气,比自己的爱还小——我爱你一百万次。”安娜·琼寇后来回忆说,“那天早上我去见杰克时,他正坐在一张桌子旁,周围都是其他作家的朋友,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们都怪他。”安德烈·布林克当时在比勒陀利亚,听到这个消息后震惊得失明了几个小时。
根据马乔里·华莱士的说法,“英格丽死的时候,亚伯拉罕·琼寇正在打猎。当他最终被找到时,他说,“就我而言,他们可以把她扔回海里。”
然而,英格丽德的同父异母兄弟库斯·琼寇坚持认为这是不真实的。根据库斯的说法,“据报道,我父亲听到英格丽德的死讯时,说了一些无情的话。但与此同时,我正和他一起在东开普郡打猎,我站在他旁边,这时农夫的儿子来了,告诉我们英格丽德淹死了。我父亲非常震惊。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说我们应该马上离开。在那个阶段,他和英格丽德的关系很好。她经常去圣詹姆斯拜访他。”
西蒙妮被飞机送到约翰内斯堡她的父亲和继母那里,直到她到达后才得知母亲的死讯。心理学家范德梅尔韦写道,“在她去世前不久,她在狄兰·马尔莱斯·托马斯的一句诗下面划了线,‘在第一次死亡之后,就没有其他人了’...因此,她确认告别发生在1965年7月19日之前。但是那天早上发生的身体上的行为使得很难保持正确的观点,来判断她的影响力的价值,因为在那一天一个传奇诞生了。”
劳伦斯·凡·德·普司特后来谈到英格丽德时说:“她自杀对我来说几乎就像是南非白人的自杀...她被她的父亲,她的人民和她的爱人拒绝了,甚至于她自己也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中...我吓坏了...由于她童心未泯的危险,我给杰克·科普写了封信,恳求他到欧洲来接她,并提出支付车费...但是一旦杰克拥有了她,他只是给了她他冰冷心灵的碎片作为回报。他是唯一一个...谁能救她。也许他试过,我不知道。我可能不公平...她需要一颗充满爱心和理解的人类之心来接纳我们,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中的一些人感谢上帝。”
英格丽德的放荡不羁的朋友们最初为她计划了一个世俗的葬礼,在葬礼上她要大声朗读她的诗。亚伯拉罕·琼寇被这个想法激怒了,他否决了他们,并控制了这些安排。据报纸报道,亚伯拉罕决心不让他女儿的葬礼成为抗议政权的场所。当它发生在1965年7月22日时,没有教堂服务,但荷兰改革宗牧师,牧师J.L .范·罗延,在墓旁主持仪式。英格丽德的妹妹安娜抵制了葬礼,以抗议对安排的改变。在葬礼上,哀悼者分成了两派。一方面是琼寇一家,他们的朋友,和一群特别分支侦探。另一边是英格丽德的朋友,他们来自开普敦的文学波西米亚。
据马乔里·华莱士说,露露·琼寇找到她继女的朋友,告诉他们,如果英格丽德的任何一首诗被大声朗读,那些被禁止的人将被逮捕,因为这将把葬礼变成一场政治集会。杰克·科普无法控制地抽泣着,当棺材被放入地下时,他不得不阻止自己向棺材扑去。琼寇一家离开后,英格丽德的朋友们把花扔进了坟墓。科普扔进了他在克利夫顿上方的斜坡上摘下的野生橄榄花环。
安德烈·布林克选择不参加葬礼,因为他觉得这将把本应是私人事件的事情变成公开的场面。
在她宗教葬礼后的讨论之后,英格丽德的朋友们于1965年7月25日为她举行了世俗葬礼。在一百多名哀悼者面前,尤斯·克里格谈到了英格丽德的诗歌,简·拉比大声朗读了她的一些诗歌。这一次,英格丽德的妹妹安娜出席了。里维尔森德兰的高中老师简·勒·鲁希望带着他的学生参加葬礼,这些学生热爱英格丽德的诗歌。在被校长和当地的荷兰改革宗牧师拒绝后,学生们为英格丽·琼寇举行了私人祈祷仪式,在仪式上大声朗读了她的诗。女儿去世后,亚伯拉罕·琼寇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5年10月
女儿去世后,亚伯拉罕·琼寇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5年10月,他剥夺了女儿安娜的继承权,因为她拒绝将英格丽德写给安德烈·布林克的信交给他。
亚伯拉罕·琼寇也开始大量饮酒,尽管医生警告说这可能会杀死他。
安娜·琼寇后来回忆说,“他不被允许喝酒,而且几乎不清醒。英格丽德死后,他经历了地狱——他经历了绝对的地狱。那是圣诞节,他腿上有血栓...露露不想让我见他,你能相信吗?!但后来一名护士告诉我,亚伯拉罕在呼唤,“英格丽!“英格丽德,”他不停地叫她的名字。然后露露说了句什么,我爸爸狠狠地打了她一拳,她就直接飞过了病房!”
亚伯拉罕·琼寇于1966年1月10日死于主动脉动脉瘤,就在他女儿自杀六个月后。
库斯·琼寇死后,推翻了父亲的遗嘱。库斯确保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安娜得到了她原本应该得到的遗产,以及他们父亲的小提琴和额外的经济支持。
然而,库斯·琼寇说,“有时我想知道一个看起来如此‘糟糕’的人怎么会四次被选入议会。他不仅受到选民的尊敬,也受到公众的尊敬。我很荣幸有一个像亚伯拉罕·琼寇这样的父亲。”
多年后,西蒙·文特尔(Simone Venter)接受纪录片采访时,承认了母亲自杀造成的心理伤害。即便如此,西蒙妮说:“她想死。这是她深思过的事情。这是她的选择。”
遗产
版权和论文
琼寇死后,法院院长将她的文学遗产和论文的版权和控制权授予了杰克·科普。他建立了英格丽·琼寇信托基金。他在1991年去世前一直是该信托的受托人。琼寇的女儿西蒙·温特是受益人。版权仍归信托所有。
琼寇的文学论文被送到了位于格雷厄姆斯顿的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NELM)。她的姐姐安娜·琼寇借了这些,打算写一本关于她的姐姐的传记。2005年11月。
文学遗产
像莱顿墙上的诗一样亲切地死去
琼寇尔的诗歌已经从南非荷兰语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荷兰语、波兰语、印地语和祖鲁语等。她写了一部独幕剧《我的心肝后的儿子》,讲述了一位母亲对自己残疾儿子的幻想。Jonker还写过几个短篇小说。
享有盛誉的英格里德·琼寇奖是南非荷兰语或英语诗歌的最佳处女作,由她的朋友设立,以纪念她在1965年去世后留下的遗产。这个一年一度的奖项由1000兰特和一枚奖章组成,交替授予在过去两年中出版了第一卷的南非荷兰语或英语诗人。
1975年,南非白人诗人布雷顿·布雷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在巴黎的家中访问南非时被捕,并因叛国罪被判处9年监禁。1977年6月,布赖坦巴赫被起诉,他被指控通过阴谋“奥克拉组织”策划了苏联海军对罗本岛监狱的潜艇袭击。最后,法官只判他犯有将信件和诗歌偷运出监狱的罪行,为此他被罚款50美元。
在服刑期间,布莱滕巴赫写了这首诗《不忠情人的歌谣》。受弗朗索瓦·维隆(Franois Villon)的《节奏之歌》(Ballade des Dames du Temps Jadis)的启发,布赖登巴赫将彼得·布卢姆(Peter Blum)、英格丽·琼寇(Ingrid Jonker)和他自己比作不忠的恋人,他们因离开南非荷兰语诗歌而背叛了南非荷兰语诗歌。
1994年5月24日,在南非第一届民选议会开幕时,纳尔逊·曼德拉赞扬了琼寇尔作为种族隔离批评家的作用,并表示她的自杀是对一个拒绝听取她的国家的极端抗议。曼德拉接着读了琼寇的诗《死得其所》(wat doodgeskiet是由尼扬加(Nyanga)士兵杀死的) (孩子(在尼扬加被士兵枪杀))(英文译本)。
然而,诗人的朋友伊丽莎白·博塔反驳了曼德拉关于英格丽德自杀原因的说法,“她悲惨的死亡不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制度。事实上,她反对压制任何意识形态。在她去世之前,她有一种绝望的孤独感和纯粹人类层面的排斥。”
2001年,萨斯基亚·范·沙克(Saskia van Schaik)为荷兰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关于琼寇(Jonker)的纪录片:Korreltjie niks是我的最爱。
2002年,赖克·哈廷赫的互动剧《奥普拖:英格丽·琼寇》(《任务:英格丽·琼寇》)在佳娜·西里尔斯主演的格雷厄姆斯顿国家艺术节上演。该剧涉及对琼寇生活的问题和评论,与她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交织在一起。
2004年4月,琼寇因“对文学的杰出贡献和对南非人权和民主斗争的承诺”被南非政府追授为伊克曼加勋章
2007年,出生于莫桑比克的南非电影和纪录片导演海伦娜·诺盖拉的纪录片《英格丽·琼寇,她的生活和时间》在南非上映。被誉为琼寇的权威作品,这是第一部在南非上映的文学纪录片。
多年来,她的许多诗歌都被改编成了音乐,从斯特凡·格罗夫(1981)的《为女高音和钢琴而作的Vyf liedere》(1981年)开始,由劳里卡·劳奇(Laurika Rauch)、安妮莉·范·罗扬(Anneli van Rooyen)和克里斯·变色龙(Chris Chameleon)等艺术家演唱。
2003年,一个南非流行乐队ddisselblom发行了一张同名的CD,里面有一首《法肯堡》,这是一首改编自容克的《流浪》的非常好的歌曲。
2005年克里斯·变色龙(更出名的是南非乐队Boo的主唱!)发行了专辑《我重复你》(Ek Herhaal Jou),其中包含了琼寇创作的一些诗歌。该片上映恰逢琼寇逝世40周年。琼寇的一些诗歌启发了变色龙的歌曲,如比特贝西·达布里克(《比特贝瑞黎明》)、利得·范·迪·格布雷克特·里耶特(《破碎的芦苇之歌》)和翁特夫卢廷(《逃亡》)。
此外,2007年关于英格丽·琼寇的故事片《所有的突破》的工作已经开始。这部电影是根据在约翰内斯堡市场剧院工作的海伦娜·诺盖拉(Helena Nogueira)的剧本改编的,重点讲述了琼寇和塞西老虎三年来的生活,他们聚集在开普敦克利夫顿的诗人尤斯·克里格(Uys Krige)周围。这部电影由大卫·帕菲特(《莎翁情史》)、查尔斯·摩尔(《辛德勒的名单》)[需要澄清]和单穆德利制作,由诺盖拉执导。
2011年,荷兰女演员卡里斯·范·侯登在保·范·德·奥斯特执导的传记电影《黑蝴蝶》中扮演英格丽·琼寇。这部电影还由爱尔兰演员利亚姆·坎宁安扮演杰克·科普,鲁特格尔·哈尔扮演亚伯拉罕·琼寇。尽管《黑蝴蝶》完全是一部荷兰作品,讲述的是一位用南非荷兰语说话和写作的诗人,但它完全是用英语拍摄的。
同样在2011年,南非音乐家克里斯·变色龙发行了一张琼寇的作品专辑,名为《如果你再写一遍》。
2012年,尼古拉·哈斯金斯(Nicola Haskins)为格拉汉姆镇的国家艺术节(National艺术节)编排了一部讲述琼寇生活故事的舞剧,随后在包括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Pretoria)在内的多个场所进行了表演。
传记
琼寇的传记作者是彼得罗娜·梅特勒坎普,她在2003年出版了《英格丽·琼寇——诗人生活的写照》。这本书包含了对诗人生活的新见解,包括情书(一些没有寄出)和她朋友邦妮·大卫茨对琼寇死亡之夜尚未发表的描述。据说这本书的收益在经济上帮助了西蒙·文特尔(琼寇的女儿)。这本传记的英文更新版本出现在2012年:《英格丽·琼寇——诗人的一生》。
5 ) 诗人之死
南非女诗人英格丽琼蔻的一生可以说是大多数诗人一生的写照。极度渴望自由,向往纯真热烈的爱情,向一切规则与道德挑战,她父亲说她“你一向为所欲为”。与其说她是一个反种族主义诗人,还不如说她是一个彻底的诗人。她的那首荡气回肠的《尼昂加死去的孩子》,也并不是在为政治摇旗呐喊,而是源于内心深处对自由与希望的深深渴望。
她的死,是一种宿命,诗人很容易对这个世界绝望,其实是对他们梦想中大海般深邃的世界绝望,这是命中注定的。世界肤浅冷酷的运转着,从来不会真正被华美丰盈的诗句所震撼而有丝毫改变。
每一个诗人的死,都是这个世界上一朵花儿的凋零,一颗星辰的陨落。
很喜欢她的一句诗是,我想你多过日升日落。是她拥抱久别的小女儿时说的。她的诗句很多极富冲击力,狂风骤雨般的让人无法呼吸,但这句却让我触及了她的灵魂,她的灵魂是一首关于爱与梦的诗,不属于现实世界。
6 ) 《黑蝶漫舞》:身陷灣流的女詩人
荷蘭導演寶拉凡德奧斯特(Paula van der Oest)的最新電影《黑蝶漫舞》,便以英格麗堪稱傳奇色彩濃厚的一生為題材,除了以同為女性創作者的身分,細膩地傳達出英格麗的情感波折和衝突,也展現出英格麗在面對男性代表的強權時,強勢和柔弱兩面一體並存的矛盾,以及身為女性所面臨的困境。
對父親/強權的反抗
由於父母離異,孩提時期的英格麗(Carice van Houten飾)跟著姊姊安娜(Candice D'Arcy飾)和母親一同生活,直到母親過世,兩姊妹才由父親(Rutger Hauer飾)接回扶養。或許是出於這層因素,英格麗和父親的關係總是若即若離,游移於親密和疏遠之間。然而,即便兩人的關係不甚和睦,英格麗仍三番兩次親近父親,分享自己的詩作,希冀能讓父親肯定自己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只是,換來的往往是父親的冷漠和嘲諷。英格麗向父親說:「文字就代表了我。」掌握創造之筆的英格麗藉由詩作試圖拼湊出屬於女性的自我,但是,從她將詩作給父親過目、企盼換來讚賞的行為來看,英格麗的自我似乎仍需父親,也就是男性的肯定。另一方面,對父親而言,英格麗的自我是不存在,也不允許其存在,因此父親才會不斷地否定英格麗,不但對她說:「妳就是妳的母親。」還當面撕掉她的詩作,甚至辱罵她「爛貨」。此外,當英格麗的言論受到媒體注意時(顯示出英格麗逐漸成為一位有發言權的獨立之人),父親便以「媒體是因為我才對妳有興趣」企圖抓回男性的掌控權。也許,在父親(男性)的眼中,英格麗只能是他的女兒(女性),充其量不過是附屬物罷了。
英格麗的父親在片中不僅代表父權,任職於政府審查部門,負責查禁「內容不適宜」的文藝作品的父親,同時也象徵政府強權。想當然耳,父親查禁的魔爪也伸到英格麗的作家友人身上。起先是黑人作家尼可西(Thamsanqua Mbongo飾)的作品遭查禁,英格麗和小說家傑克考普(Liam Cunningham飾)想盡辦法協助他逃往國外;接著,劇作家艾斯(Graham Clarke飾)的新戲也以泛政治的理由被查禁,英格麗還因此和父親起爭執;最後,連英格麗的詩作也差點遭遇查禁的命運,是父親考量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名聲才放過她一馬。從這個層面來看,英格麗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其實可以看作人民對政府強權的反抗。
此外,在種族歧視問題嚴重,甚至一度施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白人普遍擁有優越感,英格麗的父親即如此。英格麗的父親認為「黑人普遍智能低下」,對家中的黑人女傭也總流露出輕蔑的眼神,也不讓家人與她們多加交談。然而,並非所有白人都像英格麗的父親一樣,對黑人百般歧視。如同前述,英格麗不僅幫助黑人作家友人逃亡,還在公車上為黑人出頭,與司機吵了起來;當她親眼目睹白人警察開槍射殺黑人時,大為震撼,反覆低語著:「那孩子還沒死……」並寫成詩作〈一個在加彭被士兵射殺的孩子〉(The child who was shot dead by soldiers in Nyanga),這正是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1918-)在就職典禮所朗誦的詩作。
在片中,英格麗的父親不單單是象徵男性文化的父權,還有政府、白人的強權,可說是綜合三種強權於一身的角色。因此,英格麗對父親的抵抗其實大可視為她對強權的反抗,正如電影開場時英格麗朗誦的詩句「對體制的麻木」所示,主流體制構築而成的強權並非她所畏懼的,無怪乎曼德拉前總統會如此讚揚她。
以我的乳臨摹你的掌
在握有創作之筆的男性眼中,女性頂多是附庸,是創作靈感的來源。然而,英格麗完全翻轉此一規則,縱使她沒有男性之筆──陽具──她仍以女性第二性徵之一的乳房當作女性之筆,男性和性愛便成為她的創作養分。在和傑克的一次性愛之後,英格麗寫下詩句:「以我的乳臨摹你的掌。」不僅顛覆男性在愛撫、性愛裡的主導位置,化被動(被撫摸)為主動(撫摸),更進一步暗指女性成為創作的主體,而男性則轉為被書寫的客體。
英格麗藉由文字細膩地記錄著自己的情感,試圖從中回歸女性自我(雖然從某個角度來說,她的自我仍需父親,也就是男性的肯定),不僅如此,她的筆觸還延伸到社會關懷,為遭遇不公的弱勢族群(被白人歧視的黑人)發聲。基本上來說,身為詩人的英格麗善用語言展現自己在創作上的無限潛能,也藉此從男性的權力架構下找到情緒和欲望宣洩的出口。
那麼,在愛情中的英格麗呢?是否同樣獨立自主?當差點溺水的英格麗被傑克救起後,向他說:「為我寫首詩,我會回敬你一首。」主動為兩人牽起日後相見的橋樑。當然,先寫詩送對方的人是英格麗。育有一女、和丈夫關係不甚良好的英格麗,率先拿起筆寫詩給傑克,完全拋開世俗或父親的眼光,勇敢表達真實情感。往後兩人的互動和性愛,也幾乎是由英格麗引導,例如:英格麗裸身走向傑克,從後方環抱他,主動且毫不保留地展現自己的欲望。然而,英格麗還是擁有依賴男人的柔弱面相:英格麗多次要求傑克娶她,渴望共組家庭,過上安定的生活;當傑克要離開一陣子時,英格麗為了送行而辭職,即便最後只能淚眼望著傑克的離去,仍流露出為愛瘋狂的一面,以及對傑克的深深依賴。
身陷灣流的女詩人
電影的後半段,英格麗逐漸走向瘋狂、崩潰,以至於最終自我毀滅於波濤洶湧的大海中,會招致這樣的結果,我想是英格麗內心的矛盾帶來的困境所導致。英格麗在追求自主、自由意志的同時,仍受限於男性引領的社會和傳統之下,讓她亟欲得到父親的肯定和讚賞,並將自己的情感寄託於無解的戀情和不曾出現的溫馨家庭上。兩相衝突之下,讓英格麗如身陷強勁灣流般難以掙脫,折磨得她再也寫不出任何東西,也無法再愛。死亡,對英格麗來說,或許是唯一美好的結局。
同樣身為女性的寶拉凡德奧斯特導演,用細膩且充滿詩意的畫面勾勒出英格麗的多舛人生,在呈現英格麗勇於求愛、展現自我的同時,更加深她內心所蒙受的巨大苦痛,讓觀眾也能深切地感同身受。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導演在片尾以曼德拉前總統的就職演說作結,似乎在為英格麗的悲劇人生補上一個美麗句點。但是,怎麼美也比不上英格麗留下的文字,那才是真正由人生淬鍊出的美麗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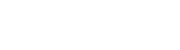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荷兰
海滩很美
别说,说出即错。
整体构思不错,但是不够硬
诗歌,女权,人性,南非。
因为看过黑皮书而喜欢上了Carice van Houten所以选择看了黑蝶漫舞,对于女主勇于对抗体制的那种个性而敬仰,也对坎坷的感情路而揪心,歇斯底里的她也逃脱不了精神的枷锁!
看完心里很难受。
一个女诗人的爱情和命运。她明显的具有艺术家人格特质,贫穷坎坷的童年,一个冷漠父亲,一生靠近却永远没有结果……电影一开场就吸引人,爱她的神经质,她的才华,她的个性……她内心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当杰克出现的时候,一个梦幻场景出现了,所以她的情诗那么温柔
燃烧
虽然不是我喜欢的路子,但是也蛮有意思。没有被摧折的生命,也就没有诗。
条目之前所有的信息都是错的,我第一个看过于是就修改了。《黑皮书》女主角Carice van Houten在这部电影里再次出色演出。讲述了南非女诗人Ingrid Jonker传奇的对抗南非种族隔离不屈一生。电影总体来说相对沉稳,只是感情处理还不够细腻,稍显冗长,总体3.5星。
Carice van Houten出演这种情欲澎湃、至情至性、自由豪放、歇斯底里的独立女性角色已经成了拿手好戏了,让人很满意却也找不到意外的惊喜。一辈子遇人不淑,遭遇两个情人的背叛和父亲的不认同,万念俱灰之际选择了自杀。又是一个女人的独角戏!★★★☆
Ingrid Jonker:“所有心碎、沉淪与凋敝,一如射出的精液,除了辜負,别無他义;物有本末,事有始終,就像人生,始于子宫。所有成就莫過于以墓為終。”…
The child is not dead
为爱痴狂
女主真是大爱啊
英格曼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幸是杰作的源泉。
劇情失重,到底想講INGRID的感情還是種族議題?而且也感受不出INGRID哪裡偉大優秀。最後曼德拉的朗誦感覺只是為了加而加。
现在的女导演都流行拍片很用力嘛......整体属于不失不过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