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剧情介绍
高肖梅《跑道終點與不敢跟你講:不該被遺忘的兩部影片和一個導演--牟敦芾》搞定女神的N种魔法神的骰子暗潮汹涌2000给爸爸的信(国语版)波纹2023韩战:不曾结束的战争北京女子图鉴疯囚长夜43栋的女人们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夜疯狂万人迷(国语版)合理怀疑 第二季格杀令(普通话版)老爷车大翻新第三季闪灵特工队异世浮生张学良将军热恋中的他南拳北腿斗金狐布鲁纳瑟非斯丁卓越航空新闻播音员第二季拾芳情妇2023血脉之树有其父必有其子人鱼恋爱法则第一季生辰八字2009火星救援占领区第二季飓风营救3独活女子的推荐 第三季影后风云死神傻了情牵你我她第一季甜水谣人鱼之海牢物怪苦月亮神探南茜第四季超级吉普赛流氓沉默的证明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 第四季
长篇影评
1 ) 魔幻的死亡感《跑道终点》
除了反抗意识,《跑道终点》最打动我的原因,莫过于牟敦芾以当时华语电影前所未见的电影感,去刻划满腔愤怒和反抗意识的原点。原来那出自脆弱敏感的孤独,是一种接近漫威宇宙的大魔王完成自以为的宇宙大业之后,却莫名陷入沉思的孤独。 牟敦芾非常擅长藉由诗意感性的图像构图,去传达这样的孤独感。例如在《不敢跟你讲》片头打出演职员名单时,主人翁大原侧坐,那个由他身体去分隔草原和天空的远景镜头,便暗示了这个男孩的渺小与孤寂,以景喻情的功力令人难以忘怀。《跑道终点》也出现许多将人与自然巧妙合一的完美远景,比方以俯角拍摄操场跑道,跑道上的永胜在银幕上只有丁点大,椭圆形跑道那种无路可出的循环意象,于是在对比之下显得更为巨大,定调了此角的悲剧结局
2 ) 半世紀以前的出櫃宣言——破解《跑道終點》遺留的牟敦芾密碼
全文請見://bit.ly/3fIHj1G
■ 異口同聲的大師經典,眾說紛紜的「同性戀」
與後起之秀新浪潮電影對照,聽過《跑道終點》的觀眾之少,與電影展現的高超水準完全不成比例。這部本該成為影癡們耳熟能詳的劃時代經典,竟在冰庫度過沒沒無名的五十年,直到 2018 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才重見天日。或因如此,深藏於本片的密碼,至今仍未被完全破解,值得我們重新發現──
人物設定乍看老派。體育好、家境不好的李永勝,碰上數學好、家境好的姜小彤。小等一下,為免「小彤」二字可能無法建立起與男孩的直覺關聯,我以下稱那位愛跑步的男孩「永勝」,擅長珠心算的則容我改叫他一句「彤弟」。
影展手冊的劇情簡介這麼寫:彤弟與永勝兩人鎮日玩鬧在一起,形影不離。而永勝在練跑時意外猝死,讓在場的彤弟悲痛自責,雙方家人的不諒解以及失去摯友的孤寂,迫使他走入黑暗。
關於永勝與彤弟的關係,說他們是彼此的摯友,我想看過電影的都會同意。但「兄弟情義」是否有更進一步的「異男忘」或「同性情慾」,大家的詮釋多少有差異。
影評鄭秉泓在一本書叫《看得見的記憶》盛讚本片,通篇卻微妙地隻字未提「同性戀」。參與本片演出的資深演員劉引商,時隔五十年後有機會看見本片也說,裡面不過是非常單純的男孩子玩在一起,哪有什麼人家說的「同性戀」。
刻意迴避,多少是為了回應江湖謠言。坊間傳聞,本片 1970 年被禁演,是因為裡面出現「同性戀」。電影前三分之一的一場關鍵戲,彤弟對著永勝喊──「林小華說我們是『同性戀』。」──就只這麼一句,讓許多人積極肯定這部電影,突破我們以為戒嚴時期同性戀絕不會出現在大銀幕的禁忌,認為是台灣電影少數勇敢闖進同志爭議議題的先驅。
如果這就是《跑道終點》全部的重要性,那也難以激起我力推它的動力。畢竟以「否認」同性戀來「處理」同性戀的電影,古今中外遍地:1961 年的美國片《雙姝怨》,略刪幾句,就順利通過審查在台上映;台灣導演李美彌 1980 年的《女子學校》,也比《孽子》更早被人指認出,有以「姊妹情誼」或偷渡或消音的「同性戀」。
這都不足以形容《跑道終點》。我要說,正是因為導演與編劇嫻熟包裝與曖昧,才讓冰在片庫數十年的這部片,成功守住導演的秘密,卻也埋沒其超越時代的意義。
只要各位轉變觀念,回頭捕捉電影裡一個個小細節,我們最後會發現,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導演拍出這麼一部「出櫃」宣言,一場至今仍令人瞠目結舌的藝術實踐。
《跑道終點》是我所見過處理得最早也最深刻,對白與故事鋪陳皆令人驚艷的台灣同志片。本片已可見許多台灣同志文學的原型,更有滿到溢出來的心酸與浪漫場面。讓我們從最直接可見的「同性戀」開始,一起細讀導演如何趁這三字光明正大出現時的七句台詞,埋下各種「說」與「不說」的曖昧,只待有緣人細心品味。
■ 啃口你的臉,讓你變成同性戀
彤弟與永勝一日決定比賽:看是你的珠算算得快,還是我的飛毛腿厲害。這是一場快手與快腳,各要解決十題珠算與三千公尺的競賽。比賽開始,算珠算的彤弟找了個時間點,拋出那句:「林小華說我們是『同性戀』。」
永勝邊跑邊喊:「『同性戀』?什麼意思啊?」中文的多義,常讓人看字幕會錯意,除實際看片聽語氣,也可參考底下英文翻譯:What’s a Queer?永勝這句的語意顯然不是「林小華什麼意思啊他!」而是在問:「同性戀是什麼啊?」
一個短沉默(反映彼此刻意裝傻的互相摸索)。跑步中的永勝再補一句:「他媽的,明天有他好看的。」顯然經過幾秒,他已能聽文會意,知道「同性」加上「戀」所代表的含意,以及這關係當年可能有的負面意義。
算數學的彤弟聽到這兒,接著喊:「你不要去揍人家。」有種乖寶寶的善良,更有種明確接收到保護與安慰後,得了便宜賣乖的興味。
跑步的回得更有趣:「我要在他臉上啃一口,那我跟他也是同性戀了。」我小時候有聽過男生女生牽手會懷孕,倒沒聽過啃一口就出櫃是什麼概念。而且,「啃」臉究竟是什麼畫面?
不管了,算數學的正面回:「我也要啃他一口~」。跑步的竟一個反手秒回:「你不怕他臉上滿臉的青春痘?」一方面是開嗆那沒事搞事的林小華無誤,另方面或許也有點小小吃醋的曖昧,否則怎麼前一秒自己說要「啃」就沒在怕?
仔細想想,永勝對林小華的「報復」方式實在特別。有人沒事說你是同性戀,你會怎麼回?永勝的回應,其實一點都不「直」觀。他並不是先預設「同志=不好」→你說我同志→我就揍你的那種回應方式。
他「報復」的方式,竟是想把林小華「啃」成同性戀:某種程度上擱置了同志=好或壞的判斷,目的與手段只是讓對方能對同性戀有所同理與體會。這種並非「直」覺的回應方式,默默隱含永勝對「同性戀議題」的進步與友善。
關於這七句台詞,即使去掉我誘導性十足的說明,至少我們能學到一招曖昧技巧與對話之術是──跑步的永勝,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正面回答(遑論否認)彤弟一開始拋出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同性戀」。
只要曾身陷「異男忘」的小 gay,大概就能體會,只要對方不說破,不拒絕,這樣的一來一往,就能讓我們從中體驗凡事皆有希望的準戀愛滋味。這一點,我會說明,真的是導演刻意鋪排於此,先餵給我們的一點甜頭與曖昧。
■ 從裸泳到田徑的「同志奧運」
如果各位有心如此「歪讀」這部片,那麼其實全片早在前三十分鐘就已埋下了各種伏筆。這些伏筆,更可能全面翻新我們該如何解讀本片結尾。電影片頭,是一片黑暗中閃爍的兩道光,那是正準備從礦坑隧道回頭走出的永勝與彤弟。黑暗隧道,是彤弟警告永勝不可告人之處,更是永勝口中「咱倆發現的世界」。兩人之所以沒真的走進去,是因為彤弟說裡面深得不得了,根本沒有底。有點敗興的永勝出場劈頭就罵,「他媽的,我真恨不得把我的膽子分一半給你。」
文謅謅的台詞和暗喻,各位大牛如果一開始還參不透的話,下一場戲馬上給了你肉體變現:兩人直接在溪邊全裸曬日光浴。一個笑對方屁股長痔瘡,一個笑對方包皮過長。非常之中二(啊他們也真的就國中生),但也無意間流露,兩人目光已隨自身角色停留何方。(別看漏了鏡頭給各位觀眾的福利,只是國中生還未成年,你各位請多注意)
緊接著是《囍宴》般的「媳婦見公婆」場面。裸泳結束後,李永勝帶著彤弟到他家開的麵攤。哦,原來不只雙方情投意合,家長也買單。準婆婆給彤弟加了顆滷蛋,還跟孩子的爹稱讚這功課好的朋友交得真是讚。
下一幕台版《斷背山》。餵牛吃草的彤弟,碰上把牛群全踢走後,直接翻牆烙幹的超中二永勝。牛躲得一頭不剩。彤弟憤而追上去,兩人動真格,在泥漿地裡扭打成一團。有的異男看到這,想說這不就真的火大打架嗎幹。但是經過東奧時期各種謎因粉專對男子柔道與角力的「腐力」全開,相信各位已不難體會,兩個男子近身肉搏的時刻,在「有心人士」眼中潛藏著浪漫與曖昧。
山頭吵,海尾和。接著來到台版《碧海藍天》。波濤洶湧,這是一望無際的兩人世界,玩累了就回到岸邊。兩人拿出便當第一點,不是自己低頭猛扒飯,而是先給彼此夾菜送溫暖。幼稚的彤弟從永勝書包偷出一紙作文,上面寫的是他想及早看見爸媽從麵攤開到麵店的心願。接著就是為了討回那張紙,兩人開始在大海中追趕跑跳碰的畫面。人生要是能與奧運選手有這兩小無猜的幸福片段,我想那是許多小gay此生無憾的浪漫。
再來是一段重點。兩人就讀的國中要開學。所謂的操場,只是什麼都沒有的一片田。整個至善中學,男男女女同學們一起戮力重建校園:綁足球網,畫自己的籃球框,犁田翻土是為了讓後繼者能在此跳遠。就說東奧時期重看這片特別讚,這片段簡直像極我國體育環境的預言,在一片組織的爛泥地裡,胼手胝足打造出自己舞台的最大功臣,始終是不分男女的運動員。
不過,眼尖的朋友看了片會發現,我們兩位小哥哥對此可不滿意。男男女女的團體行徑裡,並沒有這兩個叛逆小子的身影。他倆刻意躲在鐵絲網旁,更啐著那群人不知閃了沒。這兩個人想幹嘛?他們跟大家格格不入。他們要等操場都沒人,去重畫自己最喜歡的跑道線。
這關鍵的一刻,導演牟敦芾給了個全片最用力設計的畫面。兩人為齊心畫跑道,在銀幕上第一次有了手握手、頭碰頭的連結。只要你願意違背昔日黨國的意志,將至善中學校訓中的「守恆勇善」,變成今日早已習以為慣的「從左往右」看。牟敦芾早已在這畫跑道的起點,賜給他們電影世界裡的「永恆」。
■ 啞巴與同性戀啊,誰才是苦難的禍源?
永遠有多遠?總是同性戀最能體會人世間的一切無常與善變。
青春與死亡相連結。遺憾正是發生在永恆的起點:他們自己畫的跑道線。我說導演在珠心算大戰飛毛腿那場同性戀的爭辯刻意施以曖昧,目的是回憶越甜,對比後的心碎時刻越會令你淚流滿面。
彤弟贏了。他跑向永勝,興高采烈地要跟他跑到終點。後面的悲劇全世界都已預見,就他一個人沒發現:不祥的心跳音效與永勝已跑到扭曲的臉。
永勝死了。劇情雖略帶狗血,所幸來得極早,全片才三分之一不到。導演是要告訴我們,他要處理的重點,不在前半小時的兩情相悅,而是後面這一小時,彤弟這「禍源甲」,其電影中的餘生如何持續為永勝的死懺悔。同性戀與罪,還有什麼比這更常見的搭配。
姜小彤的贖罪之旅,劇情走向沒離大家想像太遠:昔日最疼彤弟的李媽開始恨他,倒是李爸出面挺他。功課好的他開始失常,而原生家庭的爸媽,一會擔心他,一會拿成績壓他,但看見自家貴公子竟在狂風暴雨中幫李家推麵攤車,還是忍不住冒著風雨下車幫他們一起拉。咻一下 time flies,彤弟終獲接納,好不容易李家的新麵店也要開張,一切看似就要回歸日常⋯⋯
關於這部片的電影美學,許多評論早已發表,不敢掠美於前:幾段蒙太奇交叉剪接值得細細品味,也有人指出,後期配音的配音演員聲音太老成,是本片的敗筆與硬傷。讀過《毋甘願的電影史》就能體會,之所以都得配上那足以毀了全片的「標準國語」才算「國片」,以及台灣遲至 1989 年《悲情城市》才能以同步錄音技術拍出一整部彩色劇情片。這拖累台灣電影發展的技術遲滯,實是黨國體制厲行國語運動所致。
扯到《悲情城市》,是為了引出《跑道終點》中許多人忽視的關鍵:一位啞巴。當彤弟獨自一人來到永勝墓前,在一旁默默看著他的,是一位本省籍農民樣的啞巴。是他給了彤弟掃墓用具,而在許常惠作曲、黃明正彈吉他的配樂掩蓋下,我們看見彤弟不斷地向啞巴訴說關於永勝與他,他那永遠不敢對別人說的話。說得愈多,鏡頭就將我們退得愈遠。
台灣戰後幾項重要社會差異,從劇中兩個家庭明顯有別的「階級」,到本片主題核心的「性」,導演也用這兩家人以外,唯一一位重複登場的啞巴角色,說明他絕沒錯過最關鍵的「省籍」。在本片出現的本省人不會說話,是個啞巴,卻最能同理同樣邊緣的彤弟。
啞巴的第六次「出現」,是劇情最末,當彤弟備受衝擊,想去掃墓,主動先來找他。原本在家遍尋不著他,後來才看見那親切身影出現在山坡下。彤弟喊了句「老先生」,想不到那人一轉身回了句「幹什麼」──用標準到不能再更標準的捲舌國語冷答。從沒有過那麼一句話能如此澆熄彤弟,原來他不是那位啞巴。
一位啞巴,一句話。導演早在 1970 年,比《悲情城市》更早示範如何只以簡單一句話,說明這故事一點都不簡單的複雜。
(未完,因平台上有文字限制,全文請見://bit.ly/3fIHj1G)
3 ) 剧终 (附链接)
永胜,我实在没有办法,好像什么都不对
记得以前,我们谈到对父母的态度问题,有时候觉得应该依顺
有时候又觉得,应该建立一点自己的性格
但总是弄不清楚,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跟他们谈,他们说我们是小孩子
不跟他们谈,又说我们孤僻
反正一句话
除非你不遇到事情,一旦发生事情,什么都会不对了
今天的白,说不定就是明天的黑
世界上的一切是是非非,都会因为时间、地点和人的不同
随时改变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也弄不清楚
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弄清楚了
可是,这次的事情,我是知道的
我不能替你,正如你不能代替我一样
所有我做的事情,今天是黑的,我想,明天仍旧是黑的
这一点,将不会改变
我算理出一点头绪来了
我想……我想我是懂了。
//pan.baidu.com/s/1ehPC4VsEx4NmeGzBBvjdrQ
提取码:hgk2
4 ) 我想对你说
永胜,我实在没有办法,好像做什麽都不对。记得以前,我们谈对父母的态度问题,有时后觉得应该依顺,有时后又觉得,应该建立一些自己的性格,但总是弄不清楚,在什麽时候该做什麽。跟他们谈,他们说我是小孩子,不跟他们谈,又说我们孤僻,反正一句话,除非你不遇到事情,一旦发生了问题,什麽都会不对了。 今天的白,说不定就是明天的黑,世界上一切的是是非非,都会因为时间、地点和人的不同,随时改变。到底为什麽会这样呢?我们也弄不清楚。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弄清楚了。 可是这一次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不能代替你,就如同你不能代替我一样。所有我做的事情,今天是黑的,明天仍旧是黑的,这一点将不会改变,我算是理出一点头绪来了。我想,我想我是懂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仅从网上四处搜罗而来的几张剧照和修复中心的剧情介绍,想象着这部电影的样子。
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彤与永胜,经常在一起练习跑步,但是有同学就说他们是同性恋。俩人因为此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扭打在了一起。

打架后,迷茫的永胜在跑道上奔跑,然后问了一个问题:“同性恋,什么意思啊?”

这件事情过后,俩人依旧像没事人一样,一起锻炼,可是再也没有以前那样自然,永胜也有意无意地地跟小彤保持距离。在一次跑步训练中,永胜在跑道上练习,他今天明显有点不对劲,脸色发白,不住的喘大气,小彤并没有让他停止,而是鼓励他继续加油!

永胜又跑了两三圈,脸色愈发地难看,看见小彤就在前面,小彤还在给他加油加油,此时的他再也支持不住,倒向小彤的怀里,不住地往下褪,小彤立马扶住了他。

永胜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永胜家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小彤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他含着眼泪对永胜父母说出了实情,永胜父母更加悲恸,永胜妈喝止小彤,让他不要再说了。从此小彤开始了自己的赎罪,放学就来永胜爸妈的面摊来帮忙,有一次台风来袭,小彤帮助他们在风雨中收摊。

小彤爸说他不要在这样赎罪了,小彤从家跑出来,到了永胜的坟墓前说出来本片开头的那些话。

跑道终点,目前成为我最想欣赏又不得的影片。我在想牟敦芾导演会用什么样的镜头语言来展现这个悲伤的故事。牟敦芾导演,我会有机会欣赏到这部影片么?
5 ) 大师起点就牛逼!
终于看到了中国殿堂级CULT电影大师牟敦芾的失踪了近半个世纪的黑白电影《跑道终点》(1970),这部电影应该是他的第二部作品,他的处女作《不敢跟你讲》也已经找到,在台湾的资料馆里存放,前几年还在电影节公开放映过(但无源)。 这两部电影都是因为某些原因,在当年被台湾当局禁止公开放映,所以一直被封存至今,甚至专业研究者都没有看过,所以一经公开就引起了小小的波澜。 影片前三分之一是描绘了两个半大小子的相爱相杀,他们每天形影不离,去废弃矿坑探险,弄得一身脏,然后脱光衣服裸奔入大海洗干净再回家(罕见的自然主义,没有避讳裸体,大量的外景,和当时流行的摄影棚电影大相径庭)。两个处在青春期的小伙子也非常叛逆,他们互相打闹,甚至在泥坑里打滚,虽有争执,但已经分不开。 永胜是草根家庭,父母每天推着小吃车在街头售卖,他喜欢跑步;小彤是白领家庭,住在有电视机的高级公寓(母亲是“灭绝师太”张冰玉),他擅长珠算。两个不同阶级、不同兴趣的少年竟然走到了一起,可能就是最纯粹的吸引吧。 悲剧猝不及防,一天两人打赌,一个跑步一个珠算做题,看谁快,小彤做完了,永胜还在绕圈跑,步履渐渐蹒跚。小彤说:“同学说我们是同性恋”,永胜说:“他再说我就要啃他一口!” 小彤见永胜跑不动了就为他加油,他不知道永胜已经快要死掉了。永胜的心脏出了问题,但他不想让好朋友失望,还在冲刺,用最后一口气抱住了小彤。牟敦芾新浪潮似的快速剪辑蒙太奇非常凌厉,迥然于当时的其他华语电影。 永胜死后,小彤被道德和情感所困扰,他觉得永胜的死是因为自己,对不起他的父母。小彤的房间床头挂着两人的大照片,暗示他是这份禁忌之恋的发动者。他变得沉默寡言,形单影只。 放学后,小彤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去永胜家守候,起初永胜母亲对他有怨气赶他走,但后来看他是诚心帮忙,也接纳了他。扮演永胜母亲的演员演技是整部电影里最高的,她给小彤盖被子那一幕让人动容。 片中没有庸俗的撕逼大战,两家父母都是朴实本分的人,小彤的父亲开车暗中看到儿子在路边帮忙,但没有过去叨扰。当台风来袭时,他还不顾浑身淋湿帮永胜父母推车。这一幕幕让人愈发叹息如今社会的人心不古。 影片结局是黑暗的。小彤最后渐渐领悟,自己再怎么弥补也是于事无补,他一个人走入了黑暗的废弃矿坑。 牟敦芾从一开始就展现了自己的特殊才华,可惜作品被封存至今,无法显山露水。后来他去了香港加盟邵氏,另辟蹊径,成了一代重口味大师。 《跑道终点》是罕见的台湾早期新浪潮电影,构图、剪辑、配乐也都很棒,就是两个少年的演技欠缺一些火候。据说其中一个少年如今年过六旬,才第一次看到自己主演的电影,而牟敦芾导演也早已仙逝,无法共襄盛举、分享心得,令人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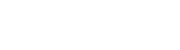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日常的突發變故,以行動重建秩序,一句輕言又整個碎裂,健康寫實的反動? 當年若能上映,也許台灣的新浪潮可以早個十二、三年,永勝和片中的母親劉引商一起現身映後,實在太感人,14歲演電影,48年後才看到自己的作品,已經超過六十歲了,新浪潮前最佳台灣電影(沒有之一),2018.05.05@TIDF-華山
開頭兩光點搖曳(好浪漫!),與墮入黑暗的晦暗結尾,應會記得好一陣子。就算看完一週,黑白畫面還是召之即來。小彤與永勝默契無間的感情、臺灣式望子成龍父母、已有自己看世界方式(所以該作為成年人對待的)少年。牟特別知道怎麼激起觀眾焦慮,跑道與算盤兩段剪接有效。街角想起牯嶺街。掃墓場景美。
好看死了,兩位男同學的情義,第一場戲兩個頭燈,最後一場沒入於洞穴。跑步與算盤的競爭,完成好友生前的夢想!全台走透,他們說我們是「同性戀」,狂風暴雨、永勝麵店、墓上墓下,父母的愛取代不了的兒子。今天的白,明天的黑,我想我懂了。跑道終點,有我抱著你。社會階級,再差幾步蒙太奇
台灣電影史得因應《跑道終點》重寫。《長跑者的寂寞》、《四百擊》,每個地區似乎都有自己的Rebel with a Cause,而戒嚴下的台灣似乎又特別壓抑,尾聲只有深不可測的黑⋯小彤的爆發或許太過,也未必有充分的鋪陳,可是放回台灣脈絡,又很能接受,滿腔的憤怒,化作直白的批判,也化作濃烈化不開的抑鬱。跑道/算盤,精密計算下的反覆(日常)迴圈,以及偶然的閃電颱風、終點前(永勝餐館招牌掛上)的突發,又回到原點,徒勞若薛西弗斯;而兩個男孩所面臨的阻礙,也並未簡化為樣板反派父母,沒有壞人,是一種世代隔閡、時代氛圍。
在悉尼的台北故宫博物展上看到的电影,一直哭着。后面的压抑,无力和悲伤随着音乐一直敲打着。有些东西失去了整个世界都变了,小彤多孤单啊。
心心念念好久的影片,终于看到。从来没有这么一部影片,让我这么不舍得看完。牟敦芾导演,谢谢你!
1970年,台湾电影里的青草男儿,同性情结,裹夹着荷尔蒙与死亡的青春记忆,出尽热汗后,热泪无法停息,无法负荷成长中突如其来的苦痛,无法诉说,无法挣扎,无法得到答案,只有问题接二连三,甚至逼人说出疯狂的话,逼人出走,只是这个世界没有平静的地方,耳边总是充斥着倒计时的声音,那是那天下午的回响,那时他围绕着你在狂奔,镜头拉至半空,看下去就像一个时钟,椭圆形的跑道,他是秒针,你是时间的圆心,你拨弄算盘的声音便是时间的声音,你越快,他便越快,时间便越快,终点也就越快到来,最后他真的倒地不起,尚未弄清的心底的情愫也就此打住,而你活着,你还活着,并且还要长久地活下去,这便是最简单明了的事实,亦是生而为有心人最难以承受的事实。
华语影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品。母题上从青少年不易察觉且被忽视的情感心理上入手,将幽深阴郁的少年思绪缓缓道来,独特而少见的阴暗气质和片中夏日炎炎的灼伤形成强烈的反差,大概从未有电影能够这么早就触碰到这一块小小的角落。前面20多分钟对男性少年伙伴关系炽烈真诚而坦率的描写,对边缘词汇的隐隐指涉,都是布满阳光的,然后意外来袭,急转直下的不仅是故事情节,还有提前来临的关于生死的反应和思索。也同时开启了两个家庭的对比,两家巨大的地位落差凸显出立竿见影的效果,创作者是有社会批判的,还存着一份善意和怜惜。片中对男性身体的直接拍摄是大胆的自然的,营造的疑虑重重的少年形象亦然是不可取代的。不同于主流电影的审美和立意,完全在意人的存在意义。
真是沒想過台灣有出過這樣的電影,本次TIDF最驚豔
太奇特了!内核上处于60年代健康写实电影到台湾新电影的承接处,质朴又哀婉;但是暗涌的反骨又有日本新浪潮的凄厉;剪接上有法国新浪潮的实验性质;环境与个体性之纠葛关系的交代上,包括空镜头,大全景,超广角又有维斯康蒂唯美主义的影子;而物候和景物的自言自语,以及镜头对其质感的触摸,又像是偷师了塔可夫斯基。太多电影中都能找到这个片子的影子:四百击,上帝之国,今年的亲密甚至直接“翻拍”了前半段。我只能说我目瞪口呆。
目瞪口呆
真棒,有些日本新浪潮的味道,光影、镜语、人物、剪辑都是一流,1970年台湾就有这样的电影,也是厉害,尽管是黑白片,掩盖不住的亚热带气息扑面而来,两个小男生演得很自然。要是牟敦芾一直这样拍下去,后面不去玩邪典,可能就是一代文艺大师了。
2012年7月12日,我給本片建了豆瓣條目。直到最近才有機緣看它。當時在劇情簡介裡說了一些暗記猜想。今年有人更新條目,全給刪了。刪了也罷。有些話留不留下都一樣。就像本片,即便出土了,其薄如紙的謎面一條一條在眼前飛來飛去,誰看得見?
牟敦芾给人的印象是香港导演,比较大尺度,但《跑到终点》却是实打实的台湾电影。影片是关于一对小玩伴比赛,其中一个娃猝死,另一个娃心中很难释怀的简单故事。音乐和画面的留白都是比较多的,这后后来的一些电影有很大区别。影片表述的情感很细腻,清风拂栏,哀而不伤。
如果说影片的大部分拍摄对象是符合逻辑的日常,好友的猝死和招牌的破碎代表了这样日常的崩坏。无忧的欢乐时光总会戛然而止,家庭条件的进步终究是一层表象。随后而来的主人公近乎神经质的忏悔和愤怒,是否也是对于日常的一种反叛? 伦理的实践之后,是不满和醒悟,而他也最终选择走进了黑暗深渊。
乍看是隽永冲和的散文笔调,“草创”期的台湾农村大远景,镜头中亲密厮打的少年身体在水浪泛起的银波里闪着光,生命的机能蓬勃、野蛮、肆意,仿佛两个少年能一起走到天荒地老,大胆的裸露镜头与隐晦的同性情爱。矿洞的回声如死亡预告,珠算与跑步双线并进的剪辑渐露生猛之色(多处平行剪辑几乎榨出苦涩胆汁),留下的那个注定要在这缠作一团的噩梦中反复咀嚼失去的痛苦,他没法和任何人说起这些究竟是黑是白的事,于是一日日地向守墓人诉说(唯有对陌生人才能开得了口,无台词的远景处理很棒)。结尾非常好,既然一个人到达不了承诺过的地方,只有回到曾映照出死神的黑洞里去。
早期牟敦芾在台湾时期的作品,当年被禁,据说在台湾电影年鉴上始终没有片目,直到去年TIDF才出土。如今看来仍觉得相当先锋,前1/3部分是在华语电影里第一次看到将赤裸或半裸的同性身体袒露于全景镜头下的自然风景(山野和海滩)中;其后牟敦芾让其中一个死去,使影片得以聚焦于主角的创伤心理,并插入一系列关于阶级、族群的饱和式表征,两段回忆段落采用平行剪辑(在高速拼贴中使过去和当下彼此交缠,构筑梦魇般的情感空间),视听都非常有力。唯一不足的似乎是在过度郁烈的作者意图造成的复调拉扯中,最后的转折稍显“过火”。
侯孝賢楊德昌都拋到腦後了..........如果前者是對於某種過去的自己的緬懷,牟敦芾展示了一種"現在"
既然导演是拥抱西方文化的文艺青年)我感觉它的根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一线里的:自取毁灭的少年,非职业演员,没有路人没有环境音的场景,各种scape穿梭,阶级挣扎……然后用这些来描述当下社会难以消解的困惑。因为好歹也70年了,加入了精神层面蒙太奇这些手法;台词里直接写入“同性恋”确实是很先锋了。
台湾新电影的前章,一位三级片导演被埋藏多年的艺术片佳作。那两个男孩成日在青春里奔跑、撒欢、摔打,亲密得犹如爱人一般 ,但这种感情究竟是什么?他们还未来得及分辨就已被命运打断。少年时代有太多迷惑,而之于这些迷惑,电影只给出无尽的留白,是山间的风,是街上的雨,也是少年沉默的背影。最后时刻那个孤独的男孩走入矿洞之中,他对着离开的挚友喃喃自语说自己懂了,但他到底懂了什么?一切都没有答案,一切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