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优质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剧情介绍
杰克(Jesse Metcalfe 杰西?麦特卡尔菲 饰)的姐姐莉莉(Kiele Sanchez 基拉?桑切斯 饰)沉湎于死亡漩涡,多次自杀未遂,最终被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为了解救失去自由的姐姐,杰克假装成精神病人混进门禁森严的精神病院。偶然间,他发现医院内的吉尔尼迪大夫竟然用病人做试验。他强迫并人们服用一种药物,并将他们变成嗜血狂魔。 得知真相的杰克策划逃跑,他们触动了医院内的电子保全系统,精神病人全部跑了出来。当然,也包括穷凶恶极的吉尔尼迪医生和他冷酷无情的吸血军团……我的初恋女孩奥菲斯粉雄救兵:巴西篇第一季少女椿殖民地202110-10书中自有男友力满园春色香港版表姐,你好嘢!2国语天山的红花闭嘴吧!高金灿大酱老婆就一个好邻居疑犯追踪第五季夜魔人功夫传人之龙拳小子恶魔之椅斗龙战士之星印罗盘西部执法者心理罪万圣节传说小丈夫遗留搜查4圣诞老人快乐再疯狂第二季幻影凶间石俊峰办案记饿狼传说:满月杀手罪与罚2002画中仙岸边露伴 卢浮宫之行只有喵知道群尸屠城卧底警花棒球之爱2011白山黑水拉凡德山的暴徒丧尸的屁股化身邪魔对丑陋人物的简访斗魂之熊孩子我们命之途鼠胆熊心传染病(粤语版)初吻1980东京铁拳黑钱第一季
长篇影评
1 ) 来自乱七八糟瞎写的公众账号文章
舒尔茨毫无疑问的是一名超现实主义大师,其作品充满了无数天马行空的幻象和想象,艾萨克·辛格对舒尔茨这样评价:不容易把他归入哪个流派,他可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他有时候像卡夫卡,有时候像普鲁斯特,而且时常成功地达到他们没有达到过的深度。
作家余华给予了舒尔茨极高的评价:“即便有卡夫卡的存在,布鲁诺?舒尔茨仍然写下了本世纪最有魅力的作品之一
《沙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地,主人公以寻父为名穿梭于各色的时空中,时间的分岔,欲望与精神的纠缠,精神突围的悲歌或赞歌,精神内部机制的微妙与嗳昧,神话般的背景,无一不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影像世界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你可以尽情的将思绪放飞,时间和空间早已错位,而叙事者仰或是参与者仍旧不管不顾,流连于各个世界之间。
无数意象在这部影片中不断呈现,无论是永恒的寻父主题,还是淫荡的女人,若隐若现的造物主,稀奇古怪的飞鸟,失明的穿梭于各个角落的列车长,然而,剧情本身或者是意象解读在哈斯的这部《沙漏》中已然不重要,就单单是导演所创造出的这个影像世界,就能使我们流连其中,难以忘返。
大量中近景的长镜头成功的串联起各个角色和场景,精心布置的空间格局,迷离的彩色灯光和各色魑魅魍魉接踵而至,镜头很慢,而意象却蜂拥而至,在你等不及细细咀嚼的时候,悄然隐退。
“还记得多少呢?”
“全都忘记了”
如同梦醒时一瞬间的迷惘,除去睡梦中强烈的情绪印记,什么都没留下,又或者多了些什么,却又很难用言语表达。
如果说绘画是作者将自我意识投射在画布之中,摄影是主体将动态真实的瞬间停留在胶片之上,毫无疑问的,哈斯的《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则是瞬间与永恒,自我意识和现实世界,流动和静止的综合体,它带领读者走进那个封闭着的却又永恒流动的世界。
原作节选:(原自饭托)
普通事件都被依序排列在时间中,好像一段一段地串在一根绳子上。这里每个事件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它们互相紧紧贴在一起,推挤着接踵而至。这种流动秩序对任何视连续和顺序为灵魂的叙述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那些在时间中没有自己位置的事件,那些来得太晚,所有的时间都被分配、分割、派定后才出现的事件,那些被扔弃在冰凉中、不曾被登记造册、悬浮在空中、无家可归、游移不定的事件该怎么办呢?
难道是因为时间太窄了,无法容纳全部事件吗?看在老天的份上,有给时间投标的吗?车长啊,你在哪里呢?不要激动,不要惊慌,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参照系中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2 ) 我不想要食与色
小时候的约瑟夫,被书中的地名和故事吸引,总是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好在他的父亲经营者一家杂货铺,日子过得还不错。坏的地方是,他父亲似乎总是不着家,小时候的记忆总是始于母亲责令自己去寻找父亲。
杂货铺经营布业生意,在小时候的记忆里店员们是虔诚的信徒,拉着自己一起歌颂上帝,小约瑟夫也在梦幻中坠入了宏大叙事的陷阱。等到青春期,店员们开始鼓动他和阿德拉建立性关系,他一方面羞涩于面对赤裸裸的性,另一方面也因戴上了“帽子”而无法享受世俗的快乐。他和阿德拉争辩消防员的伟大,书籍的神圣。在被忽视和鄙夷之后,他靠在床下,发现阿德拉的姘头昨夜就睡在她的床下吃着粘腻的果酱,他邀请他吃,蛊惑说它是多么美味,可约瑟夫尝了一口觉得令人作呕。
约瑟夫拿着神书去寻找父亲,路上遇到了不远万里来谄媚父亲的卖鸟人,无数为了现实利益而讨好父亲的市井小人。约瑟夫看不起这些人,可父亲真正地与他们打成了一片。这让约瑟夫迷茫、嫉妒,不知道人们怎么能不依赖书和信仰获得意义呢?
父亲说,长大后的某一刻你就会发现书不重要了,你不会真正地在意它,它就会像不死鸟一样迅速烟消云散。不忿的约瑟夫找到了鲁道夫,鲁道夫和约瑟夫看起来是一类人,集邮、看书。他把愤怒发泄给鲁道夫后,见到了另一个女人——碧杨卡。约瑟夫为了获得碧杨卡,卷入了一场侦探式的皇室迷局,最终或真或假地发现碧杨卡的身世秘密。可碧杨卡竟然要求约瑟夫和自己发生关系,“堕落吧”,这种邀约约瑟夫感到错愕。由于没有得到好的回应,碧杨卡闹脾气说鲁道夫比他强多了,言听计从,可以随意玩弄。约瑟夫感到崩溃,从剧中解离出来,同时列车长出现了......
他见到了父亲和鸟儿,父亲要求他指出鸟,他就学鸟叫,父亲对他非常满意。临别时,父亲把他的镀金帽子摘下来,换上了新帽子,并祝福他获得鸟儿的一点点【新东西】。所谓新东西,其实就是世俗享乐。
回到家的约瑟夫,在母亲那里得知店里出现了许多无法查清根源的偷盗行为,母亲非常地担忧,派约瑟夫送茶给父亲,然而真正到达店铺时,店里早已经没了神圣感,充斥着世俗、奉承与情色,唯独没有书、宗教和秩序。死的头被制作成玩物,殖民地的残忍可见一斑。新宗教使团的到来使约瑟夫眼前一亮,以为那些金色皮肤的异乡人能够神启般改变家族的命运,然而他们只是前来做生意的俗人。随后驻地遇到了一连七年的饥年,饿殍遍地,即便是节日也不能敞开肚皮吃。直到那一刻,约瑟夫理解了“只要发生过,就是发生过”这个道理,也知道了自己才是本部戏剧的唯一主角,一种虚幻的控制感、解脱感冲昏了约瑟夫,他急于找到碧杨卡。
3 ) 布鲁诺·舒尔茨的电影改编:《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
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不是一种平行移植,而类似于一场翻译——它涉及媒介、语法的转换,涉及在一种文体中可见的信息在另一种信息中变得隐形这个老问题。毕竟词语是依靠想象的,电影却主要是用来“读”和听。 舒尔茨的主要职业是画家,这帮助他在斯大林时期逃过一劫,当时他画了两年的斯大林像。他还曾为自己的作品《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作过插图,出版过一本兼有蒙克和马索克风格的《偶像崇拜集》(The Book of Idolatry)。这并不能保证把他的作品翻译为电影时难度会降低。相反,因为舒尔茨的想象主要依赖多种感官的综合,尤其是事物难以在视觉上呈现的方面,比如生与死的临界状态、色彩的过渡、时间的空间化,以及扑朔迷离的幻觉,这导致电影必须对情节进行重构才能达到跟小说同样的效果。另外,几乎所有舒尔茨的招牌隐喻,还有他打破语言惯例的尝试,都很难在电影镜头中等值地呈现。比如,当他把夜空比作“漆黑的大教堂”时,我们如何拍摄出这样的画面呢?就像当莎士比亚把黎明比作“红色的斗篷”时,他呈现了画家无能为力之物一样,舒尔茨往往只是呈现,而不描绘;他引发想象,但对想象之物却并不给出确切的定义。在《现实的神话化》一文中,舒尔茨提到:“词的生命存在于一种联结趋势中,像传说中那条被切断的蛇,黑暗中各个碎片找寻着彼此,那词向着一千种关联收紧、拉伸自己。”这种词语之间的引力和有机化的趋势,是很难在视觉上呈现的,它有时反而以视觉上的电流短路为前提。 波兰导演沃伊齐希·哈斯的影片《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Sanatorium pod Klepsydrą,1973)提供了对布鲁诺·舒尔茨原文的一种很好的“翻译”。同名小说是一个在中文中只有30页的短篇,电影却长达两小时。也许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舒尔茨感”,哈斯把舒尔茨的其他小说,如《书》《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跑》中的某些情节也拼贴在这部电影里。 影片从一节越驶越慢的火车车厢里开始。哈斯很好地捕捉到了舒尔茨小说的前现代氛围,即使是火车这样的工业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在电影中也与吉普赛式的流浪联系在一起,并且泄露出一种笨重感,看上去就像是一只侵犯感不明显的生物哈着气,里面的乘客像是在马车车厢里一样慵懒,处于漫游的、精神涣散的状态。从这个开头,我们就不经意间滑入了“沙漏时间”,而非“钟表时间”,前者是一种更加天然的计时工具,与自然的节奏、人工的粗疏联系在一起。 舒尔茨世界里的现实总是充满了疏漏的,是一种已经解体了的事物的碎片,仿佛处在事物的黄昏时刻。沙漏是一个原型象征,作为时间的衡量尺度,它却只能在空间里呈现。同时,它也永远处于满盈之后的耗损状态,换言之,一种事物的开头已经过去、很大部分难以追回的状态,一种“不及”的状态。沙漏意味着在故事开始时,我们并非处于起点;而在故事结束时,我们也并非处于终点。计时的工具必须比故事更长,我们只能从中间或“晚期”开始。 火车停滞、靠站的那一刻,我们便到了疗养院,一个和肉桂色铺子、鳄鱼街一样的地方,一个幽闭空间。可是那里的一切早已开始,“我”的父亲濒临死亡,并且已经在这种临死状态徘徊了很久。窗户上挂着破碎的蜘蛛网,地板上满是灰尘,床头柜上摆着药瓶和一杯天知道是猴年马月冲制的冷咖啡,这寓示着这是一个“旧”的世界。“我”很快就会发现,“以前似乎来过这里”。电影和小说在主题上没有显著差别,都是讲叙事者对临死父亲的告别。但这场告别延续了很久,本来是一种临界状态,却经过多次“回放”,时间处于冷冻然而接近支离破碎的状态,仿佛是在玻璃被寒风吹裂的那一刻凝固下来,之后就在碎玻璃片中以最低的速度来回折射。我们可以用《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跑》中的一段话来概括这一奇异的现象: “这个时候,我父亲确实是死了。他已经死了很多次,总是死得不干不净,总是留下一些疑点,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死进行重新校订。这也有它的好处。把自己的死亡改成分期付款,父亲让我们习惯了他的离去。我们对他的归来已经无动于衷,每次都越来越短,越来越可悲。” 不管是哈斯还是舒尔茨,都经常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者,但是和一般的超现实主义的能值游戏不同,哈斯和舒尔茨都尽量言之有物。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容词和色彩的盛宴背后,导演和作者都有一些需要从容道来的东西。疗养院是死亡的发生地,但是“父亲”一直处于肉体尚未冷却的库存时间中,如同博闻强识的富内斯,在梦一般的环境里,他身体日渐虚弱,仿佛走着走着就会一头栽进土里,他继续在一家眼镜铺旁盘了一个小摊,沿街兜售自己的货物,兴高采烈。“我”被囚禁在这一濒死的循环中,最终发现这一切都是名不副实的虚假……当然,“虚假”在舒尔茨这里的含义已经被颠倒了。电影中有好几分钟的傀儡人物场景,“我”在其中看到一个人机械地倒下,脸上被打破,露出陶制外壳下面的塑胶眼球和黑色弹簧片。对于迷恋外观的舒尔茨而言,这也许要比空无更容易让人接受。哈斯的另一部作品《萨拉戈萨手稿》(Rekopis znaleziony w Saragossie,1965)也涉及这种“外观”的形而上学:一个年轻男人在山洞中遇到几个自称是伊斯兰教徒的女子,于是发生了一场《游仙窟》式的故事,那部电影在讲述时也显示了一种异教式的宽容姿态。 作为创作的元指涉也很好理解,舒尔茨的生平和作品经历了被诗人和研究吉卜赛生活的学者耶日•菲科夫斯基考古并重新发现的过程,而舒尔茨本人则多次把自己的写作类比为是对童年记忆的考古学研究。“我们通常认为词是现实的影子,是它的符号。翻转这一表述才会更为正确:现实是词的影子。哲学实际上是历史语言学,是对词深度地、创造性地探险。”在他看来,写作类似于巫术,或是神话,通过这种行为,他可以召回自己的童年,也就是时间尚未解体的那一刻,那时的宇宙处于原始的发酵和圆满之中,一本普通的日历书可以被当作唯一的世界之书来反复品咋,而一个孩子可以从中窥探到世界上所有的秘密,比成人世界的加起来还要多。童年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新鲜,并趋向无限的衰落,人在生命起源阶段对事物的有机把握渐渐被年龄封存。成年就像是废墟,写作者只能通过自己的笔在断垣残壁上寻找昔日的蛛丝马迹。

要在视觉上表达这种空洞的、分崩离析的时间,展示它的磨损和筛子般的千疮百孔,或者是人物的没日没夜的昏睡,就像舒尔茨用文字的炼金术展示的那样,当然不能再采用舒尔茨本人的词汇。哈斯试图在自己的镜头中打通异质的空间,实现舒尔茨在两个相邻的词语之间制造的令人眩晕的效果。比如,影片中有多次,主人公钻到卧室床底(寻找什么或是为了躲藏),暂别了卧室内的对话,却在床底遇到了找了许久的旧书籍或是什么人;当他从床底另一端爬出来,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里往往正在载歌载舞。于是室内、室外,床底、床上的故事就获得了“隔壁感”,这也是舒尔茨在词语之间成功建立的隔壁感。
4 ) 哈斯的四维空间
Movie2019No.118《砂质时镜下的疗养院》一封瑰丽奇幻写给父亲的致歉信。以时间的嵌套结构展开,比萨拉格萨更奇幻隐晦,更具象征意义。每一个结构都是一个独立又与其他结构有关联的空间,空间彼此以门、床底、地洞这些梦境中经常出现的元素相连,每一个空间都承载着对一段历史的回忆和哈斯融入其中的感情,有对年少生活时没能帮助父亲母亲的歉疚,有对纳粹残杀犹太人的愤恨、恐惧和哀恸,有对父母经商理念的质疑,有自己年少时的性觉醒和性冲动。
影片开始哈斯坐着火车,如果注意车窗外的风景,能发现列车在做圆周运动,如同表盘,行走方向是逆时针。暗示时间倒流。梦境开始,疗养院大门是嵌套结构的开始,前半部分越走越深,后半部分从床下原路折回,又回到疗养院大厅,本以为终于要醒过来了,没想到换上了一幅假眼,穿上了时间列车上列车员的制服,又被护士重新推到了时间的沙漏中去,陷入其中再不得出。
非常美丽的一部电影,构思精巧,有关四维空间的描述,诺兰严谨而恢弘,如同交响乐,哈斯则把四维空间做成了鲜艳瑰丽极具民族色彩的的迷幻民谣。
5 ) 在密训的密训
1973年的《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是波兰导演沃伊切赫·哈斯最为奇诡绮丽的作品。哈斯的野心显然不只在于将布鲁诺·舒尔茨这位文学大师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影像化,而是在糅合和集聚舒尔茨之下试图对苦难之国波兰及其历史进行高度概括和细致呈现。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得益于舒尔茨,影片所采取的并不是外部与现实的逻辑和视角,而是聚焦在不断为外在力量所塑形或者不如直接说是捏揉的主体(个体或波兰犹太族群)身上,并以影像这一外化形式悖论式地持续朝内牵引:空间繁复折叠,时间持续崩塌,而童年和父亲正在不断死亡与复活。
哈斯舍弃了舒尔茨小说中的父亲-动物的直接变形,削减了轻盈,并在某种程度上更改了原作主旨,但影片仍是在舒尔茨的诸多符号(乃至直接挪用小说语句作为台词)中进行的,而哈斯强大的结构与表现才能使其不致散乱,反而在皱褶与裂隙间拓展与逼近各种可能,同时也让影片真正成了自己的作品,让它与《萨拉戈萨手稿》一起璀璨镶嵌在他创作生涯“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内心独白”中的第二环。
于其间,于哈斯褴褛之梦的长镜中,脚步是不间断的,但你不知道自己走过的是不是时间(以事件为表征的历史-时间),是时间的流逝和重回,还是两者几乎不可逾越的距离,唯一确定的是你找不到归宿,永远——
“够了!离时间远点儿,时间是不能摸的,不要刺激它!你拥有空间还不够吗?空间是为人类准备的……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不要擅自拿时间捣乱!”(布鲁诺·舒尔茨,沙漏下的疗养院)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电影有什么感受,可能会分读没读过舒尔茨原著,以及了不了解波兰历史两种。我呢,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喜欢舒尔茨,但对波兰一无所知。波兰这个国家很奇怪的,出各种精神病艺术家,像电影的祖拉斯基和哈斯,文学的舒尔茨、密茨凯维奇还有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卡尔丘克这样的。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波兰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小国,几百年前的大国,到后来一直被瓜分,导致它文化里有种深深的不安感,呈现出来的作品就会是撕裂和癫狂,在东欧荒诞派里别具一格,和同样也是小国、文艺里也是诡异的日本也不一样,波兰的精神病里没有那种病态,一直有一个向上牵引的,或者说形而上的力量。
电影的主体是改编自舒尔茨的同名短篇,同时糅合了他的其他短篇(舒尔茨只写了不到三十个短篇),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更像是在各个短篇之间进行跳接,当然哈斯的转接做得很漂亮,差不多就跟梦的转接一样自然,而且很多镜头都还是长镜。我们可能会说,一个艺术家的才能就表现在他素材的呈现方式或者对素材进行搭配的能力,也就是说艺术其实就是在拼想象力(哲学和科学也是啊),想象力归根结底就是新的结构,新的链接,那我们说哈斯做得很好。
但哈斯在影像化的过程中,有改变的东西,有沉默,我们真正要去看的是这个沉默,我们去理解一个作品,其实看的更多的并不是他表现了什么,而是他没有表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其实都没有那些没讲出来的或者没能讲出来的话真实。
哈斯的省略,首先有他不得已的地方,从文字到影像,嘴巴到眼睛,肯定要丢失很多东西,文字本来就已经是固定和排除了,视觉的剪除只会比文字更厉害,所以怎么去抵抗这种限定是他要认真考虑的东西,方法当然就是超现实,是舒尔茨和哈斯共同的选择。不遵循现实逻辑,不是因为现实缺乏或者现实乏味,而是我们在恢复和维持被现实削减掉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就像使这个电影运转的核心:回拨时间,恢复各种可能性,甚至是相悖的可能,重新死亡的可能,他父亲在叙述之外其实已经死了对不对,甚至我们也可以说主角约瑟夫其实也死了,但是他死得很混沌。这就是很荒诞的,跟舒尔茨自己的意外死亡一样,舒尔茨是个犹太人,50岁的时候被盖世太保枪杀,但不是死于对犹太的仇视。因为有才能,舒尔茨被一个盖世太保保护,但是有一天这个盖世太保杀了另一个盖世太保的什么人,那个盖世太保就杀了舒尔茨作为报复,很荒诞,死于一场游戏,当然很难说反犹不是一场更大的游戏。
第二个是改编必须的舍取和变形,也正是舍取才会让改编的作品真正成为自己的作品。尽管舒尔茨小说本来就以绚烂的想象力和色彩见长,但哈斯的具体影像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很赞叹,那些场景、调度,但技术解析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你当然可以去解读它的隐喻、意指借符号、色彩去厘清它的脉络分层,蓝色调和白色调,但这不是主要目的。
我们要去看在哈斯舍弃的是什么,是舒尔茨的轻盈和灵气,当然这也不能说是失败,只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已,但这个能让我们更明白这部作品。
可能和我们观影感受不太一样,我们去看这个电影觉得它的主题是应该是梦和时间,至少是各种外在力量聚集在个体身上,塑造“我”这个主体之后的再映现,关键就恰恰是这个,这个在超现实中自然地走来走去的人是谁,这个“我”是谁。那哈斯的野心当然不只是影像化舒尔茨,而是在糅合和集聚舒尔茨,然后试图对波兰或者我们说波兰犹太人的历史做一个高度概括。舒尔茨当然也试图重构自己或者说族群的祖先,但舒尔茨用的是飘忽的神话,一个无可名状的东西,那影像其实很难表现虚无,因为视觉直接就是可见的,它无法从无开始,梅洛-庞蒂讲,视觉不是认知,视觉中的我也不是虚无。
而哈斯呢,给本来已经是具体的影像添加了另一种具体,这让哈斯更接近卡夫卡。卡夫卡是很具体的,所以卡夫卡其实是个彻底绝望的人,那个守门人最后说,这个门是为你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这就是最绝望的时候。不知道舒尔茨生活中是不是绝望,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集中营,《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在舒尔茨不多的小说中算是沉重的,但其实还是很轻盈,有逃逸的可能,小说开场描写的那列火车是指向了某种不堪,但没有明指是什么,而哈斯在电影开场,在火车的意象里直接加进了集中营的蕴含,给影片设置了一个沉重和具体的开场。当然接下来主人公就离开了这列火车,来到了一个混沌的空间,也就是开始了对舒尔茨的整合,去加强那些小说间松散的联系,填补它空白的地方。但有了这个基调,那些飘忽的台词和场景就想要往一个什么东西、往具体上去落靠。
好在一部伟大的作品有很多层次,所以不熟悉波兰和波兰历史并不妨碍我们进入,就像我们八十年代引进和学习拉美爆炸,其实也是略去了它的现实蕴含,我们只学了“多年以后”这个时间和叙述结构,不知道马尔克斯是个左派,老朋友略萨甚至还竞争过总统。更何况电影本身也含有这个主题,这就是时间。
电影里为什么是这样的时间?我们知道,时间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时间和空间、意识一样,只是一个空空荡荡的舞台,如果没有内容,我们根本无法感知,时间最初其实观察出的天体运行的规律,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二十八星宿轮替变换,这样得到节气,按时耕作才不会被饿死,意识呢,黑格尔老早就讲,意识只是一般的虚无。艺术也一样,我们不说这个是梦,因为我们知道梦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情绪,里面的人物、情节都是随意被用来填充的,艺术不一样,艺术不能是随意的,更不能是空白的,它需要东西需要血肉来承载,对肉身如何塑造以及塑造得如何,才让艺术家有了各自的风格和高低。
对于时间来说,填充它的就是事件,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发生,都在经验,这个不可避免,但事件或者说历史-时间如何塑造了你,这个是可以抵抗的,只要逃开现实主义的叙述逻辑就可以。为什么现代艺术都不再讲述故事了呢,现代的人死了,长期以来构筑现实的“我的人生是一个故事”现在需要变成“人生是一个白痴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现实和梦一样,同样只是对一个个“理念”的模糊接收,两者都是第二级的东西,所以无所谓层级次序的分别,人在今天比起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来,无疑都更像一堆杂乱无章的幻影,我们应该像第八十一分钟的那个角色一样,在身上挂满钟表,就像挂上勋章。
我们其实是不能占有时间的,更不要说连续性的时间,我们只有空间,小说里也说,时间是不能碰的,但空间是给人类准备的,我们一起离开那列火车之后,目睹的其实不是时间,时间根本不可见,我们进入的只是空间,一个不再有时间的死亡空间,那里面事件当然还在发生,但已经不再是在时间里发生,而是发生在时间空间化的空间里,在意识-空间里。所以也可以讲,哈斯用自己的风格去丰富舒尔茨的,更多的是在空间方面。我们要学的,可能也不是他如何具体地拍这部电影,而是我们每个人要怎样去确认和回应发生(发生和没有发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怎样去叙述它,去在空间里面一个点一个点的生存,我们要学的是这个,把自我夹在经验的实在性与意识的否定性中,去逼出人真正的东西,像主角约瑟夫那样,最后从坟墓里爬出来,成为自我否定的上帝(我们是自己人生的叙述者)——瞎眼的列车长,当不再能看时,他和我们,或许就能够去触摸那不可触摸的力量,去承受那不可承受的——
“那些普普通通的书就像陨石。每一本这样的书都只会闪耀一时,那一瞬间就像凤凰呼啸着翱翔而过,它的每一页都会燃烧起来。因为那一瞬间,此后我就永远热爱它们了,虽然它们很快化为灰烬。”(布鲁诺·舒尔茨,书)

荨麻地
——致舒尔茨和哈斯
我那时在夜晚里工作,虽然像但并不是盗窃,住朝北的房间(如果你相信物理的话,朝北永远要比朝南低上五六摄氏度,但是我不相信,这只是经过铁道时别人告诉我的,我如今连话语也不信了,但如果从你那里再也得不出语词了我可能会伤心,像妈妈一样),我在北半球拉不会中断的四层窗帘,想要跳过自杀直接进入到死亡,但可能我早就已经与它混融一处了我不确定,这很难吗?因为在现实里的某些时候我看着一部关于梦的电影,却和生活一样不是正在生活和做梦而只是对它进行回忆和分析,在那里(在人间的所有角落)我犯了一个错误,接着是许许多多个错误,但也也许,没有一个错误能够成为本源和开端,错误的场景、错误的人物以及错误的话语在线上变换交杂着,突然又自然,那些变形和消失的都去哪儿了呢?但也也许它们会再来临,而我会再次看见它们,我一直是我,在同一时间和一生的全部时间——也就是说,在一瞬间接着一个瞬间的瞬间——我的和你的我,牙牙学语和垂垂老矣的我,黑色西服和赤身裸体的我,被审问和被损害的我,瘫痪奔跑和喜悦失落的我,自己父亲和母亲并儿子的我,拥有阴茎乳房太阳月亮的我,荨麻地里的一株和樱花林里的一棵的我,生前和死后的我,所有的这些,我们会再次相遇,但也可能不会,我没有在等着,而是,我只能是我,是博尔赫斯。一颗高贵的心脏曾在我胸膛跃动。
6 ) 人生是一场盛大的步死之旅
《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可以说视觉性隐喻贯穿了整部电影,从而形成了一种视觉在场的形而上学,让整部电影的剧情通过视觉性的感受逐渐展开。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执迷于洞穴幻影的囚徒逃向真实世界的过程,就是凭借高贵的视觉亦即心灵的理性之眼获得真理之启示的过程,是囚徒摆脱枷锁获得真我知识的过程。在这部电影中,哈斯设置了一个寻找父亲的男人,而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二战前期,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这个角色并不是按照常规叙事的模式来完成整个寻找的过程,而是摒弃了真是叙事的模式,让角色完成一种心灵之旅。
在这里可以说电影的主体不再是中心化的主体,而是离心化的主体,一个在欲望的煎熬中找不到出口的主体,那么,让角色备受煎熬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影片中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就是死亡,这部电影就是一场盛大的步死之旅。
本片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二战的前期,这样的设计让本片具有了浓厚的预言性质。《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拍摄于1973年,二战结束于1945年,哈斯出生于1925年,可以说,哈斯是二战的见证人。波兰是在二战中受到的戕害有目共睹,在目睹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之后,哈斯的心里定然是无法磨灭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就是《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中的种种意象。
影片中的男主角是哈斯自己,哈斯借他人之眼来完成自己的回忆之旅,他就像一个胆怯而好奇的孩子,一不小心进入了元荒之境,他只能紧紧的拽着命运的衣角,在色彩丰富的叙事中一步一步往前走。然而,他并没有走进那个美丽的花园,看见的却是一个荒芜寂寥的噩梦般的世界,那是寒冬时节的破败废墟,阴暗的角落,腐烂的枯草,断瓦残垣,冷漠的墓碑......这些强烈的落差,营造了一个阴冷的梦境。
当二战结束以后,整个波兰体无完肤,战争的结束本来带来的是新生的喜悦,正如电影中的天堂鸟。然而战后的意识形态却逐渐走向一片荒芜,大多数经历过战争的人得以幸存,然而最终依然是走向了死亡,不可抗拒,无力逆转。整个影片描述的是一场战争,哈斯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战争的叙述。
让电影,电视,商品广告的影像文化在生活中全面渗透的时候,视觉中心主义已经成了既定的在一种梦魇式的存在。《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在观众的看和银幕的被看之间,主体的无所遁形在可见性下成为异形的傀儡,他寻找的并不是父亲,而是步死之前的回光返照,他的梦境是他存在过的经历,那些支离破碎的画面是他生命的全部,当他把这一切展示出来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当他在坟墓之前挣扎的时候,那便是气若游丝般的无力之感。
哈斯给观众营造出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他无视观众的存在,让梦魇魔术般的展现出来,从而创造出一种生与死之间的隔绝感,从而让意象更加饱满而具有说服力。在这部电影中,意象构成了想象的母体,在这一时刻,影片本身散发出来的魅力足以造成暂时性的自我丧失,从而在视觉上有强化了自我,这个”自我“也仅仅是针对电影中的角色而言。电影的旖旎并没有贯穿于电影的始末,相反,光怪陆离的世界紧紧是因为死神到来之前的欢庆,整部电影描述的是战争,阐述的是哈斯独有的生死观,表述的是一场盛大的步死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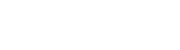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波兰“幻想现实主义”神作之一,某种关于历史和国家的变形表述是这类影片的常态。这部影片根据布鲁诺•舒尔茨的若干短篇小说改编(不只同名短篇),完全是梦的结构,失序的时间循环往复是其最大亮点。影片转场极有想法,广角镜头也用得很有风格。可惜中字太烂看的云山雾罩的……
村上当年是否看过这部电影,那里多像初冬的阿美寮。这是梦,所以剧情衔接完全凌乱,但可以感知到主线和背景:寻找晚年的父亲,家乡的店铺,小镇,童年的历险,隐秘的欲望,交织纠缠。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他的乡愁浓烈。美术超赞超花心思,73年的电影,且都是物理设景不会有电脑特技的侵袭。2014.5.17
一眼就被看穿了;布景、灯光太舞台化了;表演差;剧本在耍猴
8.0/10。FUCK!!!!!疯人院协奏曲。这片简直太让我想起祖拉斯基了。异端,恐怖,奇幻,隐喻,谜一般的赏心悦目;色调、服装、布景、构图、台词、镜头,如痴如狂,如梦如幻,牛逼得有些过份。|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这是波兰人自己的《格利佛漫游记》。
4.5 如果说看绝大多数电影购买的都是抵达某一处的单程票,而本片却是属于极少数的购买了往返票的电影,只不过回来之后的世界早已不是你出发时的那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接一个的梦境之旅,将线性的一切都彻底颠覆,作为观众也需要抛却一切线性的观影定式,去尝试加入一个疯癫的恐怖狂欢节游行;这不是我读过的那个舒尔茨,这是哈斯与舒尔茨所共同创造的荒诞而可怖的新世界,而两人本分属不同的时代,却能展现共通的属性,更可见时间、历史、人性坟墓深处的那种枯朽、腐坏不会过时
太强大了。很多处看得非常感动,快刀的字幕翻译虽然有点别扭,但可以自行脑补其中诗意,画面感很好。对父子的感情描写得抽象又细致,有个递进的过程,个人感觉更像是一个心中有愧的青年来到养老院看望临终父亲的精神描摹,但视角有些利用父亲的神志不清。全片太有梦的状态了,要知道还原梦有多难。
幻像在回憶中盲目遊走,時間就像是沙漏,不斷地倒置,不斷地流瀉。
2019-12-10欧盟影展重看,跟着长镜在这座时间折叠朽坏、空间迷失迂回的迷宫里漫游,真的宛如做了一场长长的梦。改编自布鲁诺•舒尔茨《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但也糅合了其他短篇的事件,完整复刻大量意象---在时间断裂的错层里,一个不断出走、无限复活的父亲,女王般的女管家阿德拉,丑陋鸟群(舒尔茨特别偏好)、变形蟑螂、由盛转衰的布店。这座疗养院是一列时光列车,事件充斥每个车厢,无关紧要的事无处安放,经常串联到其他车厢(时空);更是一个巨大的放置时间切片的抽屉,可正反序放映或重组,每推开一扇门就是一个全新或已踏足过的时空黑洞。于是他重游经历了各种大事件,近现代历史被微缩进这个时间迷宫,这是「反刍的、二手的」时间。迷人的废墟景观,超棒的时空转场,想象力澎湃瑰丽,无比强大的东欧超现实啊!
很奇幻很诡异,不知道波兰还曾拍过这种片子,那是1973年啊,很可惜原著没看过,不是很能搞懂其中的意思,但大致还算分明,镜头很有意思,音乐和美术十分出色,场景也很迷幻!
断瓦残垣营阴梦,踽踽独行不可拒;命将终寝旧经复,气若游丝冢前挣。
如同对陌生人的梦境毫无兴趣。
不知道毕赣和杨超看过这片子没 但今年突然出现了两个对时间的不确定性如此表达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这位波兰大师 然而 如果说哈斯对时间不确定性与进入一个时间无法被限制的空间里的表达是优秀的 那么国内某些人效仿的这个小套路所用的手法只能说是拙劣的
我的记忆,它们本是游荡和迷失的书页,如今在异象之间,它们终于结集,尔后引诱我进入沙漏滴成的泥潭,迫使我重返,迫使我面对:我是无人收聚的羊;我是虫蛀的衣裳;我是灭绝的烂物。我制造的记忆如今制造了我,我穿行而过的语句如今穿行于我,最终它们一页一页,与我的一切一同消耗在无指望之中。
#2019欧盟影展##百老汇电影中心#EUFF没有掌声的一次放映,不是因为不好,相反是因为太“神”了。气质独特乃至诡谲怪诞堪比《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男主从坟墓一直爬到阳间的长镜头惊世骇俗,也是影史经典收尾之一。卡夫卡式的怪诞,浮生若梦亦真亦幻,那个气氛诡异可以让时间静止甚至倒流的疗养院,未尝不是《魔山》的翻版,是生死爱欲的另一场放荡投影。除了亦生亦死似疯未疯的男主约瑟夫,那个存活在回忆里的父亲是影片的另一主角。过去乃至人类历史都是鲜活荒诞的,而现世却是死一样的静寂,宛如瘟疫过后的屠场。鸟的死亡预示着什么,人的消逝又有何种意义?电影主要还是在讨论时间,操控时间本身值得商榷,让腐烂的梦魇一般的过去重现更是罪恶,时间就像上帝的一张神秘之网,深陷其中的人们欢笑哀嚎却无济于事,时间永远不可抗拒。
截止当下,本人看过的最诡异、怪诞、奇幻的电影,没有之一。电影从不合常规的列车车窗外的枯树杈开始,男主角下车经过乱葬岗步入所谓医院的城堡,结满蜘蛛网的餐桌,凌乱摆设与父亲、母亲、幼时偷窥的妓女、恋人……蜡像馆、父亲的病房、父亲的布店……毫无逻辑,场景如同梦境版切换……是场梦?还是临终前回光返照式的人生回溯?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波兰电影拍摄于1973年,编导的想象力实在丰富,但是这部肯定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青睐。
太奇幻的时空交错哲学片了,没能看懂,先标。。重看再更新。。这片production design、摄影什么的都太强了,修复版值得等
说因为疗养院是影射走下坡的波兰政府,1973年其实不被允许选送戛纳,是偷偷“走私”到了法国然后拿下的评审团奖。Has刻意用三个不同颜色滤镜来拍三条时间线,勾兑编织在地狱灵界似的疗养院里,处处诡异影射二战法西斯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屠杀。时间不是直线,而以螺旋状循环轮回在两个平行世界。很妙。
观于欧盟电影展,天主教国家就是脑洞大,通向死亡的列车,由盲人列车员引路,最后主人公也成了列车员,别具一格的东欧犹太传统,波兰小镇,奥匈帝国开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王室争斗,两度穿越,倒叙个人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讨论时间和历史的关系,到最后回归主人公的成长史本身,要素很多,大开大阖。来时刚刚飘雪,前门楼子灯火辉煌,散场的时候已是灯火阑珊,只有雪还在下,观影恍如隔世,一如电影本身。
我穿过一个疯子的葡萄园,那里遍地横陈着死亡的盛宴;从一个出口爬到另一个出口,诗歌和极乐鸟在头顶盘旋,告诉我什么是永恒的
喜歡時空的穿梭。可是電影對白高度詩化,難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