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优质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非凡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剧情介绍
刘根和喜良(黄渤 饰)是在同一个工地干活的工友,一场意外中,刘根不幸离世,临终之际,刘根将自己的儿子小宝托付给了喜良,希望喜良能够带着他和自己的骨灰返回故乡。就这样,喜良和小宝踏上了返乡之旅,他们有五天的时间,如果五天内喜良无法返回工地,他就将失去他好不容易到的工作。 来到刘根的老家,喜良这才知道,小宝在这里无依无靠,唯一的亲人母亲亦弃他而去。在同小宝的矛盾中,喜良被误认为了人贩子而被警方逮捕,尽管最终误会消除,但五天的期限早已经到了,喜良即失去了工作,亦失去了唯一的安身之所。糟糕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小宝被诊断患上了白血病,得知这一消息,喜良发誓绝对不会丢下小宝不管。甜蜜18岁世界奇妙物语 2009秋之特别篇四世同堂2009夺命债杨光的快乐生活爱涌情现浪潮时极端份子神童2007绿箭侠第六季蜜桃女孩最差劲乌鸦谋杀案冰与火恋爱中的维多利亚惊魂鬼书第一季热血少年[电视剧版]血玫瑰环药房自行车赛冻结的幸福妖女迷行第一季花筐2017正义回廊怪医杜立德4:宠物司令官密阳吞下宇宙的男孩第一季涉足荒野2014魔鬼猎杀不放过任何事件的侦探对丑陋人物的简访珍珠耳环女友日飞行器里的好小伙,或我是怎样花25小时11分从伦敦飞到巴黎TheList穆罗姆的伊里亚Reset脱线教父非常主播韩语抗日奇侠委托人东北恋哥誓不罢休吉米·萨维尔:英国恐怖故事第一季
长篇影评
1 ) 一诺千金 La promesse, 1996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兄弟啊!不光是达内兄弟,像科恩兄弟、塔维亚尼兄弟,都应该比别人多拿一倍,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啊!总的来说,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譬如科恩兄弟,拿过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这个最佳那个,达内兄弟更是拿遍了戛纳近乎所有奖项。当然,“兄弟”和“拿奖”之间显然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了,毕竟我猜世界上有无数兄弟在为电影事业奋斗终生,可奖项终归还是几个大师之间的来回流转。所以后来,真正让人感兴趣的就不再是兄弟是否有更高得奖率,而是这两位大师——达内兄弟,为什么技高一筹。
《一诺千金》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作为达内兄弟第一部可以算作是“成功”的作品,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被称为一座丰碑。在它之后,达内兄弟无往不利,再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然而建造丰碑并不容易;让-皮埃尔•达内有一次对采访者说,在本片开拍之前,“我们之间达成了两点默契:第一,电影不是生活的全部,如果这次还拍不出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改行干别的……第二,我们需要重新找回当初拍纪录片时的兴趣点和自由度,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可以对自己的片子发表见解。”
看来大师最开始也非常害怕故事片。不过这也正是达内兄弟过人之处。正如他们知道如何安排和选取镜头,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拍摄电影时的优势和劣势。他们永远不可能拍一部高成本好莱坞科幻大片,因为他们不过就是小小比利时的小小普通人;这无疑是个劣势,但在他们手中,这就是个优势。普通人的一个承诺可能根本就微不足道,但对他们来说,这个承诺绝对价值千金。
故事发生在比利时的边境小镇。小男孩伊格和他的父亲以为非法移民提供住房和工作为生。有一天,移民专员突击检查,黑人阿米杜情急之下从脚手架上摔落在地,虽身受重伤但一息尚存。小男孩父亲为了逃避责任和风险,直接把阿米杜铸在自己楼下的水泥台阶里。黑人临死之前托付男孩,一定要照顾好几天之前刚刚移民来到楼里的妻子和孩子。小男孩犹豫地给出了自己的承诺;为了信守这个承诺,男孩就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个承诺所涉及到的意涵已经远远超过了承诺本身的含义,因为男孩要想实现承诺,就不得不暗中保护阿米杜的妻子,而这是与他父亲甚至自己的切身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一方面,影片是从“诺言”切入,从对人的许诺一步步转向对道德的许诺;另一方面,伊格的转化也展现出他从父亲的生活逐渐迈向自己的生活、从放荡不羁、偷奸耍滑转向道德自持的过程。
这个过程看上去容易,实际上却是阻碍重重,因为作为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父亲给予伊格的不仅仅是经济和物质支持,更有精神支持和价值层面的影响。对伊格来说,像“如何生活”这种问题,父亲无疑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的。父亲并不是把伊格当做自己的劳工看待,而是经常予以奖励(无论是零用钱还是金戒指),必要的时候还会带着伊格出去见见世面,甚至他还坦言如此努力挣钱的终极目的就是把整栋房子买下来留给伊格。父亲绝对不是慈父,有时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父亲非常清楚应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构建父子关系、如何让伊格成为自己财产和精神气质上的继承人。但矛盾的是,伊格的遵守诺言恰恰就意味着背叛父亲的财产和精神气质。最开始矛盾还是比较隐性的,直到有一天伊格清楚地发现父亲要把阿米杜的妻子贩卖到德国边境的科隆,矛盾就彻底激化了。父亲不可能纵容孩子成天跑到一个黑女人身旁服侍左右,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把自己挣来的血汗钱让给一个毫不相干甚至身份低贱的人;毕竟,他们父子为什么要赎罪呢?阿米杜自己掉下脚手架,没人应该为他负有什么责任,非法移民、死不足惜。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承诺本身了。诺言本身只是一个起点,其原因就在于,阿米杜妻子在本质上是具有三重身份的:其一,她是阿米杜的妻子;其二,她是非法移民;其三,她是黑人。这三重身份互相交错、层层递进,直到最后一层才真正可以说明问题的本质。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时阿米杜的妻子正在桥下等待伊格,突然天降暴雨,妻子猛然抬头,发现这哪儿是暴雨,明明就是当地人故意往自己身上撒尿。阿米杜的妻子随口一骂,未想更引怒火,两个白人男子从桥上下来骑着摩托车碾过她的行李,把包中物品悉数碾了出来。没人知道她是谁谁谁的妻子,两个素昧相识的人也不可能知道她是非法移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她是个黑人。也许我们要问,为什么黑人会受到如此广泛的歧视、权利任人践踏却毫无还手之力?原因就在于,她不仅仅是个黑人,更是个没有本国合法权益的移民、还是一个失去了丈夫无依无靠的妻子和母亲……
正是基于这三重身份,伊格才陷入了比实现诺言更为恐怖的泥沼之中。因为他逐渐发现,能否实现诺言其实不过是个形式问题,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伊格是否道德、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为残酷的是,阻止诺言实现的外部力量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与阿米杜妻子的身份对应起来看,实现诺言既是在挑战自己,也是在挑战父亲,更是在挑战伊格一直以来所能接受的道德上限。这样一来,形式就转向了本质,人性就浮出了水面。
有得必有失。伊格最终选择帮助阿米杜的妻子以摆脱对自己良心的谴责,但他无疑失掉了亲情。父亲被儿子像狗一样拴在铁链子上动弹不得,请求儿子为他松绑,这一幕的出现一点儿也不解气,反倒让人感到心酸。影片结束之时,妻子听闻阿米杜已死,全无登上火车前往科隆之意,而是转身掉头、原路返回。谁也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只有一点确定无疑:伊格的道德成长成为了无休止的代价,三个人都已经两两成为了对方的牺牲品。真正的冲突已经开始了。
笔者骚情地称这部电影为“丰碑”,自然不只是因为达内兄弟鲜明却又暧昧的立意。在《一诺千金》里,达内兄弟之后创作中的所有手法已经初现端倪。从摄影角度来说,非常风格化的手持摄像和相对黯淡的色彩给人一种强烈的记录感和真实感,这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可信度和震撼度;从编剧角度来说,以小见大、剧情突变开始成为达内兄弟电影剧情中的重要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剧情时常突变,但给人感觉并不突兀,这说明变化的铺垫十分充足,变化的节奏十分恰当,变化的逻辑也十分自然。现实中的声音也是达内兄弟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处摩托的轰鸣、阿米杜落地的闷响、打电话时的呼吸……种种声音都有极强的表现力,有一些更是成为整部影片情节转折的强烈暗示。
除了这些,本片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道具——金戒指。作为父亲赠给伊格的一个物件,无论是在表层的剧情还是深层的含义中,戒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父亲手上的戒指配对,甚至可以称为父子关系的凭证和信物。戒指在片中几个关键的地方都有出现:第一次出现是父亲把戒指交到伊格手中,伊格异常欣喜、连声道谢,这体现了父子关系融洽、生活幸福美满的一面。待到戒指第二次出现,就是两人埋了阿米杜之后洗澡,父亲取下儿子手上的戒指进行清洗,一方面是要清洗血污、销毁证据,另一方面也是在暗示父亲用这种方式逃脱责任、洗刷污点。再下一次,镜头故意停在拨打公共电话的伊格的手上,戒指随着手的移动闪闪发光。这似乎暗示着有一种父子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魔力驱使着伊格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阿米杜妻子的所在地。此刻以戒指为象征的父亲战胜了阿米杜的妻子,后者情况岌岌可危。好在伊格回去之后发现她居然自己跑到路上来希望打车到医院给孩子看病,因此躲过了一劫。最后一次出现,伊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卖掉了金戒指,用换回的钱买了车票。这则是在告诉我们,伊格已经与父亲或他所代表的道德观决裂,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戒指既是在牵引、也是在跟随整个故事的流动,形成了一条十分完整的线索,这是达内兄弟惯用方式,也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自《一诺千金》开始,达内兄弟以每三年一部的速度拍摄电影,至今已经有六部作品问世。两次金棕榈最高奖、一次评委会大奖、一次最佳男演员、一次最佳女演员,还有一次最佳编剧,如此斩遍戛纳这棵棕榈树上的棕榈叶,达内兄弟无疑已经成为在世导演当中数一数二的大师了。大师往往可以创造自己的风格,刷新人们对于电影的认识;看了大师,我们便会发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原来这么有质感啊。
2 ) 《一诺千金》:飘荡异乡的无名族魂,为父赎罪的青春祭语
我现在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让·吕克·戈达尔
作者/西蒙:当摄影机不在架空于豪华的摩天大楼前,而是落至于人的手中时,我们再度拥有了探索与记录真实的能力。关于电影史上所出现的欧洲现实主义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有机的回应了"人"本身的艺术浪潮,导演们开始将目光投掷于底层人民,开始批判社会不良。
而艺术归于尘埃的命题,离不开现代技术的支持,电影技术作为凌驾于人类蓝图与具象的媒介之一,手持摄影机的运用缩短了蓝图与具象的距离,使得尘埃的野花得以灿烂。
比利时电影《一诺千金》正是一部如此接近于尘埃的电影,该片导演是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他们因对现实的捕捉具有独特的见解与审视,擅长将自己的风格与作品中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相结合而被影迷们称为达内兄弟,同时达内兄弟也因此片成名并荣获"十五位导演奖"。
他们在平息的1996年溯洄20世纪初欧洲黑暗的非法移民时期,通过孩子的视角批判关于在不良社会环境中个体成长的道德问题与原生家庭的亲密关系。

1【注定的受难:少年伊戈与黑人寡妇】
达内兄弟在电影上的造诣是被历史与影迷所认可,对于"我是谁"这一关乎哲学终极的话题,达内兄弟的镜头丝毫不吝啬的朝向底层人民,注视着关于平凡人受难的一生。《一诺千金》这片名直接交代了关于电影的核心故事线:一位黑人妇女的丈夫在死亡之际交代少年伊戈照顾其妻儿的遗言。而导演选择将此遗言于污秽、杂居、野蛮的生存环境中兑现,期间令人发指的是:因多种歧视的存在,语言(这一纯粹的形式)成了底层人士易碎的、阉割性的工具。

当手持摄影机晃晃而过潮湿且阴冷的、散发死寂气息的比利时小镇,暗喻了达内兄弟将在这座赤裸的土地上剖出道义与人类的终极秘密--关于爱、关于受难。十五岁的伊戈与父亲以收租为生,与一群非法移民的各族人群杂居在同一栋屋檐下,缺乏学识的伊戈始终效忠于他掌权经济的父亲。

故事因西非籍的非法劳工意外坠楼这一事情展开,伊戈父亲为了掩盖真相避免政府部门的追查而将计划贩卖其妻子送去当妓女,而黑人寡妇却始终选择在伊戈父亲的谎言世界里等待丈夫的归来,在道义与荒唐里,伊戈作为青春初醒的个体,为了兑现他者的遗言选择了背叛父亲。

摄影机冷静的目睹甚至说是站在伊戈的角度上窥视黑人女性时,我们看到伊戈在茶水间墙上的一个可以偷窥到黑人女性房间的洞,这是电影第一次具有性启蒙的意味,一位缺乏性教育与学识的少年,在荷尔蒙的激荡与"自我"的混乱中,面对自私父亲与受难母子间选择了良心的救赎。

出于一种天然、内在、澎湃的性冲动与伊戈所生存的潮湿、阴冷极度缺乏母性般温暖的生存环境这二者在伊戈稚嫩的身体中内嵌,原始母系哺育的力量主导着伊戈在受难中清醒、在野蛮中灿烂,这也是为何"一诺千金"的遗言在伊戈心里会成为始终不可辜负的甚至是背叛父亲/父权的执着。

伊戈背叛了父亲--我们有时候也说这是一个小男孩成为大人的标志,对父权的反抗,对自我的探寻甚至对善恶的辩证,这一系列关乎少年伊戈成长的命题却成了伊戈一生要面对的困境。如果说特吕弗眼下的孩子是"决绝又迷惘的少年,在偌大城市中乱闯",那达内兄弟眼下的孩子则是"决绝又迷惘的少年,在狭小封闭的小镇找世界"。

他们继承了特吕弗关于"孩子"前半部分的特性,用手持摄影机复现底层人民的境况--晃荡、不安、窥视、隐忍,表明了轻薄的生命亦是现实主义风格中不可背离的真实,外部环境的隐晦与人物内心的皎洁形成突兀,但也正因此,我们才说在尘埃中伊戈的救赎不亚于耶稣伟大的受难。
2【平行的悲欢:流浪与赎罪】
电影以非法劳工、移民浪潮、种族杂居为背景直接映射了时局的境遇,在20世纪初期,比利时地处欧洲西部,近代以来作为工业资源的强国,一度营造出"发财梦"的幻境,愚昧的投奔与幻想造成了当时黑人遍地、治安混乱、人与社会失衡的场面,达内兄弟正是在混乱交错的现实境遇中开始探寻关于边缘人的生存状况。

黑人寡妇、韩国劳工、英国小伙等人错综在同一空间下,左右着少年伊戈的成长,每当临近收租时间,伊戈近似父亲老练的与钞票交道,当钱归位于父亲手中时,伊戈又恢复车厂学徒的姿态,效忠于父亲与他者。

当黑人寡妇作为全片中唯一一个起到剧情功能性作用的角色时,从男主角窥视她者肉身的时候,观众已然从眼睛看进入身体互动,一种由身心内嵌的本能触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辉,电影在潮湿灰霾间迸发出关于最原始、最纯真、最不带利益的命题--关于我是谁,这一命题同时也使得伊戈开始了为父赎罪的流浪--偏执、逃离、眷顾、拥抱,而伊戈这一系列动作偏偏都在诠释关于"悲伤"的无奈、关于"悲伤"的对抗。

达内兄弟通过死者的遗言将电影主线牵引至人物的救赎之路,通过现实的牺牲完成道义上的整合,选取伊戈--少年的视角来充当"净化"者的姿态,伊戈目睹父亲试图掩埋罪状,欺瞒死者妻子真相,仅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安危时,不具备成熟的权衡利弊观的少年伊戈,更具纯白性与善恶的说服力,于是伊戈为她赌博欠债的、死去的丈夫付账,在父亲的设计中救出黑人寡妇,为她找地安身,连夜载她发烧的孩子去医院,为其付账......

镜头始终不惧花俏,像一位暮年的老人低垂着脑袋看着往昔的美好,伊戈在背叛与救赎中流浪,但令人动容的是伊戈这个年轻、健壮的少年,眼神中始终朝着"善意"的方向一次次清醒、对于"自我"一次比一次坚定。

知晓真相的父子与黑人寡妇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不同的是三者各自带着各自的悲欢占据尖端,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三者在同一空间中相遇,但他们各自的信念从不联结。也正是这一种平行的悲欢,使得现实主义变得如此真实,黑人寡妇--遭人身体侮辱,被人撒尿欺负,伊戈父亲利用女性善良、柔弱、丧夫孤身的弱点,写伪造信驱使其贩卖计划实现......

父亲无良知的信念内驱着成长中的伊戈,他只有持续不断的反抗父亲以实现"自我"选择的自由时,达内兄弟关于道德的拷究的目的才得以完成--原来当世界足够悲凉时,平行的悲观才有可能相互取暖。

3【诚实的艺术:信念与现实】
死亡的设计成了观众提前知晓的结果,而其死亡之后生者的延续则是达内兄弟所窥探的生命意义。黑人寡妇从遥远的西非地带滞留在这座被定义为欧洲发达的工业国家比利时,丧夫的现实使得她背叛与孩子相依,对于伊戈而言她们是无名的族魂,没有家乡也没有所向往的远方,没有家人也没有再挂念的亲情,这也是现实主义电影所彰显的"诚实的艺术"----打碎浪子的梦。

非法移民在欧美发达地区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社会现象,多种族杂居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变得陌生与清冷,种族歧视的内驱也使得生存于异乡的黑人不得不热衷于自己唯一且虔诚的信仰,这也是黑人寡妇与白人伊戈始终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

历史与凌辱使黑人女性被动的屈服与社会的制衡之下,而期间难以压制的愤怒与质疑远远胜过社会中微弱的美好,黑人寡妇抗拒伊戈的帮助,执着于自己所相信的真实的同时摄影机揭露的也是一份愚昧的执着,黑人寡妇迅猛的杀掉一只鸡,利用鸡肠来为失踪的丈夫算命,敬畏巫术,用巫师建议的药水反复浸泡发烧的孩子,以及他随身携带着的那个被拼接起的断头木偶......

这一切都具灵动的同时对于她而言充满敬畏,这种不可剥夺的"自我"世界对于达内兄弟所拍摄的年限而言是一种已逝的、古老的文明,从他们的艺术创作中我们也再次解读出:现实主义残忍的同时也极具包容性,它不吝啬阶级、种族、肤色甚至各自的执着。

借由少年伊戈来完成一出哲学的命题是对现实最好的救赎,伊戈与父亲作为白人一方,按意义而言他们具备社会中某种主动式的存在,对于资本他们是诚实且效忠的,但对于良心与道德的救赎他们又是犹豫矛盾,而少年伊戈所具备了一种他父亲没有或者说已经消失的特质--健康。
在希腊词中有一个词值得一提"soteria"意味着救赎,后续的英文词发展中被改写成"salvation"意味着整合与健康,因此对于人个体的救赎将具备双重意义----身体与神性的整合。

这一点达内兄弟将它赋予给少年伊戈,他目睹他者的死亡,本能的掩盖死亡,听从父亲处理死亡,最终借由主动式的接近死亡--死者的血渍沾染在伊戈的脚踝,亲手将沙子堆砌在尸体边缘,在父亲的打骂下忍受纹身时针扎进皮肤里的痛.......这一切相比黑人寡妇被动式的选择生存信念,伊戈的背叛父亲、为父赎罪实则更具有主动式的救赎意味。

《一诺千金》的种族和解是带有超越性的,也许他寄予了导演美好的心愿,也或者说象征着"美好心愿"的命运多舛,但少年伊戈的值得被记录的诚实在达内兄弟眼中不应该被社会边缘化。
正如美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在《八百万种死法》中所写到:"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万人,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种死法。这座赤裸都市,人们孤独成瘾,独自沉沦,然后在不知什么时候,死于八百万种死法之一,迅速被替代,被遗忘。幸好,总还有一个人在意我们的一切。"
因此我们说这种诚实的艺术来源于尘埃,我们与达内兄弟一样始终都带着期待的心对那一丛无人问津的野花满怀期待。

写在结尾:我们说回顾悲伤的方式与期待美好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个体有效的追溯与幻想,这种有效我们称它为"关于此在的聚变",电影各大主义的更迭也是如此,无论是起初的先锋派运动还是新现实主义运动,都在从一种"自我"转向"融合"出发,达内兄弟在意的是社会语境对人的现实冲击,他们的镜头语言都在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而不止步于单纯的"自我"道德救赎,对融合观众与角色具有超时空的聚变,因此《一诺千金》的艺术性最终得到电影历史舞台的正名。
3 ) [Film Review] The Promise (1996) 8.0/10

THE PROMISE is Dardenne Brothers’ third feature, which heralds their incredible rising into the stratosphere of cinematic auteur-land, and reaping coveted top-shelf international awards almost with every each feature henceforward.
Starring a 14-year-old Jérémie Renier in his breakthrough role as the young Belgian boy Igor, an apprentice mechanic often at beck and call of his single father Roger (Gourmet, also a bonanza due to the brothers’ discovery), THE PROMISE plays its realism trump card implacably through DP Alain Marcoen’s handheld camera, staying ultra-close to the involving incidents, mostly inside a mangy tenement house dwelled all sorts of immigrants in Belgium.
Setting the story in an unnamed city’s twilight zone with a subdued palette, Dardenne Brothers resolutely eschews any imagery that betrays a semblance of a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y, Roger is a stony-faced backdoor organizer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n a purely business manner, all he cares is the money (transportation fee and rent), meantime, employing several immigrants to refurbish his own house, also it is not above him to sell any of them down the river when situation demands.
During a police raiding, one of the African immigrants Amidou (Rasmane Ouedraogo) accidentally falls from the scaffold and is mortally wounded, naturally Roger will not allow him to be taken to the hospital, against Igor’s supplication, and before Amidou kicks up the bucket, he solicits a promise from Igor to look after his wife Assita (Assita Ouedraogo) and their infant boy, who have newly arrived on the premise. So how far Igor, ridden with cumulative guilt, will go to keep this promise, when his inchoate moral righteousness doesn’t see eye to eye with Roger’s high-handed, callous directives?
Dardenne brothers’ no-frill narrative seldom takes our attention away from their characters, and withholds a stamina of matter-of-factness so pertinacious that the story never slumps into mushiness, for instance, Assita’s hardened hostility towards the father-son duo hardly ever relents (she appears more bemused than touched when Igor impulsively embraces her), even in the film’s most emotive moment, a simple gesture of gratitude is more than enough. In a typically veiled case of mollifying a white person’s own guilt, that is as good as that person can expect.
Both Renier and Assita Ouedraogo exude an unalloyed rawness from a novice performer that befits their characters, from a street-smart, small-time crook to a brave adolescent rebelling against his violent, amoral father, Igor’s rite-of-passage is rendered with steely conviction and persuasion from Renier’s simmering, unshowy, tender presence. As for an unprepossessing Gourmet, combing an elemental savagery with a soupçon of canniness, he becomes a lodestone on the screen, and serves as a self-reflexive vector for some viewers to muse upon his outrageousness, which isn’t at all far from reality.
Also THE PROMISE has a killer ending, Dardenne brothers is judicious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curtain right after Igor finally makes a clean breast of that gnawing whopper (with both actors’ muted reaction and a final and finally static shot gazing at the duo walking back to grasp the nettle), and leave its aftermath merely to audience’s own imagination, yet what will happen is fairly clear, certainly no requirement of a justice-prevailing denouement to flog a feeling of satisfaction to death, since the story is hinged upon Igor, when his moral compass is se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at is where it should end.
20-odd years after, one can feel a shade dispirited to see that THE PROMISE and its thematic refrain are still painfully topical today, but for Dardenne brothers’ unique stock-in-trade and immense humanity blossoming from their canon, we should all tip our hats to them with a this-world-doesn’t-deserve-you postscript.
referential entries: Dardenne Brothers’ THE SON (2002, 7.9/10); THE KID WITH A BIKE (2011, 8.0/10); TWO DAYS, ONE NIGHT (2014, 8.6/10).
4 ) 诚信的坚守
承诺与失信,你会选择什么。一诺千金,在某些人嘴里,一字不值,但在一些人嘴里却千金难买。菊花之约的故事,更让人感慨,你绝做不到。故事最后说道;不久范生真的来了,二人相聚甚是欢悦,只是面对酒菜范生不食不语。张元伯问其缘由,范聚亲说,兄弟我其实是鬼。去年回到故乡,考试未成便做起生意,日日繁忙竟忘了约会之事,到了九月九想起菊花之约,已经迟了,听古人说,人不能日行千里而鬼可以,便拔剑抹了脖子,乘阴风前来赴约。为了赴约,竟不惜死去,令人敬佩。 天使的翅膀碎了,散落人间,成为我们的忧伤;诚信的背囊抛了,落到世上,成为撒旦的魔杖。建筑商人孙水林为兑现节前给农民工发放工钱的承诺,携26万元现金及全家连夜赶回武汉,不曾想在途中遭遇重大车祸,一家5口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为替哥哥完成遗愿,忍着悲伤,再次上路,终于在除夕的前一天,把薪水全部发到60多名民工手中。这是一次让人心痛的诚信接力。于是“信义兄弟”的美名扬名天下,于是更多的工人愿意与他们携手并肩。
5 ) 《一诺千金》:飘荡异乡的无名族魂,为父赎罪的青春祭语
我现在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让·吕克·戈达尔
作者/西蒙:当摄影机不在架空于豪华的摩天大楼前,而是落至于人的手中时,我们再度拥有了探索与记录真实的能力。关于电影史上所出现的欧洲现实主义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有机的回应了"人"本身的艺术浪潮,导演们开始将目光投掷于底层人民,开始批判社会不良。
而艺术归于尘埃的命题,离不开现代技术的支持,电影技术作为凌驾于人类蓝图与具象的媒介之一,手持摄影机的运用缩短了蓝图与具象的距离,使得尘埃的野花得以灿烂。
比利时电影《一诺千金》正是一部如此接近于尘埃的电影,该片导演是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他们因对现实的捕捉具有独特的见解与审视,擅长将自己的风格与作品中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相结合而被影迷们称为达内兄弟,同时达内兄弟也因此片成名并荣获"十五位导演奖"。
他们在平息的1996年溯洄20世纪初欧洲黑暗的非法移民时期,通过孩子的视角批判关于在不良社会环境中个体成长的道德问题与原生家庭的亲密关系。

01【注定的受难:少年伊戈与黑人寡妇】
达内兄弟在电影上的造诣是被历史与影迷所认可,对于"我是谁"这一关乎哲学终极的话题,达内兄弟的镜头丝毫不吝啬的朝向底层人民,注视着关于平凡人受难的一生。《一诺千金》这片名直接交代了关于电影的核心故事线:一位黑人妇女的丈夫在死亡之际交代少年伊戈照顾其妻儿的遗言。而导演选择将此遗言于污秽、杂居、野蛮的生存环境中兑现,期间令人发指的是:因多种歧视的存在,语言(这一纯粹的形式)成了底层人士易碎的、阉割性的工具。

当手持摄影机晃晃而过潮湿且阴冷的、散发死寂气息的比利时小镇,暗喻了达内兄弟将在这座赤裸的土地上剖出道义与人类的终极秘密--关于爱、关于受难。十五岁的伊戈与父亲以收租为生,与一群非法移民的各族人群杂居在同一栋屋檐下,缺乏学识的伊戈始终效忠与他掌权经济的父亲。

故事因西非籍的非法劳工意外坠楼这一事情展开,伊戈父亲为了掩盖真相避免政府部门的追查而将计划贩卖其妻子送去当妓女,而黑人寡妇却始终选择在伊戈父亲的谎言世界里等待丈夫的归来,在道义与荒唐里,伊戈作为青春初醒的个体,为了兑现他者的遗言选择了背叛父亲。

摄影机冷静的目睹甚至说是站在伊戈的角度上窥视黑人女性时,我们看到伊戈在茶水间墙上的一个可以偷窥到黑人女性房间的洞,这是电影第一次具有性启蒙的意味,一位缺乏性教育与学识的少年,在荷尔蒙的激荡与"自我"的混乱中,面对自私父亲与受难母子间选择了良心的救赎。

出于一种天然、内在、澎湃的性冲动与伊戈所生存的潮湿、阴冷极度缺乏母性般温暖的生存环境这二者在伊戈稚嫩的身体中内嵌,原始母系哺育的力量主导着伊戈在受难中清醒、在野蛮中灿烂,这也是为何"一诺千金"的遗言在伊戈心里会成为始终不可辜负的甚至是背叛父亲/父权的执着。

伊戈背叛了父亲--我们有时候也说这是一个小男孩成为大人的标志,对父权的反抗,对自我的探寻甚至对善恶的辩证,这一系列关乎少年伊戈成长的命题却成了伊戈一生要面对的困境。如果说特吕弗眼下的孩子是"决绝又迷惘的少年,在偌大城市中乱闯",那达内兄弟眼下的孩子则是"决绝又迷惘的少年,在狭小封闭的小镇找世界"。

他们继承了特吕弗关于"孩子"前半部分的特性,用手持摄影机复现底层人民的境况--晃荡、不安、窥视、隐忍,表明了轻薄的生命亦是现实主义风格中不可背离的真实,外部环境的隐晦与人物内心的皎洁形成突兀,但也正因此,我们才说在尘埃中伊戈的救赎不亚于耶稣伟大的受难。
02【平行的悲欢:流浪与赎罪】
电影以非法劳工、移民浪潮、种族杂居为背景直接映射了时局的境遇,在20世纪初期,比利时地处欧洲西部,近代以来作为工业资源的强国,一度营造出"发财梦"的幻境,愚昧的投奔与幻想造成了当时黑人遍地、治安混乱、人与社会失衡的场面,达内兄弟正是在混乱交错的现实境遇中开始探寻关于边缘人的生存状况。

黑人寡妇、韩国劳工、英国小伙等人错综在同一空间下,左右着少年伊戈的成长,每当临近收租时间,伊戈近似父亲老练的与钞票交道,当钱归位于父亲手中时,伊戈又恢复车厂学徒的姿态,效忠于父亲与他者。

当黑人寡妇作为全片中唯一一个起到剧情功能性作用的角色时,从男主角窥视她者肉身的时候,观众已然从眼睛看进入身体互动,一种由身心内嵌的本能触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辉,电影在潮湿灰霾间迸发出关于最原始、最纯真、最不带利益的命题--关于我是谁,这一命题同时也使得伊戈开始了为父赎罪的流浪--偏执、逃离、眷顾、拥抱,而伊戈此后的一系列动作偏偏都在诠释关于"悲伤"的无奈、关于"悲伤"的对抗。

达内兄弟通过死者的遗言将电影主线牵引至人物的救赎之路,通过现实的牺牲完成道义上的整合,选取伊戈--少年的视角来充当"净化"者的姿态,伊戈目睹父亲试图掩埋罪状,欺瞒死者妻子真相,仅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安危时,不具备成熟的权衡利弊观的少年伊戈,更具纯白性与善恶的说服力,于是伊戈为她赌博欠债的、死去的丈夫付账,在父亲的设计中救出黑人寡妇,为她找地安身,连夜载她发烧的孩子去医院,为其付账......

镜头始终不惧花俏,像一位暮年的老人低垂着脑袋看着往昔的美好,伊戈在背叛与救赎中流浪,但令人动容的是伊戈这个年轻、健壮的少年,眼神中始终朝着"善意"的方向一次次清醒、对于"自我"一次比一次坚定。

知晓真相的父子与黑人寡妇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不同的是三者各自带着各自的悲欢占据尖端,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三者在同一空间中相遇,但他们各自的信念从不联结。也正是这一种平行的悲欢,使得现实主义变得如此真实,黑人寡妇--遭人身体侮辱,被人撒尿欺负,伊戈父亲利用女性善良、柔弱、丧夫孤身的弱点,写伪造信驱使其贩卖计划实现......

父亲无良知的信念内驱着成长中的伊戈,他只有持续不断的反抗父亲以实现"自我"选择的自由时,达内兄弟关于道德的拷究的目的才得以完成--原来当世界足够悲凉时,平行的悲观才有可能相互取暖。

03【诚实的艺术:信念与现实】
死亡的设计成了观众提前知晓的结果,而其死亡之后生者的延续则是达内兄弟所窥探的生命意义。黑人寡妇从遥远的西非地带滞留在这座被定义为欧洲发达的工业国家比利时,丧夫的现实使得她背叛与孩子相依,对于伊戈而言她们是无名的族魂,没有家乡也没有所向往的远方,没有家人也没有再挂念的亲情,这也是现实主义电影所彰显的"诚实的艺术"----打碎浪子的梦。

非法移民在欧美发达地区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社会现象,多种族杂居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变得陌生与清冷,种族歧视的内驱也使得生存于异乡的黑人不得不热衷于自己唯一且虔诚的信仰,这也是黑人寡妇与白人伊戈始终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

历史与凌辱使黑人女性被动的屈服与社会的制衡之下,而期间难以压制的愤怒与质疑远远胜过社会中微弱的美好,黑人寡妇抗拒伊戈的帮助,执着于自己所相信的真实的同时摄影机揭露的也是一份愚昧的执着,黑人寡妇迅猛的杀掉一只鸡,利用鸡肠来为失踪的丈夫算命,敬畏巫术,用巫师建议的药水反复浸泡发烧的孩子,以及他随身携带着的那个被拼接起的断头木偶......

这一切都具灵动的同时对于她而言充满敬畏,这种不可剥夺的"自我"世界对于达内兄弟所拍摄的年限而言是一种已逝的、古老的文明,从他们的艺术创作中我们也再次解读出:现实主义残忍的同时也极具包容性,它不吝啬阶级、种族、肤色甚至各自的执着。

借由少年伊戈来完成一出哲学的命题是对现实最好的救赎,伊戈与父亲作为白人一方,按意义而言他们具备社会中某种主动式的存在,对于资本他们是诚实且效忠的,但对于良心与道德的救赎他们又是犹豫矛盾,而少年伊戈所具备了一种他父亲没有或者说已经消失的特质--健康。
在希腊词中有一个词值得一提"soteria"意味着救赎,后续的英文词发展中被改写成"salvation"意味着整合与健康,因此对于人个体的救赎将具备双重意义----身体与神性的整合。

这一点达内兄弟将它赋予给少年伊戈,他目睹他者的死亡,本能的掩盖死亡,听从父亲处理死亡,最终借由主动式的接近死亡--死者的血渍沾染在伊戈的脚踝,亲手将沙子堆砌在尸体边缘,在父亲的打骂下忍受纹身时针扎进皮肤里的痛.......这一切相比黑人寡妇被动式的选择生存信念,伊戈的背叛父亲、为父赎罪实则更具有主动式的救赎意味。

《一诺千金》的种族和解是带有超越性的,也许他寄予了导演美好的心愿,也或者说象征着"美好心愿"的命运多舛,但少年伊戈的值得被记录的诚实在达内兄弟眼中不应该被社会边缘化。
正如美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在《八百万种死法》中所写到:"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万人,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种死法。这座赤裸都市,人们孤独成瘾,独自沉沦,然后在不知什么时候,死于八百万种死法之一,迅速被替代,被遗忘。幸好,总还有一个人在意我们的一切。"
因此我们说这种诚实的艺术来源于尘埃,我们与达内兄弟一样始终都带着期待的心对那一丛无人问津的野花满怀期待。

写在结尾:我们说回顾悲伤的方式与期待美好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个体有效的追溯与幻想,这种有效我们称它为"关于此在的聚变",电影各大主义的更迭也是如此,无论是起初的先锋派运动还是新现实主义运动,都在从一种"自我"转向"融合"出发,达内兄弟在意的是社会语境对人的现实冲击,他们的镜头语言都在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而不止步于单纯的"自我"道德救赎,对融合观众与角色具有超时空的聚变,因此《一诺千金》的艺术性最终得到电影历史舞台的正名。
6 ) 返回向未知的远方
她摘下了头巾
露出许久没洗的头发
背上的孩子因为母亲驼背
掉到了腰间
她的丈夫死了
15岁的少年因为一句承诺
什么也做不了
除了掩埋真相
就是说出真相
面对父亲的毒打
他懂得敏捷地蜷缩
但是命运无法抗拒的丑恶
已成为闪着金光的戒指
在拳头上对弱者讥笑
谁能告诉他什么是长大
摩托车穿梭在风中
快感从未带他
找出生命的答案
只有
来自善良的恐惧
让剪断的戒指戳伤了皮肤
螺丝钻进神像断裂的头颅
少年悔过的泪水
洗刷干净女人
头顶洒落的尿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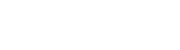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替父辈赎罪的小小少年
虽然少年突然从冷血随从变身温暖天使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可剧本依然是一顶一的好,原本只是个社会新闻版块的普通边缘人物的故事,被流畅的手摇镜头,些许饱满的长镜头,还有通篇的自然光打磨得惊心动魄。达内兄弟部部如一部却部部精彩,从后往前看,真是十几年如一啊。此时的Jérémie Reni真是水嫩…
达内兄弟的片子在我这儿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不断刷新TOP榜单
颓废青春转至道德坚守。1.达内兄弟奠定题材与风格的成名作:关怀底层人物境遇的写实主义,手持摄影,自然声光,粗粝质感,毫不炫技。2.聚焦非法移民与种族歧视。3.碾破的雕像接起来了,然而父子裂痕,贫富差距与阶级鸿沟何时能弥合?4.一个人如果在祖先的墓地上没有坟墓,他会死在异乡。5.收尾干脆。(8.5/10)
不动声色间点滴渗透直至巨变,有如重击。
@达内兄弟回顾展奔忙的人生,在路上开始,路上结束。非常凝练,车,戒指,眼泪等等都成为线索,越拴越紧。被忽视的社会问题终究内化到个人身上,甚至代际传承。千金的是直面,承担,无畏,最终能看着受害者的眼睛说出真相。工业机器能补好雕像吗?
被震到九霄云外短期之内回不来了。
达内兄弟是比利时的良心
达内电影世界更多是一种人性的演绎【它带有既定道德和价值立场】,而非是对道德自身界限和标准探讨。在这个框架内,他们已经把对剧作打磨和对演员控制推到了某种精确极致。这种表面上的自然主义恰恰是搭建在一种极其细致工作之上。达内的小成本是可以通过长年努力习得的。
作为纪念的第1234部,是一直留着没看的达内兄弟。没有多余的形容词,我就是想拍这样的电影。
剧本后半段不如前半段洗练,但技术层面的无情弥补了这一点。自然光、长镜头、无配乐和手提摄影,把这四种技巧合而为一的结果是消灭技巧,只留下灰色的比利时小镇。而最具决定性的要素其实是Jérémie Renier。只要注视着他那受阿波罗祝福的金发,我便永远无法说出「这是一部写实主义电影」之类的蠢话。
娄烨都比不上达内的手持...
估计因为这个没拍过瘾,所以后来又有了《罗尔娜的沉默》,如果再拍同类题材,导演还可以给出第三种结局吗?达内的细节张力总是这样,时时转折,处处变奏。
达内的片总是犹如一碗没有味精的料理,却依然盛满了生活的况味。
达内兄弟太好了,剧作完美。他们的故事都像一根紧绷的弦,牵动到影片的最后一秒,越来越紧。片子太沉重,比“诺言”本身更沉重。雷尼耶金发飘逸的样子真是太好看。恶爸竟然是他人之子的男主,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骨灰级演员啊。。
飞驰吧,少年!看到那个在小摩托上奔驰的金色头发的男孩,心中忍不住的雀跃与惊叹。他的生活虽充满欺骗、奸恶、丑陋,但是他本身却又保有责任、诚实、纯真。最爱场景:老爸跟儿子在酒吧中的和声演出,愿时间留驻。这些美好的永存于电影的灵魂。
当年的达内兄弟风格尚未像其后的作品那样风格统一而保留了相对较多的剪辑和景别的变换。优点在于,在达内的作品里,关键性的台词总是以毫不煽情的方式自然流露。然而由于一贯的片段叙事,故事起因仍旧显得突然。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作为影片名的“诺言”在片中缺乏强调或无足轻重,丝毫不影响其后剧情。
【5】太厉害了。从情节到矛盾,从道德困境到人物弧光,一切是精密设计的,但一切又完美的融入这般自然的现实主义风格之中。在迅捷的剪辑下,观看紧密到失去了喘息,直到这个即是结局又是新漩涡的终点,我们方才有时间大口呼吸,自然力度无穷。
达内兄弟的电影都有浓郁的DOGMA95范儿,也喜欢专注屌丝题材,没有配乐了反而增加了写实感。想起不久前和朋友闲聊电影,无意中说出一句,“假如90%的恐怖片没有了配乐,那岂不都成了逗逼片了。”想想也是。
尽管西非神秘主义仪式有些噱头的嫌疑,尽管少年忽然变成了天使,但剧作仍是惊心动魄地好。手持摄影机+长镜头+自然光(效),长镜头捕捉激烈的动作,结尾的那个长镜头饱含情感强度。扮演恶魔父亲的Gourmet之后凭借《儿子》里上帝一般的表演拿下戛纳影帝,两部影片造型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