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夏洛特(英格丽·褒曼)是某乐团杰出的钢琴演奏员,她的女儿伊娃(丽芙·乌尔曼)是一名在农村社区工作的牧师的妻子,两人之间有一道深深的感情鸿沟,七年来不曾有过任何交流。在得知夏洛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伊娃写信邀请夏洛特来同住,两人都试着友好相处,却不免又将往事重提。伊娃怨恨夏洛特没在她童年时给予她足够的爱护,只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疏远了自己和另一个有高度残疾、只能发不清晰的音来与人交流的女儿海琳(莱娜·尼曼)。而夏洛特因为海琳与伊娃住在一起,加上丈夫的去世给自己造成很大打击,也是心情闷闷紧锁眉头。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世界上最美丽的我的女儿西非历险(普通话版)常磐庄的青春坚如磐石双塔克虎口巡航小飞侠(国语版)狼人杀2021选妃记星际旅行6未来之城电玩古咒我心雀跃星际追杀吸血鬼生活远嫁日本辣妹天使幸福在哪里钟馗娘子冰封侠:时空行者国语天崩地裂下秘境星球100万粉丝唐人街探案2深海逃生儿童捕手恋爱汪汪汪最佳拍档2:大显神通(粤语版)七家房客我的奇怪朋友
长篇影评
1 ) 电影中的三人行 | 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在母亲和女儿之间,我们看见最深的恋慕,也捕捉到最了然于胸的讥诮和厌烦。这种亦敌亦友、爱恨交织的情感,比父子之情更浓稠和伪饰。在日常平淡的生活中,女人间特别敏感的心所产生的惊心动魄的交锋,如闪电的强光在柔软的心尖烙下伤痕,带着最残忍的清晰记忆,纵使一辈子也无法黯淡和释怀。如张爱玲,老年在写作《小团圆》时还字字泣血地重现母女间的对峙,对母亲当年并非无条件的、充分的爱耿耿于怀,每枚情感的毒剑都怀藏在心,时常检视。
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正因为我们无从选择出生,无从选择父母,摘下“父子情深”“母子情深”的“和睦”的面具后,其日深月久的拉锯和磨折才愈加显现这宿命般的冷酷。


伯格曼1978年的影片《秋天奏鸣曲》,表现了母女三人的爱恨关系。母亲夏洛特(英格丽·褒曼饰演),是位杰出的乐团钢琴演奏家,大女儿伊娃(利芙·乌曼饰演)嫁给了一位乡村牧师,住在湖畔的牧师住宅里。小女儿海莲娜(莱娜·尼曼饰)从小患病,身体孱弱,住在伊娃家中,只能用破碎的发音和伊娃交流。
伊娃和母亲夏洛特七年未见,母亲在大女儿的重要人生事件里屡次缺席,结婚、生孩子,包括孩子的死亡。对患病残疾的二女儿更是把它像生活的不和谐音般丢到了记忆的旮旯角落。影片以伊娃给母亲写信开头和收束,呈首尾的环状结构。母亲夏洛特在失去丈夫的悲伤中答应前往伊娃的家,既让伊娃喜出望外,又心生困惑:七年了,她这次来到底想要什么?而伊娃的疑问也是一次自问,对自己是否长大成人的一次确证和试探,她是否已经拥有了足够与母亲抗衡的力量?

三人的爱与恨
母女间第一次谈话,是母亲一段直视镜头的自恋自怜的独白:夏洛特看向虚空,镜头剪切到她在病房照看濒死的丈夫,在她博取同情的叙述里从没看女儿一眼。而当镜头转向女儿,女儿伊娃带着困惑和着迷的专注,望着母亲。两人对坐下来,开始交谈,伊娃谈到妹妹海莲娜也在家里期盼和母亲见一面,母亲夏洛特显然吃了一惊,极力掩饰惊慌和排斥,而当出现在小女儿海莲娜门前房间时,母亲已满怀爱和深情。


伊娃充当着海莲娜的翻译,一家人的亲昵交流里,伯格曼轮番给夏洛特、海莲娜特写,两位女儿如我们般观看母亲精湛的似乎无懈可击的动情演出,而一丝亲近的犹豫和眼神的嫌恶将母亲的惊慌失措暴露无遗。母亲体面伪装的热情外表下对亲情的淡漠和疏离,大女儿殷勤、热望的眼神下压抑的委屈与怒火,小女儿感动流泪下是失语和失去母亲卫护的现实。 三人的交锋在一次夜谈里将情节推至最高潮。
伊娃在酒后释放自己,终于袒露了对母亲的爱和恨,她在回忆中回到了孩童时的样子,层层递进地控诉让痛苦和折磨扭曲了她的脸,在利芙·乌曼和英格丽·褒曼教科书般的演技里,伯格曼并不将两位演员同框展现,而是将镜头逼近人物,人物的神情带着纤毫毕现的情感真实,在摄影机的逼视下无从隐藏。
在拍伊娃的特写时,略带仰视的机位,给人压迫感。温顺谦卑的伊娃此时显得傲慢、不容分说地责难,目光冷峻而无情。而给夏洛特的特写里,平视中捎带俯视的特写机位,表露了母亲夏洛特难得的软弱、自责。

“妈妈之所以痛苦是为了让女儿也痛苦。这就像脐带还没被割断……妈妈,我的忧愁难道是你隐秘的愉悦?”
“你说出你的体贴,用关切的语调,没有一个细节可以逃脱你的爱的能量……真实的我丝毫不会被爱或被接受。你着了迷,而我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失去了自我。我说你要我说的话,模仿你的手势。甚至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不敢做回我自己,因为我恨那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你在情感上是个残废,事实是你讨厌我和海莲娜。你的内心是紧闭的,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我爱你,但你认为我讨厌、愚蠢、失败。你伤害了我一辈子,你也同样受伤。所有敏感脆弱的东西你都攻击。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你都扼杀。”
女儿的血泪控诉酣畅淋漓,字字打动人心,像每出家庭里一次假想的爆发,而母亲便能全然接纳吗?


影片中母亲为自己辩解:”我不记得我的父母曾经碰过我,我对任何和爱相关的东西都很无知,温柔、接触、亲昵、温暖,只有通过音乐,我才得以抒发我的情感。”夏洛特原未及伊娃情感的放纵、粗野、不加拣择,夏洛特还是死守着钢琴家的优雅,没有吐露出对女儿真实的想法。伯格曼让英格丽·褒曼躺下来,躺在地毯上,让她的衰老和虚弱在松弛中显现,让她也回到孩童的状况。
影片是话语的海洋,在多数室内的拍摄里,将人物的内心话语显现,情感冲突用话语的交锋来表达,话语、话语、独白、独白。在戏剧高潮性的言语发泄里,我们听到伊娃的呼喊般的控诉而感同深受,这时楼上的小女儿海莲娜像得到心灵感应般,痛苦地扭曲着自己的身体,从床上滚落下来,一路爬到楼梯口,期盼着母亲的关爱和抚慰。她尖叫地嘶吼,妈妈,向母亲求救,而母亲夏洛特正经历着情感的崩溃,口中喊的是“救救我”。母女都是情感溺水的人,无法互相施救。
影片中的三人关系,更多的是伊娃和夏洛特母女两人的关系,海莲娜的失语,只有伊娃能听懂她不完整的发音,这个角色设定带着母女间沟通无望的隐喻。海莲娜在影片中起到点睛的作用,是母女创伤的一记加强音。

三组对位
影片在开始的谢启名单中播放的亨德尔F大调奏鸣曲(作品1号)的第一乐章,橙黄温暖的色彩里奏鸣曲像一双温柔的手拂过,带着爱的美妙和灵动,舒缓而放松。与剧中母女分别演绎的肖邦的第二前奏曲——凄美、哀伤,带着演奏的肃穆,形成音乐上的情感对比。前者是理想中的母女间的情感,是伊娃写信时自然流露的美好期盼和夏洛特劝服自己动身的一个优美的展望,而后者仍将他们拉回到固有的情感模式——

在这出戏里,女儿开始胆怯到后来战战兢兢地为母亲弹奏,始终紧张地注视着乐谱,弹奏完最后一个音符后,像受到震颤般将指尖放到嘴里,惊怖地等待母亲评价/“宣判”。演奏中,镜头轮流转向伊娃和母亲夏洛特,我们看到夏洛特端庄的脸上一闪而逝的不耐烦和否定,表演般的泪流和动容后又是不予置肯的神情。而她的宣判是,哦,她爱伊娃,潜台词里对伊娃错误的演奏有着不容让步的认真。然后她无视伊娃受伤的神情,不由分说地解说乐曲,亲自示范弹奏。镜头用余光关照母亲,重点放在女儿的脸上,这张受伤的脸低视钢琴,再缓缓抬头看神祇般的母亲,目露哀戚,像注视着深渊。母亲的强有力,吞没了女儿卑微无力的演奏,女儿注视着母亲,母亲注视着钢琴,从不看向女儿,女儿在一次次绝望的无声呼喊里沉没。

这里既有两首乐曲带来的情感的对位,也是两种颜色的对位。伊娃从母亲到来之后就穿绿色的衣服(两身装束)或是灰蓝的家居服,而母亲在晚餐时穿的是咄咄逼人的,招摇的红色,“绿色”的伊娃殷勤地服侍着“红色”的母亲,像奴仆般忠心耿耿。然而红色也出现在伊娃的第一个镜头里,伊娃丈夫对着摄影机独白,对伊娃全心全意的爱和不被理解的寂寞,无从了解伊娃内心的叹息。镜头远处伏在钢琴上写信的伊娃,正是一身红裙,是夫妻关系的隐喻,接受更多爱的一方更有恃无恐,往往忽视对方情感上过分的付出。

而另一组对位是情感的代偿,在两代母子感情的处理上形成饶有意味的反差。伊娃怎么在与母亲相处中得到创伤,就如何弥补在她的家庭里。儿子是她心灵休憩的港湾和支柱,弥补了母亲造成的爱的裂缝。然而儿子的早逝,又将她推向真实的深渊。她不得不面对自己丧失爱的能力的茫然现状。

无爱和现实和疗愈的可能
任何形式的爱,都可能给神经症患者一种肤浅而表面的安全感,或甚至是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不相信它,对它表示怀疑和恐惧。他不相信这种爱,因为他固执的相信没有任何人可能爱他。这种不被爱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信念,它不因任何事实上相反的经验而动摇。的确,它可能因为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根本不反映在人的意识里;但即使它模糊不清,它也仍然像它经常被自觉意识到时那样,是一种坚不可摧,毫不动摇的信念。同样,它也可以隐藏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下,表现为一种玩世不恭的傲慢,这样它就很可能令人难以发现。这种不被人爱的信念,极其类似那种不能够去爱的状态;事实上,它正事对那种不能去爱的状态的自觉的反映。显然,一个能够真正喜爱他人的人,自然会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人也会喜爱自己。

这段引用自卡伦·霍妮《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话,为伊娃做了精确的心理注解。伊娃因童年没有被母亲好好爱过,成年的她也总是像孩童时孤单地期盼母亲巡回演出后回到家,期盼着充足的爱和回应。因为不被爱,而不会爱,也不信任爱。她对丈夫言谈间深情的表白,回之淡淡的质疑,“说的很好听,但没有真实的意义。”丈夫说:“当我向伊娃求婚时,她说她不爱我,她说她从未爱过任何人,她不会爱。”
而伊娃丧失爱人能力的现实绝非一次深夜的畅谈就能解决,母女俩还是重新回到两人相处的情感模式里,影片的结尾,海莲娜对母亲的不告而别伤心地嘶吼、大叫。夏洛特逃离这份窘境,在火车上惊魂卜定。而伊娃重回平静后再次给母亲写信,寻求宽宥。平静生活下情感的创伤仍旧狂暴如海。
2 ) 出于本能,我无法感受到你虚伪言语里的爱意
一,你会说情话,比任何人都会说,声音也听起来让人愉悦。
对于女儿希求本能的母爱来讲,语言根本就无法成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没有什么会成为母爱的替代品。甜言蜜语纵然可以赢得一时的讨喜,但是长久以来必不能赢得真诚。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幸福总是在沉默中酝酿自己的甜蜜,无怪乎李尔王会在大女儿二女儿的冠冕堂皇的谎言中走向灭亡,而在小女儿一向朴实的沉默中看到了迟到的真诚。
二,母亲受的伤要由女儿承接
母亲的失败女儿要受累
母亲的不幸就是女儿的不幸
仿佛脐带从未剪断
妈妈 是这样的吗?
女儿的不幸是母亲的胜利
妈妈 我的悲伤
使你暗自快慰吗?
这句话的比喻真是绝了!脐带的输送营养功能将母女关系拉的无比亲密,这也说明母亲自身绵密不断的恨意也在这种亲密关系中被高纯度地输送到女儿身上,而女儿所承受的并不能以德报怨地将枯井生出泉水,这段关系就如此死在这里......而从尊称母亲到昵称妈妈的称呼的转变,台词效果直接拉满!

一些细节及矛盾的层次感:
开头女儿丈夫的眼里满是疲惫,他看过妻子所有的文字,无微不至地爱着妻子,悲哀却又坚定地直视着镜头说:“我想告诉她,她确实是被无条件地爱着的,但是我始终无法用语言说清楚这一点,她似乎无法领会到这一点。”有一种程度,就是深到无法用语言描述,这种境界说是绝境也不为过,因为少有人至,所以语言难以传达这一小部分人的感情。而妻子在这个家庭中却仍在书中说自己没法体味到幸福,因为她的缺陷在早年已经种下了,而他对妻子的认知,也不过是从大学附近开始。
女儿写给母亲的长信里是溢出来的情意与体贴,而丈夫听了只是淡淡一笑,疏于应对。如此体贴的丈夫,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定然是此举已经多到见怪不怪的程度,而信的内容里提到的七年,似乎也为丈夫的冷漠做出了解释。七年的持久战,似乎只是女儿的一厢情愿。
一开头的母女见面亲亲热热,伯格曼好像终于可以做个人发个糖了,但是提到钢琴的时候,女儿只是弱弱地试图分享自己的喜悦,而母亲似乎只是含有竞争仇视的意味,想要在话头上胜过女儿一筹。整个氛围瞬间就不对味了,母女之间的矛盾初次展露。这是母亲方面的挑衅。

而提到海莲娜,母女之间的交锋变得更为直接。母亲直言不想看见海莲娜,但却还是毫无破绽地演好了母亲的角色。而女儿也在饭桌上与丈夫直言从没见过如此虚伪的母亲。双方的矛盾开始显著起来。
这种交锋时而剧烈时而圆滑。女儿与母亲在睡前的谈话便是另一种矛盾:女儿周到地细数着床上母亲所爱的一切事物,而母亲似乎也不厌其烦地提醒女儿还要注意什么。而在这之后,女儿下了楼梯,在楼梯的阶梯之间便坐下来叹气,而母亲也深呼吸后马上转向她的户头清算。表面功夫是一把钝刀子,一把让人缓缓失血致死的放血刀,缓缓流失掉一段关系的活力。

铺垫与高潮:
多段长镜头:
1,女儿看着弹钢琴的母亲,女儿睁开眼表情悲怆地看着母亲,而母亲闭上眼,拒绝接受这份感情。也为后面母亲沉迷钢琴而无视家庭作了铺垫。

2,女儿的长段独白,将之前体现出的所有不和的原因全盘托出,感情浓郁得没有边界。

3,女儿的长段读信,读的是自己,也是母亲内心的独白。镜头在母亲那一扫而过,却在丈夫的冷笑中长久停留,似乎在暗示着结局的走向。我觉得,这一切似乎终究还是太迟了。

三,关于死的最终悲哀
直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母亲对于自己母亲的女性情结,她惧怕母亲的母性,惧怕从其体内产出的婴儿会夺走母亲对自己的宠爱。因此,她便将这一种恐惧投射在自己的女儿身上。但是更深一点讲,母亲对衰老生子各种各样的恐惧,究其原因都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会让人空空的站在原地,放弃生命所有的可能性而一事无成,母亲最终只是一位钢琴家,一位除了钢琴之外便一无所有的苍白的钢琴家,她拒绝成长,拒绝生命给予的多样丰富的感情,没有耐心把信心寄托在爱上,寻求自我一种有安全感的孤独。
3 ) 伯格曼:反人类的人类学家
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导演对人类表达出如此深重的“恨”意。伯格曼的电影无法引致一种爱的原因,看来不只是影像被文本侵占后表现出的干硬,更是他电影中的世界本身便是没有爱的。
在《犹在镜中》中,伯格曼还在探问:“我不知道是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还是爱本身就是上帝?”到了《冬日之光》和《沉默》,他已经进一步确证了上帝的沉默。在《假面》中,上帝的沉默以疾病为隐喻进一步直观地呈示出来。
如果说伯格曼在这个阶段探寻的是“上帝存在于否”,那么在下个阶段他则开始质疑“爱存在于否“这个与人类生活更加密切的命题。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呼喊与细语》中的爱,已经在这个中产阶级家庭内部全面溃败了,艾格尼丝的癌症仍然是一处外在的隐喻。家庭像戴着面具按一套规矩行使责任,将内心的自私和邪恶包藏在日常生活的礼仪之下。唯一的爱,发生在患病的艾格尼丝与女仆安娜之间,这个由非亲情的责任唤起的爱,成为了伯格曼电影中极少几处温暖之光。
到了《秋日奏鸣曲》,爱在家庭内部的缺失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在夏洛特和伊娃这对母女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不断柔化在平素的友好相处中,最终一触即发:这是伯格曼电影中最为残忍的一处场景,摄影机直接对准两位杰出女演员的脸,让她们激烈地为自己辩解,相互指责。在这里,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形式的爱。
我想,电影史还未有另一处场景能像此处的对话这般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它丝毫没有涉及到暴力和血腥,但刀刃却无情地切割在灵魂上,它赤裸裸呈现出人精神最内在的状态。我们感受不到这对母女间哪怕有的一丝丝爱,观众在此成了目击者,目睹到灵魂可悲的困顿状态。而他作为隐藏的旁观者和审视者,被迫触发身上的道德思考。爱在这部电影中彻底消失了。
《呼喊与细语》中爱的消失发生在姐妹之间,并没有涉及血液关系,到《秋日奏鸣曲》中,爱在具有血缘关系的母女间也消失了。如果说连母女间的亲情都已经破败到如此程度,这世间哪里还会有爱呢?当然,还有《婚姻生活》中爱在夫妻间的消退。
伯格曼在此对人类表达了最深重的恨意,探讨的角度从“上帝存在与否”转换到了“爱的存在与否”。正如他在《犹在镜中》设想的,爱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上帝存在的征象。上帝是否存在,我们也许无法探问,这超越了人类的思考能力。上帝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即便上帝存在,它也沉默了,就像它不存在一样。这便是伯格曼在《冬日之光》《沉默》《假面》等电影中着力发展的命题:上帝沉默后,这个世界会怎样?
既然上帝的存在与否无法探寻,在某种程度上爱又让我们相信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对于这种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爱,我们总是可以探寻的吧。于是在此之后,伯格曼从神学转到了人类学,即爱在这个世界存在与否的命题。伯格曼无疑是悲观的,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爱被虚假建构的世界。既可以说这个世界有爱,但这是一套礼俗规训下强制要求人类表现出来的爱,比如发生在姐妹、母女和夫妻间的爱;但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爱,因为这些爱都是虚伪的,并非发自内心。
在此,显示出了作为人类学家的伯格曼的观察视角,一个上帝沉默后,爱接着消失的世界。伯格曼将自己放置在了“反人类”的立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一部电影像《秋日奏鸣曲》一样表现出对人类的恨意,或者在最后母女间激烈交锋时爆发出对爱之消失所感到的如此深广、悲叹的震撼力。
伯格曼要表现的是现代社会人类普遍的精神状态,更准确一点,是他自己所站在的中产阶级。这与安东尼奥尼是一样的,安东尼奥尼同样将批判视角指向了中产阶级。但伯格曼观察到的一直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内部,而安东尼奥尼将触角延伸到相爱的情侣间。这样看来,后者陌生人间的疏离与冷漠远不及前者亲情的破败来得可怕。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只是“爱神病了”,人还在无法交流的状态中保持着想要交流的积极愿想,即便这些举动最终像在古希腊悲剧中发生的那样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但在伯格曼的电影中,爱不仅在夫妻间、同样也在亲人间彻底消失不见。如果这个世间没有爱,不仅不必再谈什么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人作为人存在的价值也被一并泯除了。因此,伯格曼是一位“反人类的人类学家”。就像他的电影中出现的众多疾病隐喻一样,人的灵魂也生病了,而且是不可治愈的绝症,只有死亡在等着它。
4 ) 以爱之名
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母亲,却对她无能为力。她知道在母亲身上索爱无望,却只能沉默顺从,只有猛灌几口烈酒才敢与母亲对质,宣泄积压多年的怨愤和痛苦。伊娃,夏洛特的女儿,乡村牧师的妻子,经历丧子之痛,极度抑郁,以照顾家人为由才能摆脱自杀念头的平凡女性。
这是英格玛.伯格曼影片《秋天奏鸣曲》里的一对母女。伯格曼的彪悍强大是公认的,英格丽.褒曼和丽芙•乌尔曼的对手戏也演绎得精彩绝伦。我想看过的人都会对那组母女演奏肖邦第二前奏曲的经典镜头留下深刻印象:先是一番推却,又找了一大堆借口,伊娃才战战兢兢开始弹奏。沉闷,犹豫不决,泛散当中又有突如其来的冲撞,即使外行也能感觉到琴声带出的情绪。夏洛特的表情也随着音乐变化着,先是绷得很紧的嘴角,略带讥讽,有种面对不可雕之朽木的懊恼和不屑。随后略带惊讶,垂下眼帘,有些温和的气息浮现。最后她闪现了笑容,带着淡淡的无奈。当渴望母亲认同的伊娃忐忑不安问夏洛特是否喜欢自己的演奏时,她说了喜欢,但随即补充说明:“我喜欢你。”(潜台词为:不是你的演奏),将伊娃获得赞赏的惊喜瞬间碾碎。接着是夏洛特在分析肖邦人格与作品之后的示范演奏,她眉梢微挑,闭着眼睛,心无旁骛沉浸其中。而伊娃至始至终瞪大眼睛注视着母亲,表情复杂凝重,交织着惊诧、痛苦、挫败、茫然……种种。
这场演奏者和倾听者互为交换的戏里,伊娃做为演奏者时很少出现在镜头里面,反倒是强调夏洛特的半身特写,正面的脸;而到了夏洛特的演奏,则母女两人的脸部同时出现在镜头里,做了一个巧妙而别具寓意的画面构成特写——前方是半侧面的夏洛特,后面是略微被遮挡住的正面的伊娃,映衬人物的背景是单调干净的白窗纱。
我想这里喻示了母女二人关注点的不同:夏洛特显然关注的只是音乐,在倾听的过程中,她只是做为她自己(而不是母亲的身份),以一种训练有素的专业角度去感受去评价此刻的演奏,而忽略了演奏者。在察觉到音乐里流露出来的某种情绪之后,才将关注点转移到演奏者——自己的女儿身上,并且为之感动。但这样的感动转瞬即逝,她管这叫小儿女的自哀自怜,认为是演奏中应该摒弃的东西,在她诠释对肖邦及其音乐的理解之时如此提及。她可以精确剖析大师矛盾又深沉的内心世界,探索曲谱里不尽的奥秘,却无暇或者不屑于顾及女儿的绵绵哀痛和深切渴望。
伊娃相反。无论是自己弹奏还是听夏洛特演奏,她的关注点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但是在演奏和聆听的转换当中,对母亲的看法和态度同样也在微妙的转换着。弹琴的时候,伊娃像个手足失措的女学生,此刻令她信心全无、惊惶不安的是母亲的社会身份——做为这一行当权威人士的夏洛特。她所渴望得到的认可,也是超越了寻常的亲情鼓励这一个界限吧?不过这又交织在一起的,母亲的形象里就是存在着这一无法剥离的社会面,这几乎占据了母亲全身心和全部时间,令伊娃无法享受到母爱,并自幼受到其压迫。但是,她还是希望得到这一层面上的承认,是因为母亲重视这个,还是因为自我发展的欲求?也许两方面都有,并且难以截然区分。
轮到母亲上场,夏洛特的琴声很有感召力,但是伊娃的心并没有放在音乐上,她专注又绝望地凝视着母亲,明白她已然是在另一个世界里,跟自己无关。后来母女对质的那段回忆里,有母亲练琴,小女孩被关在门外的镜头,在这里其实已经有了前兆。这时,伊娃眼里的母亲已还原到亲缘关系。
当夏洛特意识到自己做为母亲的身份,被女儿所感动并说出喜欢她时,伊娃竟然是失望的。而在伊娃的请求下,夏洛特以钢琴家的身份全心全意投入对作品的演绎之时,伊娃又感受到了与母亲的差距和隔绝之伤痛。影片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了两人之间的流动性错位:在音乐理解上,身份意识上,情感需求上,甚至人生理念的不同。与其说是失之交臂,不如讲就是在两个空间里各自循环着,纵有碰撞却难以融合。
演奏完毕,听了伊娃对母亲和她的音乐从崇拜至极到心生烦倦又回到重新欣赏的一番话,夏洛特拥抱了一下女儿,说希望还在。希望还在,不过对于这两个人,至始至终是两种不同的希望。
她们爱着对方。虽然在矛盾激化的最高潮,伊娃喊出“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是难以想象的最可怕的结合”这样的话语,声讨母女之间剪不断的脐带所带来的施虐和受虐关系,夏洛特也在震惊之中痛哭流涕,追溯自己的童年不幸并乞求女儿的原谅。寻求谅解也是因为爱意尚存,能够感同身受,明白了自己对所爱之人造成的伤害。如果没有强烈的爱,这样的恨意也就没有立足之地。
不过挑明了又能怎样?一切照旧,平缓之后又回到各自的轨迹。皆大欢喜的和解并没有在结局里出现,而是以女儿重新向母亲伸去橄榄枝做为收尾——伊娃给夏洛特写了致歉信,喻示着这样的情感纠结还没完,希望还在,纵使问题没有解决。
也许一生都不可谐调,这对母女两在情感上相互投射与映照。不,是母女三,还有个被病魔摧残兼被母亲遗弃的海伦娜。海伦娜与夏洛特的纠结,其实是更深的一出戏,这个绝对弱势的女儿竟然是母亲的情敌,虽然最终没能争夺过强势的母亲。夏洛特对海伦娜的排斥,绝不仅仅因为女儿病弱的身躯,还有这残损到不堪一击的身体里所蕴含的强韧——对爱的执著追求。这是夏洛特在现实世界里无法面对的东西,因此当她在他人面前公然表现出对海伦娜的怨憎之时,其实也含着对对手的尊敬。
以爱之名,有人占据、支配、索取,也有人牺牲、顺从、无条件付出,其实都是无意识的相互促进。而纠结在强烈的爱憎情绪当中,理解和感受力也必然会扭曲,又如同麻绳,扭曲的绝对不会只是其中一股。荒谬之处在于这股强力之下,依然你是你,我是我,只是纠缠着却永远不可能合二为一。
却也不至于绝望。影片运用了大量的橙黄基调,就连最激烈的矛盾冲突都设置在如此安宁静谧的暖调里,证实了另一种温暖和坚实的现实所在。伊娃的丈夫维克多开篇就以独白的方式表述了对妻子全心全意的爱,伊娃对海伦娜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夫妻二人痛失爱子之后的相互包容和体谅。这些是平淡和日常的,但正是这样的平常支撑起了生活的继续。
5 ) 伯格曼《秋日奏鸣曲》:不幸的家庭总是各有各的不幸
无论是室内的软装颜色,还是室外的黄昏景象,伯格曼都使用了暖色系作以背景。拍摄人物时用了浅焦摄影,把背景虚化成了一团暖光,以此衬托人物。红与绿两种颜色在色相环中呈一百八十度角,距离最远,互为互补色,所以两位主角的红与绿服装色彩早已暗示了情感的分裂,为结尾的爆发做好了铺垫。剪辑上出现了打破时空的平行蒙太奇的叙述,不像早期的伯格曼那样场景固定,舞台感十足,而是有了明确的电影感,不过角色打破第四面墙的内心独白仍然充斥着一些舞台剧味道,但这也使台词极具语言的穿透力。可见伯格曼还是保留了舞台剧的风格。 原生家庭似乎是伯格曼后期创作生涯的重要母题。当成年后的子女个性竖立,有了自己的思考方式,父母当年教育时的弊端便在矛盾之中暴露出来。爱与被爱之间本应该是相互理解尊重的关系,但在主观情绪与另一主观情绪碰撞后,爱变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变成了阻碍沟通的空气墙。你站在任何一个角度上思考都觉得并没有错,因为错的只是矛盾关系本身罢了。真是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
6 ) 《秋日奏鸣曲》:并非宿命的隐藏
你发现就是她毁了你。你的母亲。她用她的理想去塑造你。却不是你。你看不起自己,因为你不如她的所想。你恨她。因为你始终都没有接受自己。你活着,却失去了自己。 这就是《秋日奏鸣曲》里,女儿和母亲的关系。 钢琴家母亲,活力四射、才华横溢,从外表穿着到言谈举止都极至普通全无光彩的女儿。 是一个从来没有树立信心的女儿。小时候,母亲是作为一个陌生的人,练琴,离家巡演,父女两人在家里共享孤独,只有沉默。母亲曾经在一个夏天回来陪她,给她剪头发,带给她书要她读,要她戴牙套,还有,把压抑多年未给女儿的爱一并给她,但是,都是她的角度,她的想法,她从未问过女儿是否喜欢,因为她绝对相信自己,她就是真理。在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在女儿家里,睡不着的两个人回忆起了往事,女儿终于将自己的愤怒一股脑的倾泻出来,其实她烦透了她带给她的一切,说时她的样子那么歇斯底里,母亲惊呆了,我哭得不能自已。 母亲把女儿一点点打碎掉,却塑不出一个新的人。母亲要按她的想法去塑造她,去教育她,只想拿走属于她的,否定她,疏远她。她的自我,在光彩的母亲面前,显得那么不堪。无从建立。这孩子从小敏感,她看出,母亲向来言不由衷,她说爱的时候心里从不爱,她爱的只有她自己。于是她恨她。当有一天一个男人跟女儿求婚的时候,她说,我不爱你,我不爱任何人。因为,她爱的能力是被以爱的名义给毁的,片甲无存。 母亲忙着练琴,母亲有时候也跟她玩,但是她生病或淘气母亲就把她交给女佣。在母亲面前,她只有掩饰、压抑着自己,她渐渐明白的是,母亲只想打压所有的敏感和真实。她那一个不被母亲接受的自我,也被她自己一点点否定,从此,她活着,有如行尸走肉——如果不曾被真的爱过,我们就不知何以树立此生此世生存的信心。 但母亲也是一个受害者,她听了女儿的控诉,想起自己,缺乏温暖和抚爱的童年,她甚至记不起她母亲的脸,也记不起女儿的,她终于明白,自己从未长大,她只有音乐,在那里她才可以尽情抒发感情。因为她的不完整,她关闭了通向女儿的大门。她要求女儿抱一抱她,或是触碰她,但女儿没有动。 女儿写过这样一句话,被一个人爱上,这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是她丈夫最喜欢的句子。事实上,他爱她,他改造了她,女儿终于从压抑封闭的自我里解脱出来,还接来了病得厉害的残障妹妹,全心照顾她,只有她听得懂妹妹咿咿呀呀的话语,但母亲请求宽恕的时候,她没动,母亲走了,她很后悔,决定请求母亲的原谅。 其实母亲给了她这样一个机会,不把她当孩子,而是把她当作是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来求得她的关怀、谅解。那是她可以给母亲以安慰和温暖的时候,那难道不就是母亲承认了她的强大、她的能力,那不就是她曾经多么渴望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吗。母亲给了她这个机会,当时她没接受,出于狭隘的怨恨,和一时的怒气,但不管怎样,她们都该是这世上最相爱的人,她们彼此恨过,恨得很深,她们掩盖过自己,但那都过去了,所以,她们能做的只有原谅,那是令此生有意义的唯一方式。 你恨的那个人,你也得怜惜他,因为,他亦是从恨里来。你的爱,才终结那恨。女儿躲藏了一生,因为她始终接受不了真实的自己,因为那个真我母亲不喜欢,所以她总是那么拘谨,小心翼翼。而另一个人呢,母亲,快人快语,总是自信的、光彩的,却也是不真实的,这早就被女儿发现了,她们一样可怜。虽然她们看起来截然相反。她们更该同病相怜。 以为是宿命的隐藏,原来是从那个人那里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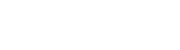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我们永远都只能是一个人,即使是与最亲密的人在一起,也会感到痛苦和孤独。
人需要一辈子来摆脱家庭带来的阴影
乌曼和褒曼大飚演技不是重点。最温暖的色调,最黯淡的内心。台词简洁、尖锐、直达心灵深处。舞台剧式的独白、眼神与眼神的长镜头,伯格曼一定是痛楚和勇敢到了极点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不用说太多,一句看到人落泪,足够。
1.亲情无法一蹴而成,突如其来为了爱而爱的爱只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女儿是个体,应给予自由和尊重,当然,更重要是发自内心的关爱;2.不断沉淀积累的感情鸿沟再也无法跨越,大声的宣泄也只是带来了一时的解脱,却无法得到挽救;3.秋日里的奏鸣曲再美也渗透着一股凄美和哀婉。
票价伯曼展映@ GZ二刷,大银幕重复创伤体验,很爽。母亲和女儿本质是一体两面,海莲娜则是她们关系的具象体现|看得PTSD严重爆发。“她从未爱过任何人。她不会爱。”我也不会。作为我的第3000个“看过”标记,这部片实在太疼了,看得我一直想死,想停止存在,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够用“喜欢”的心情来看待它。但是它反映出的苦痛我全部明白,全部明白。不能爱已是小事,如果生你的人使你生不如死呢?忍不住又看,忍不住又想:还好不是在影院看,因为要在寂静的黑暗中无声地哭非常累
#重看#所有最深的伤害都只会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畅谈或忏悔过后,原谅不会发生,一切回到原点,冷漠继续冷漠,沟壑依然沟壑;大块橙色&红色与冰冷苍白的内心戏形成强烈对比,明暗光线&正反打,正面&背影;乌曼演技真好,不愧御用。
镜头质感超凡,色彩打光简直美得一塌糊涂,拉大提琴那一场就像一幅构图完美的油画。从头到尾如同一场有限空间里的心理话剧,大段独白相当挑战演技,然而母女两人都是异常出色,这种情绪突如其来的爆发和内心的挖掘既是拷问也是自省,和解的不可能也早已注定。
女兒看著母親彈肖邦,她盯著她的臉,那表情在我心上扎了一個又一個窟窿,血噗噗往外冒,真疼。
这或许就是我喜欢伯格曼的原因——描述至亲的亲人间的相互折磨。这种折磨以爱的名义进行,将母亲的痛苦变成女儿的痛苦,母亲的失败变成女儿的失败。有时候觉得,家才是最孤单的地方,正是因为共度了最长的时光,才看不清彼此真正的模样。
伯格曼着实擅长探讨家庭关系中的疏离、误解、仇恨与虚伪,这回连母女关系中可能潜藏的自私、虚荣、傲慢与偏执亦被袒露于银幕之上。暖黄色调的室内陈设挡不住亲情中的刺骨冰冷。暮年的英格丽·褒曼和盛年的丽芙·乌曼飙戏,伯格曼式的特写与大特写一次次地揪出人的灵魂,攫住观者的心绪。整体还是比前作[呼喊与细语]更加具有舞台剧气调,尤其是以丈夫直面镜头自陈来引入(与收尾)故事的拍法(后景中是弹钢琴的妻子),以及一个个固定的镜头与多处门框式构图。(9.0/10)
姐姐的呼喊(近乎咆哮的控诉)与妹妹的细语(语焉不详的呢喃),后者可视为前者精神上的分身以象征恋母的本性,而伊娃已然只剩下恨意和愤怒;母女的两副假面,母亲生气的时候微笑,叫恨的人“我最亲爱的”,叫厌烦的人“亲爱的小女孩”,以爱的名义施行毁灭,用玫瑰中伤所爱之人,女儿则是佯装快乐,“因为我恨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如肖邦之音乐,不露声色的痛苦、短暂的解脱、解脱随即消失痛苦依然;依然是老伯克制冷静下暗流涌动的独幕剧式室内场面调度、振聋发聩且真诚内省得近乎内心独白的问询式台词、直接曝露人物情绪流溢的乃至显得狰狞扭曲面部大特写;尽管主题看似通俗浅白,但结合彼时戏外伯格曼、褒曼、乌曼的人生际遇来看,又添了许多别样的深意。
阿尔莫多瓦的高跟鞋,也是处理母女情感,比起伯格曼的细腻,就差太远了。
本片的艺术气质相当耀眼,从片名到结构,从故事到表演,从画面到台词,导演赋予了太多可资分析的样本。母亲噩梦惊醒后与酒醉女儿的对话,层次之递进关系,表演之精准程度,恍惚有种看心理惊悚片的错觉,揪心不已。
褒曼的角色是她自身真实的写照,亦是伯格曼的,这两位瑞典最富盛名并且拥有相同姓氏的伟大艺术家,都为了各自的事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可怕的创伤与疏离,乌尔曼那时也与伯格曼劳燕分飞,由她扮演的女儿,对母亲的爱与恨,在我看来,兼是对伯格曼的。褒曼随罗西里尼浪迹天涯,在好莱坞沉浮多年后终于回到故乡的怀抱,这样一位瑞典巨星,居然是第一次出演瑞典电影,这与影片的“奏鸣曲”结构不谋而合,伯格曼曾说:“我们在年轻时,从父母身边逃开,而后一步步,再回到他们身边,在这一刻,我们长大了。”
【中国电影资料馆展映】很惭愧,这是我看的第一部伯格曼作品。也很幸运,能在大银幕看到如此佳作。体会到了什么叫“飚戏”。银幕放大了演员一举一动一蹙眉的神情,也放大了色彩与气氛。让观众跟着揪心,回味震撼。每个人都深受家庭的影响。一滩平静的潭水下,激流涌动。完美的观影体验(尽在小西天~
褒曼和乌曼实在太适合饰演母女了,两人敏感、紧张、激动的神情和含泪的眼眸都有同样的特质,令人心痛。
人生最无法控制的两件事:自我的才华和出身,从婴儿诞生的那一刻起这二者就以命运的名义形塑着所有悲剧。而在亲情里,所有的解释、呼喊、疯狂、道歉,都是无用的。你的亲属关系,是你“天赋”的重要组成部分。
褒曼晚年有力的角色和作品(也是她和同叫伯格曼的大导的唯一一次合作),两个母女一台戏,完全可以搬至舞台的电影啊!两个人以中产阶级特有的文学性吵架方式(不看伯格曼不知道吵架还可以这样吵的啊)从天黑吵到天亮,积蓄多年的情感喷薄而出却并不是任何事情的解决⋯演员太好啦。弹琴那段最好。
我宁愿将海莲娜看作是伊娃的潜意识。爱恨交织的极致是一种失语症,能用语言组织起来倾泻的总是带着伪装,伊娃借酒宣泄用言语逼迫母亲时,海莲娜剧烈痛苦地挣扎着,母亲请求原谅伊娃不发一言时海莲娜叫喊着妈妈,过来!母亲逃跑了,伊娃低落沮丧看似平静,海莲娜喘不过气濒临灭绝崩溃,最后喊出的是妈妈
如果有人真实地爱我 也许我有勇气正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