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阴暗压抑的工业小镇,刺耳的机器轰鸣噪音。亨利?斯班瑟(杰克·南斯饰)初次拜访女友家,然而目睹到的却是一个怪异扭曲的家庭,霸道的母亲、无能的父亲、植物人似的祖母以及笨拙的女儿。而更令亨利感到无助的是,他被迫与女友结婚。一夜之间,亨利成为一个畸形儿的父亲。相貌丑陋恶心的婴儿让亨利异常恐惧焦虑,也让新婚妻子因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而半夜出逃。亨利再也忍受不了如此不堪的生活和夜夜噩梦,他最终亲手用剪刀肢解掉了这个畸形的早产儿。 由美国电影新浪潮运动旗手大卫·林奇创作的长片处女作《橡皮头》,历时五年完成。一经公映,便以强烈的前卫诡异风格挑战了当时还相当传统和保守的电影界。在情绪化的摇晃镜头与随处可见的阴暗腐败中,大卫·林奇构筑出了一幅扭曲病态的家庭人物关系,赤裸裸地破开人性的阴暗面。这种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来剖析人类精神世界中焦灼郁闷的手法,加上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特殊身份(普通话版)大明奇将之荆楚剑义梧桐雨宽恕与原谅金斩,有何贵干?疾风使命目击超自然:拉丁美洲篇第一季幻影车神3:魔盗激情铿锵玫瑰:走近女子澳式足球联盟五杰道士出山3:外星古墓(下)初来乍到 第一季日出之食 第三季我要做明星鲨卷风2父女特工我和我的第二故乡家有儿女新传虽然妈妈说我不可以嫁去日本形如父子血胎换骨贵客光临三剑客威龙二世本阵杀人事件OK 亲爱的我人生中最精彩的瞬间
长篇影评
1 ) 橡皮头,一个筋疲力尽的人
在2014年“橡皮头”收藏版DVD上市之时,大卫·林奇曾经说过,尽管这部电影发行这么多年,但他仍然没有看到哪个人的解读准确的捕捉到他拍摄电影时所想象的那些“画面”。由于“橡皮头”内容确实怪诞惊异,晦涩难懂,而身为作者的林奇又拒绝给出标准答案,所以至今也没有看过让人满意的剖析文章。林奇不去解释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要为他保护艺术价值的态度叫好,他认为如“橡皮头”这样的电影,其创作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去解读,标准答案反而会破坏艺术的想象空间。所以一时半会儿指望他老人家亲自做解释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部电影诞生的背景中,旁敲侧击的找寻创作理念的蛛丝马迹。比如林奇曾经提到电影里那些工厂和街道的影像,来自于他生活过的美国工业城市费城。黑白胶片让电影的景框散发出一股破败的味道,结合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背景,那些遭受重创的工业城市的状态,想来电影显得如此压抑其实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电影所散发出的压抑之感可能不仅仅是大环境的原因,还有来自于林奇本身的经历。众所周知,这部电影从开拍到成片用了5年(1972-1977),期间林奇一边要养家糊口,一边还要在预算极低的情况下完成拍摄、剪辑、道具、特效等一系列工作,其中的艰辛旁人恐怕无法想象。在失业的人群纷纷茫然的站上城市街头,当犯罪率上升、皮肉生意兴隆的时代,“橡皮头”像个怪胎一样孕育而生也许不是什么巧合。
人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想看过此片的人都会有一套自己的理解,那今天我也想说说我心中的“橡皮头”,其中很多解读都没能在电影中找到支持我观点的证据,这恐怕是犯了电影解读的大忌。但因为影片本身留给观众的提示不多,再加上林奇的“鼓励”,所以我姑且斗胆犯忌一次,纯从“感受”的角度出发,谈谈我对这部电影的理解。
观众可能最先纠结的一点是,电影中到底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是梦境,但我在这里不想追究这部分(尽管它也许确实有区别)。因为电影中的怪胎出现在绝大多数卧室的场景之中,我认为这一点让梦境和现实的区分失去意义,所以我宁愿假设从一开始,这一切就是一场怪诞的存在,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魔幻现实或者干脆是一场幻觉,毕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幻觉和梦产生的原理相同,都是本能逃过压抑审查的结果。抛弃掉梦境和现实的争论,你会发现卸下包袱,反而可以更好地聚焦电影中的人物和元素,以下是我的“幻觉解读”。
亨利是一个有性功能问题的男人,他和女友玛丽的生活很不和谐,亨利从信箱里拿出的很小的白色蠕虫,代表了他不举的“阳具”。我们看到亨利把“小蠕虫”放在了床边的神龛里面,在睡觉前拿出来看,最终略显失望的收了起来。而玛丽被嚎叫的怪胎吵得睡不着的那晚上,可以推测出怪胎代表了人的欲望(本我),代表了玛丽内心对性生活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亨利好像并没有听到怪胎的嚎叫的原因。无法忍受没有无性生活的状态,玛丽终于夺门而出,结束了这段关系。有两段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其一是玛丽离开房间的时候,跪在床前使劲儿拖拽行李箱的镜头,可以看作是绝望的玛丽最后一次激烈的替亨利打飞机,希望看到一些“效果”,当然她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

其二是睡梦中的玛丽,在床上一边磨牙揉眼睛的情节,揉的姿势让我想到了女性自慰的动作。另外,玛丽曾说:“I can't stand it. All I need is a decent night's sleep.”,这句话字面意思是我受不了,我只想好好睡一晚上,但我们完全可以把decent sleep“曲解”为“合格的sex”的意思。
所以带着这个假设,我们回头看亨利拜访玛丽一家的片段。在这个片段有些部分非常有趣。玛丽的母亲问亨利“what did you do”,表面上看是问亨利在假期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你做了什么”,暗指玛丽和亨利的性关系,在这个时候玛丽的怪异行为出现了,她不停的用手挠自己的膝盖,表情抽搐,看到这个场景让人第一联想到的可能是玛丽在自慰的夸张画面,与此同时亨利说“我是一个printer”,这时候犯病的玛丽突然恢复正常说了一句“Henry is very clever in printing”(亨利对印刷很在行)。请注意print这个词,在美国俚语里print有做爱的意思,结合之前我给亨利定下的不举的调性,这么看似乎焦虑的玛丽在帮亨利掩饰?
看过电影的人可能会感受到亨利对于住在隔壁的女人的欲望,从这个女人和身份不明的老头一起回家的情节来看,我认为女人很可能是一个妓女。怪胎身上的疮也很像性病的症状,所以我猜测,亨利对女邻居的欲望,有可能被对性病的恐惧所阻碍,还有一种可能是,亨利因为和女邻居有染,感染上了性病。而妓女的设定也符合美国70年代经济萧条时的社会写照。
既然是林奇的电影,免不了要在Freud的精神分析上做文章。顺着这条思路,我猜测影片最开始出现的星球,代表了亨利的躯壳,而住在星球上的破房子里的满身癞疮的男人,则代表了亨利的自我,原因有两点,首先他操纵着仪器,很符合精神分析里对自我的定义:自我小心翼翼的服务于本我和超我的要求,调节着它们产生的矛盾;其次这个男人身上千疮百孔,也很像自我那不断受到压迫的状态。最后亨利在怪胎(本我)的嘲笑下,毁灭了它,导致自己躯壳破裂,反而在消灭自我和本我后,与舞台上的女人拥抱在了一起。这个舞台上的女人是谁呢?我个人感觉她代表了死亡,因为她唱过“In heaven,everything's fine.”她的数度出现,也代表了亨利企图毁灭自己的愿望。或者干脆她就代表了女性的卵子…

说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已经编不下去了(扶墙),最后再提一点吧,eraserhead在俚语里有“筋疲力尽的人”的意思。可能这部电影根本就是在讲一个男人,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在工作、生活(特别是性生活)中挣扎的故事吧。
90/100
2 ) 我们以供奉虚无为生
在灰暗中,我们看不清东西,存在总是一副即将被照亮的状态,但在绝对光明下,什么都看不见;不可忍受的刺目之白将我们的视线覆盖。
二
渐渐变大,戛然而止;
渐渐变亮,戛然而止;
事实上,除了自杀,没有什么东西会戛然而止;
如同橡皮,我们总是在各种绝对力量的挤压中恢复原状。
三
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但确实跟我有关;正如这个世界不是我的,但它确跟我有关一样。
四
面对哭泣安然入睡,
面对嘲笑辗转难眠。
五
当我们看,光明舞台上的角色总在躲避着什么。当我们走上这舞台,与我们有关的孩子(世界/文明)将我们谋杀,我们成了符号的替身。换而言之,舞台(前景)上呈现的东西,只是我们造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们的真实命运则是成为涂抹者或者被涂抹者。
六
在黑夜与白昼、醒着与梦着的轮回里,是我们抹去梦境,还是梦境抹去我们?
七
我们以供奉虚无为生,而在这虚无中加上别的什么东西,将会是一种千疮百孔的错误。
3 ) 片子令人恐惧的是它令人恐惧的真实感
看完了橡皮头,感觉压抑的喘不过气。片子里的恐怖不光是感官上的怪异,而是利用隐喻反映了生活中无法逃离的恐惧感。男主像是被关在一个屋子里,无法逃逐。唯一的出口是死亡,是摧毁,是犯罪。他出不去,四周是牢笼,岳母是牢笼,欲望是牢笼,他以为的出口只是另一条肮脏的下水道。他以为把畸形的孩子,那性的结晶摧毁,他就可以自由。但他无法自由,他的自由只是自我救赎,只是一种毁灭,一种逃跑。他向往的那丑陋,快乐又原始的妓女,是片中不算救赎的唯一救赎。
之所以恐惧,因为它像诗,像音乐。它像一个通道,将你带入另一个人的噩梦里,完完全全的让人沉浸。许多瞬间像是桥梁,令人回忆过去,虽然从未经历过。
4 ) 父弑子、子弑父
所谓大师,大概就是,一两个画面就把人物的处境和关系表达清楚,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现实主义。第一次看大卫林奇的电影,觉得颇具天才气质。电影内容方面会有更多维度的解释空间,第一遍看下来,简单讲就是:父亲是儿子的橡皮头,地球是人类社会的橡皮头,这种“铅笔—橡皮”关系是一种坚实而庞大的体系,我们的存在方式何时变得如此畸形?这是值得考虑的。
有趣的是,林奇这部电影没有在橡皮头擦过后,橡皮的粉尘被一掸而尽而结束,他拍了一个反叛的结果——父弑子。“父弑子”隐隐回应“子弑父”,我将它看成对古人神话的回应。这部电影内部也同时具备父弑子与子弑父的形式。如果说父母对子女是一个古老的谎言,那么子女对父母的谎言似乎更加现代化,更是体系化的结果。西方古神话中父弑子的故事似乎并不罕见,子弑父更显得反叛,如今却似乎相反了,这是就具体形式而言的。但如果着眼更大的体系来讲,从反叛与自由来讲,这两点都可以归结到同一种精神/同一种气质,这种从古至今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感到它是超越的,是灵魂天生的,也或许是上帝赋予,来反抗所有伪上帝的。
========
睡了一会儿想到,这部片从性的角度阐释也是通顺的。最后那个姑娘,两颊长了两个鼓鼓的球,很像睾丸,球与身体的比例神似勃起的XX。所以这又是一个男人找回自己的鸡巴(纯粹的性欲),自我解放的故事。
5 ) 梦境——观《橡皮头 Eraserhead》有感
在读《梦室: 大卫·林奇传Room to Dream》之前,我一直猜想这位格外擅长拍摄恐怖猎奇电影的大导演的童年是不是有什么非同一般的遭遇,让他在之后的创作中能有那么多关于人类负面情绪和记忆,各类噩梦的灵感闪现。《梦室: 大卫·林奇传Room to Dream》是一部回忆录与自传“合璧”的传记,由克里斯汀·麦肯纳与大卫·林奇合作完成,克里斯汀先用传统的传记写作方法完成一个章节,林奇则在通读后做出补充和修改。相当于两人交替讲述同一个故事,大卫·林奇拍的电影晦涩难懂,但是说话还是很好懂的,诙谐幽默,风趣十足。结果我一直读到林奇进电影学院,都没觉得他的童年少年生活有什么特别独特之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前期得到的教育资源甚至很有可能不如现在的普通中学生。1966年初,大卫·林奇回到了费城,进入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就读,并开始尝试制作影片。1968年,执导彩色短片《字母表 The Alphabet》(我很喜欢这个,反反复复看,小女孩背字母表吐血的场景让我联想到自己从前努力背书的样子,很有亲切感),他凭借该短片获得了美国电影协会的奖学金,但是他不久就离开了电影界,继续专注于他的美术学业。他真的热爱着画画,一直不停地画画,“我就到学校管理部门去求情:‘让我退课吧,我不想成为物理学家。’可他们说:‘大卫,人生中有些事,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得去做。’我弟弟很早就对电子那套东西感兴趣,他后来也进入了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将来会做什么了。他们应该让我离开学校,全神贯注发展那项特长。我的妈呀!在学校待的那些时间完全可以用来画画了!而且我什么都没记住。什么都没记住!学校里学的东西我他妈全忘了。”后来拍电影了,时不时在影片中插入一段动画,制作一些别具特色的小道具都是林奇的拿手好戏,别人可做不来这些。1970年,执导剧情短片《祖母 The Grandmother (1970)》(这个时候他还没系统学过怎么拍电影,没钱没资金没技术,几个演员是临时拉来的隔壁邻居和同事,但是看过这部片子的人都知道,大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之后进入美国电影学会研读电影研究。1974年,自编自导自演短片《被截肢者 The Amputee》。1977年,大卫·林奇根据自己动荡的生活以及费城贫民区生活给他的启发,执导了恐怖电影《橡皮头 Eraserhead》,他因人手不足他还担任了该片的制作人、剪辑师、配乐、艺术指导、美术设计等工作,“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所有东西都是常识,自己就能琢磨出来怎么做特效”,这是林奇执导的个人第一部长片。

大卫·林奇在学院的马厩里花了五年才拍出了《橡皮头 Eraserhead》。在《祖母 The Grandmother》中,林奇的很多风格已经初具雏形,我认为林奇最天才之作就是《祖母 The Grandmother (1970)》和《兔子 Rabbits (2002)》,混混沌沌,疯疯癫癫,让人臣服。篇幅很短,但是惊悚和荒诞充斥在每一帧之中。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大师确实就是天生的,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但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时候的林奇还只是一块璞玉,要想闪闪发光除了努力,还需要很多好运气。电影学院虽然给不了天才的构思,但是给了林奇拍摄场地和最初的那笔资金。“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某些事会突然而至,将一切带上正轨。这种事在人生中有可能发生。但假如你盼望着它发生,就可能会失望。但你应该随时做好准备,因为这种事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林奇电影中的那股子荒诞感到底从何而来呢? “荒诞的本质是对人生的无意义的虚无性的审美感悟。荒诞是人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现象和本质分裂,动机与结果的背离,往往以非理性和异化形态表现出来,现实中的荒诞是审美活动范畴中荒诞的根源,荒诞审美形态是对现实中荒诞人生实践以审美的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加缪认为,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首要原因是习惯。自杀则意味着承认这种习惯的无谓性、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人一旦与生活产生这样的“离异”,就会产生荒诞感。在相反意义上,人的生活需要一种“自洽感”,无论是目不识丁的民众,还是思想深邃的学者。 “一个哪怕是能用邪理解释的世界,也不失为一个亲切的世界。” 我猜,费城那种沉重嘈杂危险的工业感给林奇带来了太多灵感。《橡皮头 Eraserhead》拍了5年,这期间多次因为缺乏资金等原因停拍,其间林奇为了赚钱又干起了老本行——开车给人送报纸,他自述年轻时非常擅长扫地,靠着把一个陈年脏马桶刷得洁白发亮而得到了房东的青睐,最后把房子租给了他,还允许他随意改造车库。那五年到底吃了多少苦,林奇没有详细讲述。他自己讲的故事里,好多事情都是拖一拖磨一磨就好了,演员们就是随便一挑,每一位都那么合适,一切都不可思议般恰到好处。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几年的提心吊胆自然是少不了,几个演员也能一直坚持下来简直就是奇迹了。


《橡皮头 Eraserhead》中,好多道具都是林奇自己做的,妆容也由他亲手设计(成名之后很多电影里他也自己做道具,全能型人才),即使我已经看了大量猎奇恐怖的片子,影片中那个小怪物依然让人过目难忘,太了不起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现在虽然可以用特效制作各种逼真恶心的小怪物,但是都没有这个毫不血腥,大部分场景中都不能动的小怪物留给我的印象深刻。一个怪异扭曲的家庭,霸道的母亲、无能的父亲、植物人似的祖母以及笨拙的女儿。而更令亨利感到无助的是,他被迫与女友结婚。一夜之间,亨利成为一个畸形儿的父亲。毫无疑问,主角们患上了某种产后抑郁症,小夫妻在没准备好的时候就生了这个孩子,当然觉得它比怪物还恐怖。林奇透露,影片中的脐带都是用的真人脐带。噩梦,幻觉,潜意识,诡异又暧昧难明的氛围真是拍得太好了。林奇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他从来不解释自己的作品,所有的一切都由观众自己来解读,比起作品已经完成,还要对角色指手画脚,并一直改来改去的作者好太多了。林奇自己说:“《橡皮头》是我最具精神性的一部电影,不过许多人都没看出来。当时我产生了一些感觉,但不知道这些感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我拿出《圣经》开始读。我读着读着,看到了一句话,我说:‘就是它了。’但我不能告诉你到底是哪句话。”
“你的天性已经在那么大程度上被决定了,虽然父母和朋友能产生部分影响,但你却一直还是最初的那个你。我的几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而且从一出生起就带着他们各自的小天性了。”人生是多么奇妙啊,看似命运天注定,却又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愿所有人都能在人生之路上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
6 ) 橡皮头付体
在梦中依稀感到自己就是橡皮头,一个生活在现在,一个泱泱大国里的橡皮头。
仔细想想,我学校毕业后便到此地,一个工业和商业均发达的地方,以前大家都来下海,现在,只能下河,我在这条污秽的河里带着梦想,荣辱洗淘着。
为了工作,放弃很多,永远没有归宿感的租住房,永远没有朋友的工作环境,没有一片净土,而工作就象强奸,哈哈,放弃尊严,放弃爱好和自己的小爱好。
永远看不到头的打工生涯,只有在电脑前发泄自己欲望,只有在梦里,才能看到的她,性欲,就想是一个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怪婴,你想要,而得到后,却是一个恶梦。
发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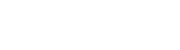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天才之作. 大卫林奇在处女作中完整地展现了其后毕生的创作观念,长片宛如短片的感觉证明了凭借一种美学或风格足以支撑叙事,在这个意义下他堪称雷德利斯科特的先行者;之所以将他与卡夫卡相提并论,正是因为其作品以虚构的形式"如实地"描绘生活,以致反而凸显出"真实世界"的不真实. 作为七十年代的低预算影片,出类拔萃的声音设计可谓十分惊人.
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精神多了。
大卫林奇横空出世,这部处女作也影响了他今后的发型选择。真是把生活恐惧的噩梦都具象化了,好久没在影院里看过这么恶心的电影了还是巨幕,观察旁边观众的反应也很有意思,感觉好几个被男友带来的女的都快码架了。70年代的特效模型噪音先锋实验颠覆,但作为长片还是有些勉强,有些凑。北影节科技馆。
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你是我写过最霉的情书。
以后可能再也吃不下老妈兔头了
拍完这种电影居然还有人给钱他拍商业片……
"Exterminate all rational thought." Visual storytelling, visual远高于storytelling. 这是最林奇的电影,后续作品中几乎所有元素都从中有迹可循,领会了它就领会了林奇。也是他作品中最不需要在意情节的一部,声音与影像直接入侵潜意识。
一部以极端的“所见”引发对“所不见”之关注的电影。在这个角度上,我能够在它呈现的所有畸形、机械与恶心里看到对自然与自然物的无力渴求,和失去自然的恐惧、绝望与哀伤。无论欣赏与否,林奇都是一个从处女长片就拥有了自身电影语言系统的导演,不仅个性,而且完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嫉妒的了。
A-. 恐婚恐育终极指南,繁殖已经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彻底的畸形秀。这部处女作就像大卫·林奇职业生涯的某种“摘要”与“宣言”,他在后期作品中所钟爱的手法(打光的方式,轰鸣的环境音,梦与现实deja vu式的勾连,标志性的游走pov镜头)与主题(性渴望/性压抑/性无能的矛盾,光鲜秩序下的疯狂失序,生活本身的戏剧性与表演性),基本都能在这里找到原型。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奠定了一种编译恐惧的法则:通过将熟悉陌生化,去诱发基于纯粹感官与直觉的uncanniness。He really is iconic right from the start. 2022.1.7 Filmothèque
#重看#四星半;77年的大师处女作,时隔七年再看,震惊和讶异未减少分毫(观影初期的口味维持至今);梦见自己死去,梦见一切摧枯拉朽,梦见所有光和影都沦陷,没有经历过地狱怎会在腐烂泥沼中涅槃出光明,噩梦是灵感源泉;从主题和技法上讲,林奇后来更著名的片大多没有超出本片。
影史处女作TOP3,不输《皮囊之下》等任何一部当代科幻的水准。在拍摄有人物运动的中景或近景时,人的头部(包括表情)其实是观众首先下意识注意的部位。人的脑袋是一个巨大而陌生的星球,身体围绕头颅漂浮。摄影机像“卫星”那样运动。每个人的头部都以夸张的形象出现,男主角、腮帮子鼓鼓的女人…硕大的、具有生殖功能的精子头部坠入卵子,交媾诞生成人类。主观镜头也神棍极了,回忆一下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它等于“地球”的眼睛在看月亮。
我以为他的头是用橡皮做的。。。
反正我是看爽了!!!
产后抑郁症大战新保守主义狗崽子
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丝丝入扣。焦虑恐惧不安黑暗困惑,令人毛骨悚然的梦境。黑白片的好处就是能更好的引导观众的注意力。这部处女座和后来的穆赫兰道比后者就只能算是林奇的通俗片。对人性阴暗面的偏好,摇晃的镜头和充满矛盾的情绪正是林奇风格的完美体现。
大卫·林奇导演处女作,大胆,诡谲,离奇。断续的噪音、让人不安的配乐加上黑白摄影与用光营造出阴暗恐惧感,梦境,想象与现实交织的无序剪辑与叙事让人如坠云雾,畸形人、种种梦魇般的意象和无处不在的性隐喻直指人心,这也许是最好的展现在压迫与恐惧中彷徨挣扎的人性图景的作品之一吧!(9.0/10)
你们水瓶座的脑洞我们大射手都hold不住……倒无所谓看不看得懂,片子里那种焦虑的情绪是很容易直观地体验到的,至于将这种情绪对应于何种原因,则视观众的经历而定。就我个人而言,最有共鸣的是男主角突然醒来后,从身旁的女伴被子里不断揪出巨大的精子一幕,那种恐惧感最为直观。
焦虑压抑下诞生的畸形怪物,紧张不安下飘洒的橡皮屑,你最惧怕的噩梦被林奇用影像具象化出,阴森抑郁深入每一寸骨头,现实?幻想?梦境?梦醒?实物?隐喻?一场内心最深处恐惧与焦虑的噩梦,梦没有尽头。 8.5 ★★★★
【B-】想象力不如之后的作品也没有之后的好看,我不觉得这部的故事有许多人想的那样复杂,除了几个明显的梦境,大部分东西只是对费城工人家庭的映射,与其说故意让人看不懂,我倒更觉得那是因为大卫林奇本来就不是正常人
音景有趣,不絕於耳的工業噪音(大者如工廠機具聲、小者如唱機指針磨蹭聲),好像所有角色動作造成的聲響都加大回音,許多對話聲異常尖銳刺耳聒噪(或許因而加深惡夢感,讓人想逃、想醒),當然,可能也是表演太爛使然⋯(有讓人想起John Waters)大銀幕重看後不得不說,Lynch首部作有點過譽、有點裝逼⋯非常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