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剧情介绍
故事发生在1900年的美国南方,瑞吉娜(贝蒂·戴维斯 Bette Davis 饰)和她的兄弟们都以贪婪而著称,他们决定合伙投资一个工厂项目,这个项目可以给他们带来巨额财富,却对当地居民无益甚至是压榨。由于瑞吉娜并没有足够多的钱,于是她将目标放到了自己的丈夫霍勒斯(赫伯特·马歇尔 Herbert Marshall 饰)的身上,派出了二人的独女亚历珊德拉(特雷莎·怀特 Teresa Wright 饰)请回了因重病在外地疗养的霍勒斯。 然而霍勒斯识破了瑞吉娜的用意,拒绝了投资,而她贪婪的兄弟们竟因此铤而走险。脊柱医生DA师王志文版那山那水好人2020天火伊娃嬉闹大酒店地狱宝贝恶童侦探机械师2:复活英语金刚归来(普通话)歌舞青春:音乐剧集第四季心慌方·零软萌娘子是杀手高斯奥特曼VS杰斯提斯奥特曼 最终决战全员单恋第三次世界大战 四十一小时的恐怖末日使者惩戒失忆症癫螳螂雷德利 第一季生死航班隐形受害者 伊丽莎 萨穆迪奥案件犯罪现场调查 第二季皇家师姐之中间人铁人王进喜2011我们天上见球迷达人碧血丹砂小夫妻的火烤新婚生活胖者生存第一季龙虎少年墨水特别胜利(国语版)我的小卷毛尽诉心中情最佳销售员远大前程地狱厨房(美版)第六季实习大叔嘘声
长篇影评
1 ) 她只敢杀她不恨的人
不知道1941年的《小狐狸》映后女主受到如何反响,但这位水蛇腰凝脂肤的美艳贵妇若是来到21世纪20年代,必定是引起热烈欢呼的“美强惨”。
她“贪”——美艳妖娆,养尊处优,不安现状,心眼儿和眼珠一起滴溜溜的不停转,卖完女儿卖老公,面纱一戴,谁也不爱; 镜头一转,这位贵妇低垂着长睫毛,我见犹怜的诉说着她“贪”的因——悲惨童年,父母长期忽视冷落,兄长霸占家族财产,原生家庭的缺位撕开了口子,慢慢变成了填不满的窟窿眼儿。
我相信,一定会有观众很爱她。
她象征着一类极端情形下的女性觉醒。
首先觉醒的,是对欲望的坦诚,超越了世俗对女人的“功利心”的刻板印象—— 女主野心勃勃地谋划远在芝加哥的未来,引导兄长一同畅想暴富,像男性一样甚至超越男性,毫不掩盖对钱和权力的向往;
其次是突破传统框架下的女性形象—— 不再是“无私的母亲”,而是用女儿婚姻牟利的独裁者; 不再是“体贴的妻子”,而是当面咒丈夫早死的悍妇; 不再是“乖巧的小妹”,而是威胁兄长放权的勒索者;
最后一层觉醒,已经是超脱“女性”层面,到达人性本身的探讨—— 通过“弑父(父权)”达到权力的更迭。
最后这一层是女主区别于其他“恶女”形象的一层。
这一层够凶恶,是“人”性的真实,真实在于人性之恶本就无需因果; 但也很懦弱,是“女”性的悲哀,悲哀在于这里所指的“女”性而非“女性”,不是相对于“男性”的性别属性,而是相对于“父权”体系的“母权”文化。
此时已经无关乎性别,在父权制度下受压迫的不光是女性。
今村昌平在《复仇在我》描绘了一个连续杀人犯的诞生,男主自小对父亲恨之入骨,却始终无法突破弑父底线,这种矛盾使男主无法面对虚无的自我,只能“无能狂怒”转而四处对无辜者行凶。 最后父亲站在临刑的儿子面前说:你杀不了我,你没那个胆子。你只敢杀你不恨的人。
同样的,在《小狐狸》的高潮部分,女主的“恶”无所畏惧,眼睁睁看着丈夫逝世不带一丝怜悯,但也同时是委身父权体系的懦弱——她只敢杀她不恨的人。
父母冷落,她不敢埋怨; 兄长掠夺,她不敢反抗; 世俗约定男婚女嫁,她便嫁作人妇。 和《复仇在我》的男主一样,恨的是父兄社会,却无法突破传统观念,这种冲突同样也使女主无法面对虚无的自我。
女主老公问她为何嫁给他,女主回答:“因为我年轻时很寂寞,真的寂寞,不是一般人所指的寂寞,我寂寞想要的东西都得不到。” 于是女主把自己的寂寞转化为对具象化物质的贪婪,其实女主真的渴望钱与权吗,只是原始冲突无法解决的虚无感需要一个落脚点。
无法解决根源的虚无带来无止境对物质的贪婪,最终女主的丈夫为此殉葬。
表面上看,似乎女主完成了如同《甄嬛传》爽文般的“弑夫”,然而在本片的语境中,“弑夫”并不等同于“弑父”。 女主并没有完成对父权体系的反抗。
当然,并不是说《小狐狸》是一部失败的女性意识觉醒之作,而是在时代背景下存在无法规避的局限性。 在无法推翻父权体系前,更重要的是找回在强权之下被扭曲的初心。
女主最后对女儿说的那段话: “小珊,你总算有思想了,我一直以为你是甜而没内容的小甜水。”(小珊,恭喜你,你不再是父权体系里流水线生产的淑女产品了。) “我们不应该做坏朋友,我不想我们变成坏朋友。”(我们的终点其实不尽相同,虽然你要走的路和我不一样。) 可以看作一个走极端的女性觉醒案例面对后辈的忏悔及对自我的救赎。
愿大家不会委身强权无法面对真实自我。 都敢“杀”自己真正恨的人,都敢争取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2 ) Poor Regina
看完之后,出乎意料的并没有对Regina恨之入骨,反而感到非常同情她。
这个极其贪婪的女人不断地在掠夺着别人的一切,企图用金钱来填补和照亮自己那无穷无尽而又黑暗无光的内心世界。她空虚的灵魂根本得不到救赎。
况且没有谁会生来就贪得不厌。长久以来那种无法得到满足的压抑,一旦爆发,就会让无休止的欲望侵蚀了我们的整个心灵。
Regina向Horace摊牌的最后那一幕,她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她是个女人,从小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便是小小的属于自己的空间。父亲死后,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兄弟,她什么也得不到,无可依靠,一无所有。她只能嫁人,即使那并不是自己所爱的人,但至少会是孤海中的一根救命稻草。
女人和男人这两种人类的基本身份,向来都不能相提并论。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等级,平等地与男性等级进行交换、订立契约。很长一段时期里,女人都没有自主订立婚约权利,常作为隶属身份被父亲、兄弟所支配。
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看做生产者,他的生存之正当性被他为群体做的工作所保证。生殖、家务等等历久已来的各种缘由,致使女人在此层面上没有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尊严。
在Regina所处的那个时代,如果选择独身,那只会使她降到寄生者和贱民的地位。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途径,也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
可以看出,Regina非常向往离开小镇前往芝加哥开始新的生活,她极其想摆脱自己这种依附于男人的现状。她如此狡诈,机关算尽,也只是因为觉得自己生命中并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Regina待人一直都很强势,想要自己的两个兄弟完全受命于他,也许还因为心里不平衡。在Horace告诉她,她的兄弟们偷了债券时,我感觉她那句"I don't believe!"中,还包含着发自内心的对现实的绝望。
她确实是个心怀恶意的女人,但是并非十恶不赦,她并没有想要故意害死Horace的动机,她只是想得到那七成五的股份,只是想要赚到足够的钱然后定居芝加哥。
至少在Horace倒下后她有向他跑去,而不是等他倒在楼梯上死了之后再叫人。
至少她在最后清醒过来时,她还会感到害怕,还曾经恳求过女儿陪她一起睡。
3 ) 如海一般沉静深邃的父爱

“Marshall turns in one of his top performances in the exacting portrayal of a suffering, dying man.”摘录自当时各界媒体评价1941年《小狐狸》(The Little Foxes),赫伯特•马歇尔饰演银行家霍勒斯•吉登斯(Horace Giddens)。在这部奥斯卡金像奖九项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奖)的影片里,丈夫霍勒斯的死亡,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对比出贪婪、冷酷的妻子雷吉娜,有着极其强烈的震撼效果,是揭示人性贪婪、冷酷的高潮部分。
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像《圣经》里的蝗虫一样要吃光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人。霍勒斯看穿了妻子的贪婪,他断然拒绝了雷吉娜贪婪的计划,与蛇蝎同在屋檐下。他感到恶心,他厌恶她,以及她的兄弟们为了得到一毛钱而费尽心机。他厌恶这群人已经足够富裕,依旧不择手段的谋算压榨穷人。无疑,这对夫妻三观极其不合,维系他们的是女儿。雷吉娜利用女儿把病重的丈夫霍勒斯从医院劝诱回家时,霍勒斯很清楚自己将面对什么。他的神情中带着深深的忧郁和无奈。他爱自己的女儿,不但教育她,要懂得善意和礼貌,同时为她规划,不能让雷吉娜毁了女儿的未来。
兴许很多观众看到了霍勒斯的病苦,Bart把握的很好,不均匀的呼吸,时常喘息,时常无力无神,典型的心脏病患者。少数观众看到了霍勒斯的理智、持重、知性、公正。我还看到了他的感性:他看雨,听钢琴,还不点灯。在短暂的平和气氛里,他眼神是游离的、茫然的。他的思绪仿佛飞到了别处,在那里才能得以宽慰。要么离开,要么死亡。最终,他被摧毁了(雷吉娜无疑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在他临终时,他轻微抖了一下手,他握住了女儿的手,将它送至嘴边,轻轻吻了一下,不仅令人潸然泪下。

4 ) 摘录
凭借自己与戈德温的关系,托兰能经常与威廉·惠勒一起工作。他们俩合作拍摄了《三人行》(These Three;1936)、《夺妻记》(Come and Get it;1936)、《死角》(1937)、《呼啸山庄》(1939;他为此获得一项奥斯卡奖)、《草莽英雄》(Westerner;1940)、《小狐狸》(The Little Foxes;1941)以及《黄金时代》(1946)。正是在30年代后期与惠勒的合作中,托兰开始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在工作中系统性地采用纵深构图、多重动作层面、“带屋顶的”场景(能看到天花板的室内布景)和明暗对比的灯光(用聚集的灯光照亮原本阴暗的布景的若干部分)。这需要用“更快的”生胶片、具有创意的灯光技巧和对焦范围比较大的摄影机镜头进行广泛实验……
在这部电影的高潮时刻,赫伯特·马歇尔[Herbert Marshall]扮演的角色在背景中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去,而在前景中,贝蒂·戴维丝扮演的角色却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种构图是完美的“托兰镜头”,只有一处美中不足:马歇尔的形象略微有点失焦。(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世界电影史》)
5 ) 一个矫枉过正的南方
惠勒早期影片的主要情节大多发生在室内,但就在这样狭窄的空间内,他总是能以令人惊异的方式表现出心灵的巨大变化和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惠勒电影的空间是极度浓缩的,他的人物亦如此。在《小狐狸》里,哈伯德兄妹几人一出场,便让我们看到了战败的南方如何陷入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后果当中——原先的优雅和教养被彻底抛弃了,对金钱的贪欲主宰了一切,婚姻都因为经济利益而缔结,就像本•哈伯德对来自芝加哥的投资商马修•威廉露骨地说的那样:“我们接管了那些没落贵族的大农场,也接管了他们的女儿。”面对在当地投资纺织厂有可能带来的巨额回报,本•哈伯德更是像个小学生那样迫不及待,直接把为威廉接风的宴席变成了商业会谈。在这里,惠勒给我们作了一个绝妙的对比:本•哈伯德对南方贵族出身的弟媳伯蒂•哈伯德极尽打击之能事,讥讽她跟不上时代,以表明自己是观念开放的新潮人士;而来自工业之乡的威廉反倒对伯蒂充满同情和敬意,并为她对旧生活的留恋辩解:“有时候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学习新东西是很难的。”晚宴后,客人开始欣赏伯蒂和亚历珊德拉合奏舒伯特的钢琴曲,诺大的客厅里,除了工于心计的雷吉娜故作姿态之外,哈伯德家的人个个如坐针毡,无所适从,教养在他们身上已消失殆尽。
威廉•惠勒向来擅长以严谨的结构和均匀的叙事节奏来呈现人物的内心,深谙如何逐步逐步地释放主题。在影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哈伯德兄妹三人的粗俗和贪婪如何一步一步升级的:先是雷吉娜利用女儿把病重的丈夫贺拉斯•吉登斯从医院劝诱回家,而且根本不管后者的健康状况,在投资纺织厂的问题上对他纠缠不休,因为贺拉斯有着最充足的资金。在当地建工厂,低廉的工资将使贫穷的人更加贫穷,贺拉斯断然拒绝了妻子的要求。于是,李奥•哈伯德便在父亲的指使下去偷窃贺拉斯放在银行的债券。这种贪婪发展到最高峰便是雷吉娜为了得到纺织厂最多的股份,看着丈夫在她面前死去——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贺拉斯在病情发作时必须靠服药来维持生命,在与妻子的争执中,贺拉斯内心过于激动,结果药瓶掉到了地上,而雷吉娜则在旁边以无比的冷酷看着惨剧发生。在这一场戏里,我们看到了贝蒂•戴维斯令人惊叹的表演才华,由她饰演的雷吉娜身上那种人性的幽暗竟然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哈伯德一家的贪婪,正如智慧的黑人女佣艾蒂所说的那样:“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像《圣经》里的蝗虫一样要吃光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人。”这句充满寓意的对白跟影片的名字遥相呼应。《小狐狸》这个片名来自于《圣经》中的《所罗门之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肆意妄为的小狐狸们毁坏了一切:榨取穷人的财富,败坏了家庭,更重要的是,摧毁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信念。贺拉斯在死前不久曾怒斥妻子雷吉娜,道出了郁积在心中的绝望:“我对你感到恶心,恶心这所房子,恶心与你在一起的不幸生活,恶心你的兄弟为了得到一毛钱而费尽心机。” 小狐狸把家庭变成了埋葬活人的坟墓,知性、持重的贺拉斯就这样被摧毁了,而伯蒂•哈伯德则是另一个更富悲剧意味的牺牲品。作为南方没落贵族家的后代,伯蒂就像威廉•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小姐一样活在过去,自己向往的旧世界被摧毁了,却又始终无法融入新生活。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婚前的少女和童年时代,这些美好的记忆都凝结在一个地点和一个人物上——巨大的莱尔内农场以及她的母亲。一提起跟过去有关的事情,她便开始滔滔不绝,但无论在何种场合,她的丈夫和儿子却总是在一边各干各的,根本无人应和。伯蒂向众人吐露内心的那场戏,则是全片最令人心碎的段落之一。首先,她谈到了自己的儿子李奥——他继承了父亲的贪婪,却没有继承后者的精明,所以只能成为父亲的应声虫。伯蒂充满悲哀地说:“你们想知道一些事情吗?我不喜欢李奥,我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是不是很滑稽?”奥斯卡•哈伯德当年为了莱尔内农场而跟她结婚,而伯蒂自己却以为是爱情,她哀叹道:“每个人都知道他为什么跟我结婚,除了我自己。愚蠢,愚蠢的我啊!”如今,哈伯德家的人又想故技重施,正在策划李奥和亚历珊德拉的婚姻,所以伯蒂不无伤感地说:“珊,你的情况会更糟,因为你没有一个那么好的妈妈可以怀念。”
所幸的是,伯蒂的预言并未成真,大时代牺牲了一批人,同时也意味着新一代青年的诞生。当这些充满朝气的新人认识到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如此腐化、扭曲后,会去积极探索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威廉•惠勒,他总是喜欢让他的电影里闪动着年轻的身影,这些囿于狭窄生活经验的青年初涉人世,稚嫩的目光尚未能分清世界的真真假假。正是在这些将要形成自己独立人格的天真烂漫者面前,现实才显得触目惊心!在惠勒看来,与世界的丑陋短兵相接,才有可能带来年轻心灵的成熟。《小狐狸》原本是一部揭示人性贪婪、冷酷的作品,但因为正值豆蔻年华的亚历珊德拉•吉登斯的存在,使影片远远超越了社会批判性主题本身的局限。通过小珊的目光和感悟,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精神转型从个人成长的层面得到了深化。
作为片中最惹人喜爱的形象之一,亚历珊德拉身上有着许多美好的东西——质朴,快乐的天性,未脱的稚气,这使得她如朝阳般充满活力,并能怀着美好的情感看待世界。但是,质朴和单纯同时也意味着无知无识,尚不具备对生活的判断力,只能依靠天性来行事。所以我们看到,小珊身上同时又有着那种来自于她母亲雷吉娜的狭隘、恶劣的作风:在她接父亲回来的路上,为了让父亲得到好的休息,小珊竟强行叫旅馆经理从已经住满客人的一楼腾出房间来;当她看到她喜欢的大卫•休伊特和一位女士在共进晚餐,便像坏脾气的小孩一样表现得相当无礼。所幸的是,小珊的身边有着积极寻找新生活的大卫和一个公正、理智的父亲。他们两人对珊的善良天性充满信心,每次珊陷入困惑的时候,他们总是叫她自己去做出判断,叫她靠自己获得认识世界的目光。大卫经常鼓励她:“你走出了第一步,然后会是第二步,然后你会发现你正在靠自己在走路。”所以,当珊听到母亲恶毒地对父亲说出“我希望你死”这句话的时候,家庭的温情面纱在那一刻被撕得粉碎,小珊的目光终于变得通透了。她开始以完全不一样的目光来重新审视她的母亲——这个女人除了是她的母亲这一特定的身份之外,她同时还是谁呢?她的舅舅们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当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少女的脑中盘旋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她真正获得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目光。她开始自己判断,自己选择,承担自己的行为。当珊最后推断出是母亲故意不救父亲的时候,她终于明白了她所生活的南方,已经从深处开始腐烂,反倒是以工业起家的北方,尚还有自由和健康的空气。
《小狐狸》改编自著名左翼女作家丽丽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同名剧作,并由原作者担任编剧一职——这是这位女作家与惠勒的第三次合作,前两次分别是1937年的《死角》和1940年的《西部人》。本片女主角贝蒂•戴维斯继《红衫泪痕》和《香笺泪》之后,也是与惠勒第三度合作,贝蒂再次证明,她对犹如女巫般邪恶的角色的把握是无人能及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蒂在影片中通过三个细微的情节使这个人物呈现出了立体效果——其中之一是雷吉娜在收拾房间的时候,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心中有所感触,便来到镜子前端详自己现在的模样;另外一个是雷吉娜上楼梯的时候看到了刚死去的丈夫的卧室,她在那一瞬间感到了胆怯,但仅仅是一瞬间;最后一个就是雷吉娜隔着玻璃窗看着女儿和大卫一起去北方生活,她脸上似乎隐约有点泪光。贝蒂通过她的表演告诉我们,雷吉娜再怎么把追求金钱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再怎么精明,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是个母亲。
《小狐狸》最终成了一部经典之作,但令人遗憾的是,贝蒂和惠勒因角色的不同理解而发生分歧——戏剧演员塔卢拉赫•班克海德曾经在舞台上演过同一角色,惠勒认为班克海德对角色的诠释更加到位,而戴维斯不希望重复别人的表演。虽然,该片再次为戴维斯获得了一项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但这改变不了两人关系决裂的事实。戴维斯的淡出,带走了惠勒电影中那股阴暗的气息,同时,也意味着饰演亚历珊德拉的特丽莎•赖特以明朗、知性的形象正式进入了惠勒的电影当中。在随后的几年中,赖特与惠勒合作的《忠勇之家》和《黄金时代》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包揽了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诸多奖项。
6 ) 九项提名无获奖
贝蒂戴维斯在片中的演出中规中矩,谈不上非常出彩,相比之下,我倒是觉得她在彗星美人中的表现更为出色,也许慧片中与她的现实生活更为接近一些吧。另外超不喜欢她的发型。其他演员中,我觉得班舅舅倒是将坏人演绎得让人生恨,是一亮点。辣手摧花中的小美女TERESA WRIGHT还显得很青涩,不过已经初显美人貌。
总体来说,没有预期中那么好,九项提名无一项得奖,也许说明了一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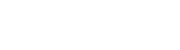




















万恶的资本主义泯灭人性的故事,复杂的室内调度和构图安排,楼梯的运用很牛
一部寓言式、无悬念的家庭纷争剧,不能当悬疑电影看。对几个人物的性格刻画,角力时谁占主动谁被动的调度安排,绝对是范本级的,比希胖更加真实自然的拍摄,但电影语言一点不输。经典。缺点就是剧情简单,太黑白分明了
导演无情的鞭笞资产阶级弊端和批判人性的贪婪,室内构图与镜头调度堪称典范,镜子、楼梯各种场景和道具的运用加上大量景深镜头深刻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贝蒂的表演着实令人惊叹~
“她最精彩的表演是在与丈夫在客厅对话后看着其走向死亡的一场戏。两人由开始的冷冰冰的对话,到恶毒的憎恨,每一个表情转化都是那样的自然,特别是贝蒂,当她坐在沙发上看到丈夫打翻了药瓶之后,她整个人是一丝不动的,灯光打在她的脸上,浮现出死神一样的惨白,没有一句话,面部如僵尸般凝固。而这种凝固就是她冷酷恶毒心态的真实写照。她的眼睛是狠毒的,嘴巴是凶恶的,两只手臂看似悠闲的搭在沙发背上。就这么看着观众。她用不动来衬托那个心脏病发作丈夫的动——请求,从轮椅上挣扎,爬向楼梯,只是在他上楼的时候她才渐渐转过头来,这个时候的摄影完全突出了女人,而那个男人的形象越来越来模糊,似乎成为了一个鬼影。假如在现实中,这个情景的时间是很短的,但在电影里这个时间却显得很长。”——摘引某影评。打男人算盘的毒妇,存备让后人看看。
金钱引诱着世人,家庭,亲情,爱情都摘下了温情的面具,成为赤裸裸的交易
一场戏,所有人物关系利益冲突跃然纸上。戏痴往往就是怎么把每一秒钟演到骨子里,享受其中畅快淋漓
谁教你去伤其他人的心?对于小狐狸而言,有时天使,有时魔鬼,仅此而已。
好演员不是会念台词哦,真正显功力的是反应镜头,看看丈夫挣扎时的贝蒂戴维斯就知道,巅峰演技不用吐一个字,这在她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威廉·惠勒保留了原著戏剧的所有精华,左翼的讽刺和鲜明的道德影射,开篇就明确了圣经的主题,同时加入了他擅长的电影风格,比如说那一个个经典的景深镜头,完美扑捉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片中还有大量镜子物件的使用,暗喻人性的多面性,戴维斯奉献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演技,贪婪势利孤独。
南北战争背景,不少南方的黑人,庄园,工厂,土地,男主人的角色挺没意思的,一副很正直但又过于懦弱的样子。女主的角色精彩很多,婚前不由己,父母更重视两个兄弟,结婚是唯一能做选择的事情,婚后不仅要听丈夫的,两个兄弟还会来打主意,女主怒而反抗。黑人小孩没吃的,“白人有好钢琴,黑人有好嗓子”
两段不幸的婚姻一段是嫁给了欲望,一段是迎娶了欲望,错位的夫妻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悲剧,其中折射出来的是人性私欲的冷血可怖,这种可怖能够完全摒弃亲情与爱情,那种血浓于水的羁绊变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所谓同一屋檐下的大家庭不过是在商言商的拍卖会。真的心疼舅妈,一位母亲得绝望到什么地步才会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心怀恨意!同时对女主也是觉得不寒而栗,一位妻子得狠毒到什么地步才会一动不动等着曾深爱自己的男人死去!情感的扭曲对人的伤害是最为致命,也许正如陈奕迅《红玫瑰》所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2、黑白分明的人物性格塑造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彰显各角色对手戏时的张力表演,缺点是人物的直白也造就了剧情的直白,使得这个家族内斗的戏码有些流于表面,失去了回味的空间。
Take us the foxes, the little foxes, that spoil the vines: for our vines have tender grapes
Take us the foxes, the little foxes that spoil the vines: for our vines have tender grapes. — the Song of Solomon 2:15/Why did you marry me? - Because I was lonely when I was young. I was lonely for all the things I wasn’t gonna get. Every people was so busy at home, so little place, Oscar got all the money…I thought you’ll get the world for me.
原来好多片子里都见过Herbert Marshall,难怪那么眼熟
7/10。舅妈告诉珊她会被家里人强迫出嫁的时候,站在她们身后的舅舅几乎被门帘所遮挡,观众焦虑地等待着隐藏于门帘后人物的爆发,舅妈挨巴掌后珊跑出来看情况,这是一个垂直纵向构图(前景的珊在画面顶部,与楼底的舅妈形成一组透视关系),影片经常出现这种前后景距离很远的短焦镜头以提高张力。奥斯卡父子密谋偷取亲戚的债券那场戏,两人面向镜子背对背交谈,空间的隔阂和镜子反映出二人做贼心虚,后面的戏里亲戚打开保险箱清点,惠勒再次用景深拍摄(左前景的亲戚侧面对着远处紧张的奥斯卡),看得出奥斯卡性格软弱但和父亲一样贪婪。为人正直的亲戚反而身患重病,他打翻药瓶后步向楼梯、挣扎着倒下之际,妻子只是欠着身默默等候,高亮度打光、脸部周围的硬边暗示她的恶毒强势,结尾纯真的女儿隔着楼梯扶手反抗她,只留下她弱势地站在窗前体会着孤独。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to teach mise-en-scene
柏蒂劝珊不要嫁给自己儿子那段拍得太好了!惠勒先把二人的半身镜头放在中间,迫切的柏蒂不断抓住珊并靠近她,所以二人逐渐偏向画面右侧。柏蒂的丈夫奥斯卡(他一直想让促进珊和自己儿子的婚事)回到房间的同时,镜头微幅向左移动,奥斯卡的上半身完全被窗帘遮住,只有下半身占据画面左侧很小的一角,但是他整个人却散发出非常强的压迫感。柏蒂注意到丈夫的归来,慢慢把头扭向他的方向。珊离去后,随着柏蒂和摄影机的移动,奥斯卡才终于露出正面,他阴森地盯住柏蒂。这时切到珊上楼关门的镜头(疑似柏蒂的POV shot),然后切到柏蒂抬眼看楼上的胸上镜头,她张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垂下视线望向奥斯卡,方才还上扬的脸渐渐垮了下来(这里演员的表演好精彩!)。镜头切到柏蒂的背影、奥斯卡的正面,她走到奥斯卡面前时被迎面扇了一巴掌。
她不喝酒也不抽烟,她的心是一把手枪,冰冷得无法打动,生来就要征服世界。
威廉惠勒太会塑造人物,以一场商业合作作为剧情推动,便将众多角色的善与恶、懦弱与残酷如此立体地呈现。金钱当前,婚姻甚至亲情都可罔顾,绝情冷酷的瑞吉娜,心狠狡诈的本,傀儡奥斯卡和蠢蛋利奥,作为恶人代表。而对立面,亦有善良的舅妈、正直的大卫、纯真的亚历珊德拉和宽厚的霍勒斯。剧情最终冷血到了极致,但幸好结尾还有一丝善意走进了光明。
女儿天真无脑,大卫循循善诱,还有话唠舅母,黑人奶妈,患心脏病的爸爸,个个都是充满道义感的卫士,那个年代的表演真是假到不行。倒是哈伯一家满肚子坏水各有特色。尤其是善于算计的大哥和傻乎乎的侄子(血红街道里的无赖)。冷酷的贝蒂最得我心!